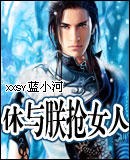独身女人-第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蜜丝林。”她靠倚在我肩膀上。
我现在仔细想起来,真不知道自己的青春期是怎么过的。仿佛是充满困惑,朝不保夕,也不晓得如何拉扯到今日,反正是一种煎熬。
我开车送掌珠回家。她的家环境好到极点,真正背山面海。住在这种地方,还闹意气,照说也应该满足了,但是当这一切奢侈与生俱来,变成呼吸那么自然的叮候,她又有另外的欲望。
当我像她那种年纪的时候,我只希望母亲不要拆我私人的信看,看了也不打紧,最好不要事后一边朗诵一边痛骂。
我的希望很低微。
“别忘记,明天早上见。”我说。
她下车,攀着车窗,眼泪默默地流下来。
这时候她父亲在她身后出现,我推推她。
“林小姐。”何德璋招呼我,说道,“请进来小坐。”
我说:“我没有空。”
“林小姐,多谢你帮忙。”
“我只是帮忙我自己,我不能同你们一样见识。”我冷冷发动引擎,把车子开出去。
回到市区还有一大段路,我打开无线电,风吹着我的脸,公路上一个一个弯,无线电播的柏蒂佩芝旧歌“田纳西华尔兹”像恶梦一样的令人流汗。
我忽然记起我看过的一首新诗:
“——在本区的餐室中,
我与女友,
共享一个沙律,
看着邻桌的一对老伴,
年长男人微笑,
拎起妻子的手,
而我想到我为我的独立,
而付出的代价。”
诗的题目叫《帐单,伙计》。现在我已经收到“独立”的帐单,我希望可以付得起。
那位钱玲玲小姐在门口等我。
我有一刹那的恐惧。忽然又镇静下来,因为姓钱的女士看上去像只斗败的鸡,斗败的鸡照例是不会再举攻击的,这是逻辑。
我用锁匙开门,一边说:“我与何先生没有认识,信在你,不信也在你。”
“我想请你帮忙。”她走前一步。
“不要再让我看见你,钱小姐,你有没有想到,台湾女人在香港的名誉这么坏,就是因为你这种人的缘故。”
“是,林小姐——”
“不要再让我看见你。”我开门进屋子,关上门。
那夜我没睡好,我不能开冷气,别笑,有两只鸟在我窗口的冷气机下筑了爱巢,生一堆小鸟。一开冷气机,它们一定被吓走,变得无家可归,于是只有在热浪煎熬之下睡觉。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真是个善良的好人。可惜环境把我训练得一天歹毒似一天。
掌珠来按铃的时候,我正在穿衣服,边扣纽子边去开门,掌珠穿着校服,我让她坐下。
“换这条裤子与衬衫,你不能穿校服。”我说。
何掌珠很听我的话。
“你父亲知道没有?”
“不知道。”她换衣服。
我抬起她的下巴。“你的气色看上去还不错。”我说。
她沉默。在这一刹那她忽然长大。“蜜丝林的化妆恰到好处”与“蜜丝张有男朋友”时代已经过去。
我们默默出门,默默上车,一言不发的到医务所。护士接待我们,我陪掌珠坐在候诊室。我俏声说:“希望只是一场误会。”
医生召她进去。我没有跟着她,她总得有她自己的秘密。卢医生跟她谈很久。然后她到洗手间去取小便验。最后她出来,我替她垫付医药费。
“医生怎么说?”
“明天再来看报告。”掌珠似乎镇静很多。
我跟护士说:“应该不必等到明天。”
“下午四点左右打电话来吧。”护士说。
我与掌珠回家换校服。
她问道:“蜜丝林,你不骂我?”
“骂你?”我问,“为什么骂你?”
“我做错了事。”
“EON——”我说,“掌珠,女人一生当中。谁没有看过妇科医生?你以为这种事只发生在小说的女主角或是女明星身上?你有空去看看法庭的男女,他们比普通人还普通,长得平凡,穿得朴素,这种人应该白头到老吧,不见得。你会以为这种人对精神与生活的要求都不高吧?不见得。不要认为你很重要,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我耸耸肩,“很平常的。”
掌珠看我半晌,她说:“我仍然希望你是我的妈妈。”
“快!”我扮个鬼脸,“我们要迟到了,还有,这件事千万别跟人说起,我不想人家剥我的皮。”
四点钟,我打电话到医生诊所。
卢医生说:“并不是怀孕。”
我顿时有喜极而泣的感觉。
“如果她觉得不舒服,可以来接受注射,可是我劝她避孕,这样下去很危险。至于不准的原因,是情绪上的不稳定引起内分泌失调,而内分泌是神秘的一件事,医学无法解释。”
“谢谢。”我说,“我明天再来。”
“明早十时?”
“好。再见,谢谢你,卢医生。”
我忙着奔出去,在地理室,把掌珠拉出来,将好消息告诉她,她拥抱我。
我说:“掌珠,下次你会小心,会不会?”
“一定。”她答应我。
我们又去看卢医生。掌珠把一张现金支票还给我。
第8章
我说:“不必急。”
“爹想见你。”她说道,“爹叫你允许他见你。”
“我长着三只眼睛?有什么好见?”我问。
“你不想见他?”
我心里念头一转,好久没到嘉蒂斯吃饭,敲他一笔也不错。我说:“嘉蒂斯吃饭?”
“好!”掌珠乐得要死。
她倒是很起劲。我看着她。
可怜的女孩子。“令堂去世多久了?”
“我出生的时候,她难产。”掌珠说。
“你才十六岁。十六年前医学已经非常昌明,哪有难产说去就去的?”
“我不知道。”
我耸耸肩。“清明可有去扫墓?”
“她不是葬在香港。”
“你是香港出生的,不是吗?”我觉得稀奇。
“是,母亲的骨灰被运回美国加州,她在那里出生,在那里长大。”
“嗯。”
到嘉蒂斯吃饭,坐下我便点了三种最好的酒。
何德璋说:“林小姐,我们之间有误会,我希望消除这个误会。”
我说:“先让我吃完这一顿,然后我再决定是否原谅你。”
“原谅我?”何德璋愕然。
“自然,否则还要你原谅我不成?”我指指鼻子。
掌珠在一旁急得什么似的。
“你对我的成见很深,林小姐。”
“哈哈哈,何先生,你抚心自问,你的所作所为。德性品行,算不算上等人?”
他很生气,“一切都是误会。”
“一场战争发动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也是误会。”
海龙王汤被送上来,我举案大喝大嚼。
何德璋食不下咽,说道:“林小姐,我发觉你这个人是活脱脱的理论派,什么都要讲道理。”
掌珠忍不住,“爹,最喜欢讲歪理的是你。”
“大胆!”他朝掌珠瞪眼。
“你就会骂我!你从来不了解我!”掌珠说。
何德璋说:“掌珠,近年来你令我非常失望。”
他转向我。
“她受了我的坏影响。”我说道。
侍者撤去汤,递上蜗牛,我换杯“堡多”红酒。喝得起劲。我一点也不生气,真的不气,我把愤怒都溺毙在食物中。难得吃一顿冤家——现在我没有冤家。又没有朋友。我是一个再平和不过的人。
掌珠用手支着下巴,她根本吃不下面前的食物,她说:“蜜丝林,我从没见过你吃这么多东西。”
我把半打蜗牛解决掉,抹抹嘴唇。
掌珠问:“第三道菜是什么?”
“烧小牛肉,蔬菜沙拉,煮茄子。”我说。
何德璋说:“我可以解释钱小姐那件事。”
“我不感兴趣,”我说着喝一口酒,“那是你家的事。你运气好,最近我性情好,否则大家在法庭上对答。”
“你无法消除你的成见?”他问。
“没法子。”我放下杯子。
“我很难原谅你这样的人,况且你何必要我原谅你?我对你的生活没有丝毫的影响作用。”我说。掌珠叫侍者把她的食物拿走。
我继续“吃”的伟大事业。
何德璋瞪着我很久。
我以为他又有什么话要说。
谁知他忽然说:“老天,我从没见过这么能吃的女人!”
我回瞪他,忽然忍不住笑,一口红酒全呛在喉咙里,咳嗽起来,用餐巾掩住嘴。
“上帝,”他说,“你吃得像头猪了!”
“现在你说我像头猪!”我骂。
“你还没有叫甜品,要什么甜品?千万不要客气。”他居然懂得讽刺人。
掌珠说:“唉,你们两个人像孩子。”
我说:“我要苏珊班戟。”
“你一定要吃完!”他朝我瞪眼。
“放心。”我说,“吃不完是你孙子。”
“你教书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吧?”他很怀疑的说。
“不,我是独眼J。你知道扑克牌中的J?有一张是侧面的,永远只看到他一只眼睛,另外一面没人知道。我就是独眼J。”
“蜜丝林——”掌珠几乎想哭。
何德璋看着我很久很久。
我没他那么好气,吩咐侍者:“苏珊班戟,爱尔兰咖啡——一匙羹糖,一个XO拨兰地。”
“蜜丝林——”
“就那么多。”我说。
“所以你不打算原谅我——”他说,“我这一顿饭是白请了。”
我微笑。活该。他准备一千元付帐吧。
“不过我与掌珠都很感激你,林小姐。”他说道。
“不必客气。”我说。
我想我有点醉,酒喝得大多,大多种类混在一起。
他伸出手,我不与他握。
“仍然生气?”他问。
“我为什么要生你气?你对我来说一点价值都没有,你是个小人,专门骚扰我的生活,令我不安,如果你可以停止这些无聊的动作,我已经感激不浅。”我说。
“你歧视我,林小姐。”何德璋说。
“你完全说对了。”我说。
“我送你回家。”他说。
“不用。”我说。
“你一上来就喝醉了,我不相信你的车子到得了家。”
“别小觑人。”
我们在楼下分手。我走到停车场去取车子。被凤一吹,酒气上涌,心头闷得难受,忽然有一丝后悔喝得大多。
电梯中有两个小阿飞,眼睛不停的向我飞来。我很气。
男女再平等,女人还是得视这种色迷迷的眼色为戒——如果没有看的时候,哭也来不及。
这时小阿飞甲向小阿飞乙施一个眼色,趋向前来问我:“喝多了吗?”
我不出声,到了停车场四楼,他们跟我走出去,我就知道事情不妙。我当时并不害怕,一直向前走,停车场里一个人也没有,阿飞甲把一只手放在我肩膀,我“霍”地转过头去,他们两人反而吓了一跳,松掉手。
我厉声问:“想干什么?”
阿飞乙自怀内拿出一把小刀。
“这把刀?”我冷笑一声,“切牛排还嫌钝。”这时我已知道腕上的手表可能要不保了。
身后忽然又伸出一只怪手搁在我肩膀上,我马上心头一凉。
我身后的人发话了:“滚!给我滚!否则就揍死你们!”
我如逢大赦:“何德璋!”
我身后那人是何德璋!
小阿飞放脚便跑,其中一个因地上汽油滑,还摔了一跤。
我说:“为什么不把他们扭往警局?”
“我也没有把握打赢这两个人。”他问,“你没有吓着吧?”
“没有,刚在发冷,你便出现了。”我说。
“你也大意,这两个小阿飞一直尾随你,你还不知道。”
“我喝醉了。”我承认。
“我开车送你回去。”
“掌珠呢?”我问。
“在车里,”他说。
“你怎么会跟着来的?”我问。
“普通常识。”他说道,“你今天打扮得这个模样,又戴着金表,无论劫财劫色都是上乘之选。”
“多谢。”我瞪起眼睛。
他替我拉开车门。
掌珠说:“蜜丝林,你没事吧?我让你坐前面。”
“不,我坐后面。”我扬手阻止。
“为什么?”
后面安全。
掌珠把地址告诉她父亲。
我靠在后面的座位上闭眼休息。坐后面最好,不必管闲事,到家便下车。坐后座的人永远是无关痛痒的陌生人,何尝不是逃避的方式?只有苦命人才开一辈子的车,命好的都有司机。
掌珠悄声道:“蜜丝林,到了。”
我睁开眼睛,“呵,谢谢。”我说。
何德璋说:“我送你上楼。”
我没有拒绝,跟他上楼,他沉默地看着我用锁匙开了门。
我忽然笑道:“如果现在那位钱小姐看到这种情形,我真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
他不出声。
我说:“再见。”关上门。
我觉得寂寞。如果一天到晚不出去,反(奇qIsuu。cOm書)而死心塌地坐在家中看电视,现在热闹了半日,独自回家,非常有曲终人散的感觉,所以我也喜聚不喜散——贾宝玉脾气。
我把手袋扔在一角,脱下身上“柏可罗宝”的裙子,倒在沙发上。我撩撩头发,取一面镜子来照。左脸颊上一个泡,唇膏早已溶掉,粉糊成为一块一块,我合上镜子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