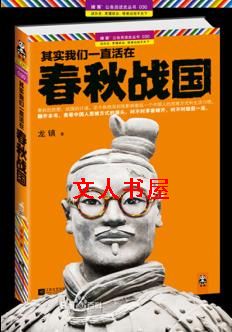我们终将独自长大-第2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许宝榛,你这是要谋杀吗?”
我看着他狼狈却仍旧英俊的脸,不知怎么就脱口而出:“你一定会去军队吗?”
“可能去,也可能不去,我还在和他周旋。”他没有说“他”是谁,但我知道,是他父亲。
司机放了音乐,李缪缪和祝融似乎都昏昏欲睡,没有留意我们的说话。我也不知自己是什么想的,突然就说:“要不,祝融你就去吧!如果那条路更好走的话,你就去走,不要顾忌什么!”
我听见他轻声地笑了:“世界上没有什么好走或不好走的路,你若是喜欢这条路,再苦再累亦是甘之如饴,若是不喜欢,再多的风光与美景,都如步步踏在荆棘上。所以宝榛,永远不要为了迎合别人而委屈自己。”
≡¨文‖
≡¨人‖
≡¨书‖
≡¨屋‖
≡¨小‖
≡¨说‖
≡¨下‖
≡¨载‖
≡¨网‖
第8章 信任
人生似乎就是这样,你觉得不可原谅的事情,若将行凶者换成身边的人,其实也没有那么罪不可恕。因为你们是朋友,无论对方做错什么,你在愤怒悲伤之余仍会找千万个理由为他开脱。
因为你们是朋友。
01。
在那场席卷博陵的沙尘暴过后的那几天,博陵一直是晴天,我的心情也随着感到雀跃—那是近两个月来,我们过得最快乐的几天,我、祝融、易扬和李缪缪仿佛又回到了从前,那些令人不快的事,都被我们抛在了脑后,谁也没有去提起,犹如什么都没发生过。
虽然我心里还有隐隐地担忧,祝融会去参军吗?他会忤逆祝参谋吗?要是最终他仍是抗衡不了,要离开,那么该怎么办?但这种不安很快被我抛在脑后,我向来善于趋利避害,那些不好的念头仅是一闪而过,便被我刻意地摒弃。
我更加珍惜我们在一起的时光。
我也一直没有再想起林达西,或许是因为祝融的话,或许就像许宝桐所说的,我其实根本没有那么喜欢他,所以我对他的恨其实也没有很深刻。我只是迫切地希望这个人快一点从我的生命里消失,不要再出现了。
有几次李缪缪还在我面前说到了他:“真不知道你是怎么看上那样的人!”
“我也不知道,现在想想我也觉得很神奇!”我轻描淡写地说起,心里平静得很。
只是有时候,很多事情并不是你这样想,世界就能如你所愿。
接到许宝桐的电话是在周四的早晨,我当时正在实验室,手机调了静音,在兜里响了好几次我都不知道。直到课间休息,我准备拿出来备注作业,才发现里面有许多个未接来电,都是许宝桐的。
那一刻,我的大脑出现了两三秒的空白,像是被人突然按下了暂停键。短暂的停顿过后,我突然觉得恐慌—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否则许宝桐不会给我打这么多的电话。
我回拨过去,因为慌乱按了好几次才成功拨出,几乎是刚接通,我就听到许宝桐尖锐的嗓音,这些年,我从未见过她如此失态。
“宝榛,宝榛,祝融被警察带走了!”
“你说什么!”我站了起来,丝毫没意识到整个实验室大半的目光都落在我身上,包括还拎着烧瓶的老师。
“祝融打了林达西,现在被带到了警局!”
“别开玩笑了。”我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干涩,“怎么可能,别和我开玩笑!”
“没人和你开玩笑!我在新洲警局门口等你,快点过来。”
我忘记和老师说一声,甚至忘记自己还在上课,抓着手机直接就从实验室冲出去,没人拦着我,应该是根本没来得及拦住我。我拼命地朝校门口跑,在校道上不小心撞到一对正在拥抱的情侣,顾不得他们的惊叫和咒骂,我气喘吁吁地拦下了一辆正准备离开的出租车。
“去新洲警察局!”
司机从后视镜里看我,细小的眼睛里透露着我非常不喜欢的打量,我又重复了一次:“去新洲警察局!”他这才嘟囔了一句什么,慢慢地再一次发动引擎。
我这才发现自己身上还套着学校实验室给学生准备的不知道穿了多少年发黄的白大褂,左手还戴着白色的塑胶手套—在打电话时,我只扯下了右手的手套。
我脱下手套时才发现,在十二月微凉的早晨,我的手上已出了一层薄汗,不仅如此,我的脸上、身上都布满细密的汗珠,当我打开出租车的门,冷风一吹,鸡皮疙瘩迅速地从每一个毛孔涌出。
许宝桐就像她所说的,在警局门口等我,确切地说,她伫立在一只崭新的绿色的垃圾桶旁边,低头盯着自己的脚,看起来焦虑不安。
自从我们那次吵架后,我们一直没有见面,也没有电话,可此时看到她纤瘦的可怜兮兮的背影,我突然觉得有些难受。
“姐!到底发生什么事?祝融呢?”我尽量克制住自己语气里的不安,好歹对她挤出一个笑,“他现在在哪里,他怎么和林达西打了起来了,到底是怎么回事?”
她的头发被风拂得微乱,她避开我的目光:“祝融在里面。”
“那我们进去啊!你还站在这里干吗?”
“不要进去,我们不要进去!”
“为什么?”我几乎要跳起来。
“祝融父亲已经来了,我想这个时候,我们还是不要进去的好。”她没有看我,像是在喃喃自语一般。我觉得她此时看起来有些奇怪,却又说不出到底是哪里奇怪。后来我再回想起这一幕,慢慢地也就明白了,当时许宝桐脸上的表情叫做踟蹰,叫做犹豫。
“祝参谋来了,肯定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我、我们不进去,或许会好一些!”她又说。
她的话并没让我安心,我心中的焦虑更甚了:“连他爸爸都来了!事情到底是怎样的!他到底是怎么袭击林达西?你把事情给我说清楚呀!”
她用力地握住手中的矿泉水瓶,塑料被挤压发出刺耳的声响,我这才发现,她的手里原来还有一瓶水。
“林达西去学校找我,我们一起去听课和吃饭,然后他送我回寝室楼下。我不知道他和祝融怎么遇见的,又说了什么,总之我听到有人打架下楼时才发现他和祝融打了起来,他被祝融压在地上撞,头流了很多血……”许宝桐的声音不大,像夹在喉咙里,虽然她自始至终都保持着镇定,但我知道她是害怕的,因为她的脸色都白了,像涂了一层厚厚的劣质粉底。
我以为我会忍不住对她发火,对她大吼大叫,可是我没有,此时我的心里只有浓浓的疲倦:“姐,你不知道祝融和林达西为什么会打起来,可我知道,事情一点都不难猜。一定是祝融看到了你和林达西在一起,想让林达西离开你,或许林达西说了什么难听的话,祝融按捺不住,所以对他出了手……”
“我没想过事情会变成这样!”我对上她色彩纯净的眸子,听见她又呢喃了一句,“我真的不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
我没有接话,我们之间又陷入了最常见的沉默,这才是我们最原始的相处方式,不是吗?
北风毫无规律地撩动地面的落叶,偶尔还卷起风沙。我靠在垃圾桶上,忽然想起一个成语:多事之秋。
也不知在警局门口站了多久,或许是一个小时,或许才过了几分钟。我听到许宝桐干涩的,带着试探的声音:“宝榛,我想去看看林达西。”
我在这时才想起了林达西,很奇怪,当我听到祝融袭击林达西被送到警局开始,我一直不停地想着他会不会有事,会不会坐牢,我压根就没想过那个被袭击的人。直到此时许宝桐再一次提起他,我才想起来问,“他现在在哪里?怎么样了!”
她点点头,又迷茫地摇头:“我不知道,他流了很多血,看起来很严重。但是,他昏迷前还记得拿起手机报警,我想应该不会有事。”她的语气非常的不确定。
“他被送到哪个医院?”
“好像是人民医院,救护车是那儿的!”她顿了顿,“你,要不要去看他?”
我听到了自己一声冷笑:“我为什么要去看他?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你要去自己去!”
“宝榛,对不起!”
“你和我道什么歉?为了你和林达西打架的人是祝融,不是我!”我的语气很差劲。
“我想去看看他,就看看,好不好?”她微微垂着头。
不知为什么,我突然觉得特别特别难过,不知道是为祝融,还是为我的姐姐。我朝她摆摆手,表示不想再说话,疲倦地抱住自己的手臂,像是竭尽全力跑了一场马拉松。
许宝桐还是走了,然后易扬来了。
他许是刚睡醒,被我电话叫过来时衣服的领子都没翻好。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宝榛,不要怕。”
我其实并没有怕,我只是觉得担心,已经焦躁,在许宝桐走后这种情绪已经达到满值,几乎要将我烧毁。好在,易扬来了,我终于又有了主心骨。
在电话里,我已经和他说了事情的经过。
“你姐姐呢?”他问。
“她走了,去医院看林达西!”我听见自己没有起伏的声线,“祝融还在警局,她却要去医院看林达西!”
“因为她知道,祝融不会有事,所以,宝榛,你也不要担心!”他站在我身边,手轻轻在我肩膀拍了一下,又快速地收起。
对话就进行到这里,我们没有再继续下去,而是沉默而平静地等待。起初我们两人像垃圾一样靠着垃圾桶傻傻地等,后来阳光猛烈了一些,我们便移到大楼旁边树荫下的花坛。我们一直没说话,默契地将目光投递在警局门口。在这漫长的沉默里,有个规律的重重的心跳声一直陪伴着我们,不知道是他的,还是我的。
我们在警局门口等了很久很久,我甚至没有去计算我们等了多少个小时,直到天慢慢地从天蓝向灰蓝转变,来来往往出入警局的人中,总算有我们在等的人。
我们谁也没站起来。
因为走在最前面的是祝融的父亲祝参谋,虽然我去过无数次侨香公馆,也见过他无数次,但我对他仍是带着一种说不出来的畏惧。他走路的姿势和祝融一模一样,不,应该是说祝融走路的姿势和他一模一样,挺直着背脊,步伐很大,重重地毫不犹豫地落在地面,刻画出他雷厉风行的形象。
在他和两个穿着常服的警卫员大步走出警察局后,紧随其后的是祝融。他身上残留着星星点点的泥土和暗红色的血迹,但好在除了灰头土脸没有什么精神,也没有明显的伤痕。
我想喊他,却被易扬拉住了手,他轻轻对我摇头:“别,别叫他。”
他们慢慢地走向路边的车,而就在这个时候,祝融似乎感觉到我们的目光,猛地回头朝我们这个方向看来。
他慢慢地朝我挤出一个没有杂质,纯粹的笑,好像他不是从警局出来,而是从篮球场赢了一场球赛出来。这个笑容撞进我的眼睛,像一只突然飞来的蛾子,让我忍不住伸出手揉眼睛。
我还没来得及回应,他已钻进了那辆黑色路虎的后座。我知道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因为自始至终,他的手都屈成一个拳头的形状。
02。
我回了学校。
易扬让我先回学校去等消息,至于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他去打听,他是男生,不至于吃什么亏。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微微地笑了一下—自从那件事之后,他很少再露出这样纯粹的没有杂质的笑。许是因为他的话,许是这个笑,我没有再踟蹰,乖乖坐上回校的公交车。
半个小时后,我接到易扬的电话。
我坐在最后一排,略微颠簸的车厢里弥漫着汽油味、劣质香水味还有冷气独有的无法描述的味道,我从窗玻璃上看到自己苍白的脸色。
“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低声地开口,声音很快被四周的说笑声和噪音融化,但我知道他听见了。
“我见不到祝融,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打起来,但还是打听到一些消息。医院说林达西刚醒,有轻微的脑震荡,没有什么大碍……”他的声音充满了懊恼,“你说祝融那家伙怎么只长年纪不长脑袋,动不动就和别人动手!”
“那他现在怎样,会有事吗?”我打断他。
“祝融现在只是保释,得看那个姓林的告不告他!不过我看悬,他本来就……”他忽然顿住,再开口已变了口风,“不过你也别担心,祝融是什么人,他可是祝家五代单传的宝贝疙瘩,祝家怎么可能会让他出事!”
我勉强地回应他,挂了电话,开始给祝融发信息,他的电话我一直打不通。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和林达西打起来,他到底和你说了什么?
—你还真以为你是护花使者吗?
—你是不是被你爸爸没收了手机?
—快点给我回复啊!
可他一直没有回复。
手机安静得就像坏掉一样,我恨不得将它拆开。
我在第二天早上,终于去了医院。
为什么说终于,因为从我知道林达西住院后,我就知道我一定会去。
无论出于哪种原因,我都应该去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