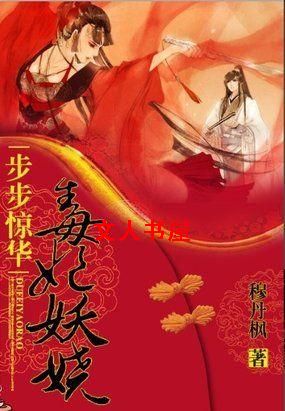鹤止步-第1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贾成荫从来就没有什么奇怪的想法,性幻想更不可能,他连做怪梦都未曾有过。每天醒来,若她说做了什么梦,他说那是梦,不值得再想。她想想也是,这样下来,她很少记得夜里的梦。她睡觉一人喜欢枕头高……他则总是平坦的,如果他们做爱,要么她在上面,要么他在上面,过程之中没有调情或未爱的话,他闭着眼睛非常忠实地尽丈夫的任务。她没有听到过他对别的女人评头论足,同样,她也不谈别的男人。
有时他去开会,打乱了一周一次的性生活,无论走再长,重新相见也不好意思立即把她抱上床。他对她有礼有节。有进她希望他对发发脾气,可是他也未做到。有一次两人去看电影,里面的男人把女人一把抱起来转几个圈,她看了他一眼,他也同时看了她一眼,两人眼睛里看不出什么异样,似乎那样的男女是疯子,他们俩才是正常的。
他们没有一起洗过澡,这么多年,他可能一次也没有看过她的身体,缤玢刚这么想,就吓了自己一跳,赶快止住。
白色的蓝鸟(5)
那磁带有魔力,她将磁带取出来,放入抽屉里一个铁盒里,方如释重负。只有一种解释说得过去,丈夫的癌症转移到脑子里了。他的头脑受到肿癌的压迫,因此产生不合常理的想法。这盘磁带千万别落入外人的手里,书虫儿一生正派,她自己一世清白,都会被这盘带子的内容毁得一干二净。她又把磁带从铁盒里取出,拿出剪子剪掉,她下不了手,一时这磁带显得格外重要,她六神无主,看着磁带,不知怎么处理它才好。最后,她打开桌子中间的暗锁,在磁带壳上写上“逻辑学批判教程第十五章,补充注释”,用一个信封包好,放在存款折子银行卡等重要文件之中。
锁上抽屉。她打电话到医院,她想找给丈夫开刀的那个主治大夫,那个叫盛年年的女人。
电话通了,可是盛大夫已下班了。
她告诉值班医生,她有急事,她需要盛年年大夫家里的电话。她急躁的态度使值班医生十分不快:
“医院无权告诉病人家属医生家里的电话。”
“岂有此理?”
“对不起,这是规定。”那边说完就搁下电话。
惟一的办法就是打电话给沈立,告诉他贾成荫可能已神志不清,开始胡说一些莫须有的怪事。最好让沈立知道,免得出事。但她拨他的电话一半就无法往下进行,她发现她怕与沈立说话。
那么,缤玢对自己说,我不能对一个病人认真,就当一切没有发生,我得挺住,那死亡的边缘上是无边无际的阴森恐惧!
直到这时,她才想到丈夫医院床头柜上的录音机,要是他继续胡说,越说越像真有其事,怎么办?她闪过这念头,披了件衣服,拿起包到客厅穿鞋。
她赶快打的,一头大汗到医院时,已是晚上九点十分。门房拦住她,说是过了探看病人时间,不让进。
她说她是危急病人家属,必须见。她的态度坚决,但诚恳。门房没办法,说是得打电话问有关人,没有几分钟,门房手一摆让她进了住院部高级病房的大门。
全是芙蓉和盆栽莲叶,虽然花园不大,但空气不错。缤玢跑上楼梯,走廊非常安静,亮着灯,她在304病房门口停了停,里面没有动静。她没有敲门,而是推门进去。丈夫坐在床上,脸色安祥,戴着眼镜,膝上放着他的书稿。
缤玢坐在床上。
丈夫抬起头,看见她,非常惊喜,放下稿子一把抓住她的手,把她搂到跟前,他的头埋在她的双乳间,久久不放开。
“怎么啦?”
“真好,你在这儿。”
“怎么啦?”她重复一句。“我是说你感觉如何?”不过她词不达意,显得含含糊糊。
“我感觉很好,从来没有这么好。我想我快恢复了。”他躺倒在床上,她整个人都在他怀里,他抚摸着她,亲吻着她,她喘不过气来。他说,“和我在这儿,我想要你。”
她吓了一跳,以为自己听错了,不过他已经在解她的衣服了。她按住他的手,红着脸问:“在这里?”
“这房间里一直就我一人,你去把门闩上就行了。”他说。
她抬头看看窗子,倒是垂下窗帘,即使不关窗帘,外面是大树,应该说也很安全,这时候不会有护士或医生闯进来。她低头一看自己已经半裸,而丈夫正热情地看着她。奇书网她突然想起那磁带,神色大变。
“你不愿意留在这里,那么我们回家去。”他站起来,抱住她,体贴地说:“离开医院吧,反正早晚都得离开。”
这话太不吉祥了,她的身体一下子僵硬,她紧紧地抱住丈夫,心碎地想,全是回光返照,没一点她所熟悉的样子,仿佛他是个陌生人,她眼睛一下子就红了,好不容易才忍住泪水。
丈夫说:“好吧,明天,医生会同意我们回去。”
5
阳光一早就照射到窗前。贾成荫一身竖条棉布病人衣服,伸伸懒腰,把窗帘系好。护士小姐就进来放好开水,检查仪器,写报告数字。
白色的蓝鸟(6)
护士小姐刚走,盛大夫拿着病历走进来。“今天感觉好吗?”她的声音永远清脆,好听。
“不错,昨天不知怎么就睡着了。”他有点歉意地说,“我们好象没谈完话?”
“我们没谈什么要紧的事?”她一边亲切地反问,一边用手势要他回到床上去。
“记得我们说什么关于幻想的权利。”他自嘲地笑笑。“搞一辈子逻辑学,却不知怎么幻想。”
“你昨天难道连梦也没做过?”
“比吃安眠药还睡得很深,我不太记得是怎么一回事。”
“想再来一次?”
贾成荫发现盛年年的额头极高,眼睛潮湿发亮,今天她在白衣里是一件咖啡色的丝衬衣,一件过膝盖的西式裙。“怎么做梦呢,”他有些惊奇。
“我帮助你。但是做梦还得靠你自己,我没有办法给你一个梦。”她在床边坐下。她把病历放在左边桌上。
盛年年一般都是坐在床前的椅上或凳子上,第一次坐在他床边。不知为什么,他很高兴。这间房是高级病房里最宽敞的一间,卫生间也大些,甚至连床也宽些。如旅馆的标准间,布置也不太像一般的病房,虽然有医院的气味,总有朋友不时送鲜花来,缤玢总是分类装入瓶里,放在适当的位置。
“你今天看上去心情真的很好。”盛年年说。
“是托你的福。”贾成荫说。“你今天看上去很美。”
盛年年脸红了,“你瞧,我忘了你的口才。”
她的身材的曲线在白衣包裹下透出来。她比玢显苗条,不过胸部饱满,腰肢纤细,显得特别性感。他从未这么看除妻子外别的女人,他突然明白,大概是由于我不会有多少幻想的机会了,因此许多本质的东西恢复。生命终结,幻想也就随即终结。
她伸出手,把他的手握着。“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她说。“幻想从另一个生命阶段超越另一个生命阶段,一个个体激发另一个个体。”
“超越我恐惧的?”
“超越肉身的局限,比如让灵魂飞翔。”
他笑了,“你是搞西医的,我是搞逻辑学的,要我们这种人相信神秘主义?”
“信不信由你。若不信就试试,如何?”
“你挑战我,”他沉吟片刻,然后取出录音机,按下键说:“好,成全你,我的大夫。”
盛年年将床单毯子放在凳子上。她的双臂托住贾成荫的头,把他放在枕头上,让他舒展四肢躺平。她胸前的乳沟从这个角度看得一清二楚,从衬衣里凸出来,几乎触到他的脸。房间里弥漫医院消毒剂的气味,她的白帽压着她的头发,显出她白晰修长的脖子。她的手放在他眼睛上,他闭上眼睛后,再也不是消毒剂的气味,而是一股淡淡的幽香,想想,也不是房间里的花香,而像是一种久违的气味,当她一张开嘴说话,那幽香就涌向了他。
贾成荫吸了一口气,浑身舒畅。她的声音像羽毛触及着他的皮肤,抚摸着他,轻轻地说,缺什么,就幻想什么,幻想什么,就会拥有什么。他随着那声音的节奏自语,缺什么,就幻想什么,幻想什么,就会拥有什么。一双手放在他的额头,如同一团火刹那间腾起,一片幽蓝的世界。
不要怕,让我们穿越过去。她说。
他穿了过去。
雨真大,他在雨水中奔跑。
他的面前出现小时经常去的草地。边上是山坡,山坡顶端有棵树,她站在那儿似乎在等他。她柔情地看着他,说她一直就在这儿等他,很好,你终于来了,她拉过他的手。他们一下子拥抱在一起,他亲吻她,她抱着他,草地上开满花朵。
雨水在他们身体中滑过,他问你喜欢雨吗?她点点头。他说我不喜欢,因为和你一起,我不在乎雨。他带着她跑下山坡,街道出现在面前。她突然挣脱他的手,进了一所房子。他跟在后面,穿过一道门,想抓住她,但她比他动作还迅速,他一靠近,她就闪躲开。她的头发散开,她将鞋子脱掉,把外衣脱掉,她的乳房漂亮极了,他一惊,不敢去抚摸,因为她的家人在他们周围晃来晃去,有的盯着他不走开,他的脸发红,因为他的心发颤,他一看见她的裸体,他就受不了,他想抱住她,得到她,想和她融为一体。
白色的蓝鸟(7)
她在前面引路,上了楼梯,全是一间间空房,一进去他就觉得很像教室,里面堆满桌子椅子,突然到处都是人,成双成对,似乎都在等着熄灯等着别人离开,才能做爱,人人都很焦急,被情欲燃烧得难忍难受。但是灯不仅不熄,反而更亮了,而且人更多。
打更的老头来了,房间里的人都蹲在桌子下。别急,他对她说,我们好好找一个地方,仅仅属于我们俩的地方,让我好好爱你一次。他翻出窗子,把她抱了出来。他们跑到一间大浴室,只有未关好的水龙头在滴着水,非常安静,他替她解裙子背后的钮扣,她给他脱裤子,她的手伸入他的身体里,她的抚摸使他实在忍不住呻吟起来。
就在这时,一大帮洗澡的人闯进来。
时间在消失,全是最好的时间。他看着她,她也看着他,无法反抗的情欲掀翻了一切,大庭广众之下,他一把撕开了她的衣服,把她抱起,在他们的注视下,走到大厅,把她放倒在光滑的大理石地上,他的手一挥,玫瑰从天空缓缓飘落,白色的花瓣旋转着芬芳的气息,他解开身上所有的束缚,吻住她的嘴唇,他把她的双手举起来,按住在背后,她一声声尖叫,那些花瓣渐渐组成一面镜子,他看见了另一个他朝他走来。脚步声,整齐的脚步声向他们靠拢,观众一圈圈增加。他不在乎,他动作越加粗野,由着性子来,把她翻来翻去,而她就像附在他身上一样,贴着他的心,他的心狂跳起来,猛地要将他们俩抛出来,抛出去又回来,再抛出去。真轻呵,上升,再上升,他听到八音盒奇妙的音乐,这音乐盖住了一切声音,他哭了起来,快乐到不能再忍受的地步。
盛年年浑身大汗,几乎精疲力竭地瘫倒在光亮的地板上,但是她的衣服依然一丝不乱。贾成荫的呼吸很平稳,好象完成一件极重要的工作,现在是享受休息的时候,闭着眼睛,进入了睡眠。
真没有想到她引导出来的功场,把自己也拉了进去。她只是想多知道情人沈立一些事,却无意之中知道了自己。从这个生命跌入那个生命,这太让她震惊了!这个肉身渐渐被癌症细胞蚀完的病人,她手术刀割开过的身体,在提示她生命中不可抗拒的事,那也是最可怕的事。她一时想不明白。
录音机还在吱吱地响。她走过去,把录音机拿在手里,“啪”地一声关掉。然后才取出磁卡。她将窗帘拉上,房间顿时暗了。她俯下身来,帮贾成荫搭上一条毯子。
6
十四天后。
沈立家里的电话铃声反复响起,却没人接,打电话的人也不愿留言,每响四下,就重拨再打。
侯机室里每个旅客的表情都不一样,行李或多或少,广播里不停地说将起飞的航班以及旅客的名字。
盛年年想,沈立是故意不愿听她声音。如同她与他约好见面,他也不来。你已经得到你想要的,他说得很清楚。不过他说等你去加拿大时,我会去送你的。但他还是爽约了。一定是什么事比她更重要。她在机场这次是五次打电话,可是还是没人接,他办公室也没人。登机的通知这次叫着她的名字,一次中文,一次英文。
她把手机收起。提起脚边的箱子,走入已经没人排队的登机口。
缤玢一身黑裙坐在家里沙发上已失神了一个多小时。太阳西斜后,天色就暗淡了。追悼会是一种不同于其他折磨的苦刑,它让你死去活来,奇……書∧網脱一层皮,掉进冰窟里。尤其是在两个多月守护寄寓了无限希望之后。
丈夫的书和稿件全部运回家,堆在书房里。追悼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