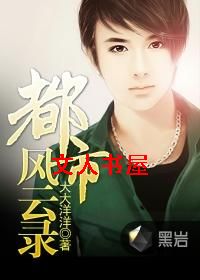嫁东风-第2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脚步声,在我面前停下,我闻到他衣上淡淡的酒香。
第十四章 结发为夫妻(下)
“宓儿。”
他在唤我。眼前陡然大亮,我抬头,只见桌上金盘内的喜杆动也未动,他却是以手掀去了我顶上盖头,此刻正昂然而立,半眯着眼,怔怔望我。
“王爷。”我启唇,温软轻唤。眼中的他,玉带金冠,朱红锦袍上分明绣着与我衣上同样的图纹——
鸳鸯戏水。
酡色一点一点,逐渐侵染上我精雕细琢的容颜。他含笑取过桌上金杯,在我身侧坐下,捉起我手掌将其中一杯递予了我,我忙双手捧过,盈然回望于他,依依道:“臣妾虽是弱质女流,却亦懂得礼义廉耻。今夜与王爷饮下此酒,从今而后,苏宓生是王爷的人,死,亦是王爷的魂。”
他目中有光亮一闪而过,握杯的手亦不自禁紧了紧,喉结微动,微一用力便揽过我去,手臂交错间,已然交颈。酒液滑下喉咙,有些微地烧灼,我缓缓阖眼,鼻尖充盈着他衣领间清冽的檀香气息,心神蓦地无比安宁,静和,耳畔他忽而轻语:“本王听说你们楚朝男女成婚时,都要行合卺之礼,燃龙凤高烛,虽不解其意,却因着你的缘故,也一一照办了,你可欢喜?”
我胸中微暖,感动于他的用心,不由低讷了语声,“王爷厚爱,臣妾愧不敢当。”
他却疏朗一笑,收回了手去,结束了合卺之礼。将金杯放回桌上,他朗声笑道:“你不敢当,却有谁人敢当?”说着环顾四周,唇角始终噙了一抹暖暖笑意,“这红烛高照,软玉温香,倒也别有一番情境,看来南人的规矩,却也不尽是繁文缛节。”
我不由含笑望他,“王爷对南国规矩礼仪知之甚广,沿用上又能取其菁华而去其糟粕,臣妾实在心悦诚服。”
闻言,他眉宇飞扬,掩饰不住的欢喜之意在眼中流转,忽而凑近我身前,重重闻了闻,奇道:“宓儿身上好香,本王方才便觉暗香盈鼻,然而却只淡淡,怎么此刻竟愈加浓郁了起来?”
我含笑不语,只依依望着他,见他一意催促,这才缓缓道来:“此香名为茵墀,乃西域所贡,平时香气甚淡,遇酒则浓,臣妾方才饮酒,故而香气逐渐浓郁。”
“倒有这稀罕物事?”他讶然扬眉,忽而伸手拉过我身子去,我被动地撞入他宽厚的胸膛,正要呼痛,却见他已然埋首我颈项深深嗅闻起来。我心头一紧,身体亦不自觉僵硬,只觉全身血液直冲头顶,脸颊红透,几乎晕染到了耳根。他鼻端温热的气息缓缓熨烫上我细腻的肌肤,有些腻腻的痒,然而更多,却是无法言状的奇异感受,一点一点,自心头缓缓攀升。“宓儿,”他喃喃低语,“为本王宽衣。”
脑中登时轰鸣。我自他怀中退出,怔怔仰望着他,我的生涩令他笑意几乎溢出眼中,见我不动,又催道:“春宵一刻值千金,还不快些动手?”
我直羞赧到几乎欲寻地缝而入,而他却愈发欢喜,一径催促,便如孩童耍赖般抬头挺胸,待我为他宽衣。眼见避无可避,我扭过脸去,用力咬一咬唇,小心翼翼探出手去,颤颤地碰上了他的衣襟,我阖上了眼,然而正当我鼓足勇气要解开第一颗衣扣时,突来的“笃笃”声却惊得我立时收回手去,望向了门口。
“大胆!”他脸色陡暗,镇声道,“何事来报?若是无足轻重,定斩不饶!”
门外有瞬间的沉默,尔后一个声音响起:“启禀王爷,小王爷突然昏迷不醒,娘娘不知所措,特来请王爷前往做主。”
“什么?!惇儿他——!”他面色剧变,猛转身便冲向门口,只听“哐啷”一声脆响,桌上放置喜杆的金盘已然被他撞翻在地,喜杆滴溜溜滚出老远,然而他看也未看一眼便拉开门,一把扯住传信之人的衣襟道:“惇儿可是旧疾再次复发?太医可在?”
是穆昌。只见他面色慌张,摇头道:“小人不知。”他说着,探头看了看我,眼神颇有不安,低低又道,“娘娘焦急不已,又……不便来此,因此才命小人火速来禀王爷,请王爷亲往做主。”
拓跋朔一把搡开穆昌,扭头看我,眉头紧蹙,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些什么,然而终究没有开口,转身径直去了。那穆昌随即跟着离去,二人脚步匆忙,很快便消失在廊下。
一切发生地太快,我来不及作出任何反应,只怔怔地望着他绝尘而去。脸颊上的热度已缓缓消退,取而代之的却是彻骨的冷寒,有莫名的酸涩浮上心头,我低下脸去,却见门边角落里一处物事金灿灿地失落着——却不是喜杆是什么?我上前捡起,拢入怀中,属于金属的冰凉在我温热的手心一点点蔓延。
他竟然,就这样离去了。温言软语犹然在耳,转眼却已是人去心凉。
我颓然起身,不防身后却突然响起明显刻意压低的脚步声,我猛然回头:“什么人——?!”
尚未来得及看清闯入者的面容,一记手刀已重重劈落我颈中,瞳孔在瞬间收缩,未及惊呼,剧痛已蓦然袭入神经,眼前一黑,我软软倒下,再无知觉。
第十五章 霜刃未曾试
身子仿佛不是自己的,软乏不堪,半点动弹不得。恍惚不知身在何处,只觉鼻端充盈着酸腐的恶臭,一阵一阵直令我恶心欲吐,然而,却也终究因此而捡回了意识。我缓缓抬起沉重的眼皮,茫然四顾——这是哪里?
入目所至,皆是一色的乌蒙蒙。我狠狠闭了闭眼,待视力渐渐恢复后再缓缓睁开,只见壁上一扇小铁窗透着微薄的光亮,照着脚下方寸之地,却也足够我看清四周:墙壁皆石块所垒,并不平整;地上有滩积水,颜色已然发黑,周遭四散着腐臭而潮湿的草料,冲鼻欲呕。石屋棺椁一般密闭,唯一的出口是一扇木制的大门,然而门上一只明晃晃的大铁锁却明确地昭示了我现下的处境——身陷囹圄。
我心下恐慌,不知离我被劫迄今已过了多久,瞧不见日头,更不知今夕何夕!腹中饥渴难熬,身体更是软乏无力,只稍一用力,额上冷汗便涔涔而下。我伸手扶住墙壁,用尽全身气力才勉强坐直身子,不过这样小小一番动作,却已令我气喘不已,仿佛遭人强行撕裂般,胸口更是一阵剧痛。我按捺不住汹涌而至的气息,猛伏倒在地便咳嗽了起来,直咳地天旋地转,眼前阵阵发黑,连推门而入的脚步声亦未曾听见,直到一双穿着兽皮靴的脚正正停在我的眼前,我才猛然收回神智,抬起头来——
一个陌生男人。
男人俯视着我,长满络腮胡的紫红脸庞扭曲着,眼神很是憎恨与不屑。见我抬头望他,他一脚便踢在我的肩膀上,以着生涩的南话恶声恶气道:“楚朝的公主,你也有今天!”
我被他踢地摔倒在地,右脸颊狠狠撞在凹凸不平的石砖上,直撞地我脑中一阵眩晕,不禁痛呼一声,伸手捂去。一丝火辣辣的痛登时蔓延开来,掌心已是一片濡湿,然而来不及顾忌脸颊的伤口,更快的剧痛却蓦地自脑后传来——那男人一把揪住我满头青丝迫使我半抬起身子,与他面目相对,恨声道:“拓跋朔加诸给我的羞辱,我要加倍地还给他。你,若不是你,本王怎会遭被擒之辱!”
脸上有热热的液体顺颊而下,滴落在地上,触目惊心的赤红,很快便没入泥中。我冷笑,勉力扭过脸去,只以眼角余光瞄他,他一脸愤恨而不知所措的模样更是令我几乎笑出了心肺,“若你以为抓了本宫,便可以打败拓跋朔,那么你太愚蠢了。”我浑然不怕他愈发阴沉的脸色,只一径激怒于他,“尽管去要挟他罢,本宫保证你的下场会比上次悲惨十倍、百倍、千倍!”
他怒而抬手,一把便将我重重扯到面前,目眦欲裂,如一头狂怒中的野兽般吼道:“不可能!你是拓跋朔宠爱的女人,他不会不顾你的死活!”
他口中的酒肉腥臭和在气息里喷薄而出,直令我反胃不已,我嗤笑道:“你觉得本宫值多少代价?可不可以让拓跋朔如你一般写下降书,从此臣服于犬戎?”
我语气极是不屑与讽刺,然而他却眯了双眼,“本王正有此意。”
我懒懒阖眼,幽幽道:“那么,你尽管去要挟他罢。本宫亦很想知道,自己究竟值不值这个代价。”
没有言语,然而灼热的气息却缓缓近了面上,我心中一动,猛睁开双眼,却见那男子目光自我脸上移开,转而在我身上肆意来回,逐渐不善,忽而伸手执住了我下颚,邪邪道:“你,还没有跟他燕好罢?”
胸口气息蓦地一滞,来不及羞赧,发自内心的恐慌已然一点点蔓延到四肢,我镇声道:“若你胆敢轻薄,本宫会即刻自尽。”
他神色一愣,但随即释然,冷笑道:“本王会令人严加看管,你如何自尽?”
我眼神愈发冰冷,语气亦不自禁凌厉了开来,“本宫若苟且存活,必定会将今日之辱牢记心头,来日加倍奉还。”
他松开了手,眼神中闪烁着估量,仿佛在思索究竟要如何行止。我有意扰他思绪,沉声道:“您擒了本宫,不过是想借此对付拓跋朔,请君入瓮。本宫若折在你手上,你便再无筹码与他叫阵。”
他恼道:“大不了与他一战!”
我冷笑不已,“何必自欺欺人?若你自负是他对手,又何苦使此下三滥的招数?”
他亦冷笑,并不受我言语之激,“你们南人不是有句话叫兵不厌诈么?本王不过是借用借用罢了!”
“那么,你便更不能动我。”我勉力爬起身子缓缓倚墙坐定,望着他阴郁的脸色,“唯有本宫完璧无缺,你才有资本唱完这出戏。王子殿下,你以为呢?”
“你——!”他危险地眯了双眼,一手摩挲着满是虬髯的下巴,忽而一摔手,“即便果真如你所说,你也莫要得意!拓跋朔已经知道你在本王手里,等他中了本王的圈套,到那时,你们两人的性命都操纵在本王手中,看你还能不能如此牙尖嘴利!哼……”
他说罢,怒而摔门而去,外头的随从亦随即锁上了牢门。已然悬到嗓子眼的心终于能落回原处,我几乎虚脱地躺倒了下去,背脊冷森森的一阵汗湿。
“好险……若那横人不受我言语之激,我行我素,只怕我当下便果真要折在此处了。”我不禁喃喃自语。受此惊吓,神智终究是大明了,很明显是犬戎乘拓跋朔与我大婚之际派人混入王府,伺机擒我以报当日之辱,所以才会事先安排好一切,调虎离山……可是——!我脑中登时激灵,可是为什么拓跋惇会那么适时的犯病!那报信之人是府中的总管,自然足以取信拓跋朔,否则以拓跋朔之精明,即便关心则乱也应该不会受生人蒙蔽,如此、如此……我本来脑中纷乱,思绪如一堆乱麻,盘亘缠绕找不到头,然而现下想通这一点,却蓦地醍醐灌顶般明澈了,一个名字缓缓浮上心头——
杳娘……
“一定是她!”我蓦地咬紧牙关,恨声道。她是拓跋惇生母,只有她最能掌控拓跋惇的身体健康,而让孩子早不犯病晚不犯病,却偏赶在大婚之夜犯病,其用心之深尤见一斑!我理清楚来龙去脉,心头登时冷寒不已,这女子,初时我只当她善妒,虽几次激怒于我,亦未真正用心与她计较。未料其用心竟如此之狠,为报夺宠之恨,不惜勾结外敌、折磨亲儿,如此种种,倒是我小觑了她!我愈想愈觉愤恨,指甲几乎生生攥入掌心,火辣辣地痛,然而临此境地,身体的疼痛我又如何放在心上?愈是疼痛,愈是令我清醒,而此时,我最需要的,便是清醒。
一低头,微弱的光亮中我清楚地瞧见身上那件尚未来得及脱下的喜服,那金线所绣华丽而反复的图纹虽已污浊,却仍旧明晃晃的刺目。我一手抚上脸颊伤处,血迹已经凝固,亦不若初时疼痛,只余冷凉的触感反复刺痛着我的神经,提醒着我该做什么。冷笑攀上了嘴角,即便没有铜镜,我亦知道那笑,凌厉而冷寒,没有丝毫温度。报仇。我听到心底深处不知名的声音,枉我还言之凿凿说要尽全力保身边人周全,连自身的安危都悬于他人之手,这样子的我,有什么资格苟活于天地之间?这肮脏污浊的处境,满身满心的伤痛,更是令我双眼几乎恨出血来,我不是予慈拔苦的神佛,更不是逆来顺受的痴人!这一次,我不会再选择忍让、宽恕,若得度过此次劫数,我定要大权在握,肃清奸佞,从此我为刀俎,人为鱼肉。我心中暗暗立誓,当下再不作他想,只静静倚靠着墙壁小憩,留存体力。
第十六章 始是新承恩泽时(上)
恍惚不知又过了多久,只觉窗户中透进来的光亮由明黄变成了惨淡的白。应是夜间了,我心头切切,仰望着石牢上方那抹幽亮,手指无意识地在泥地中划着,一笔又一笔,待得惊觉时,已然清楚地写出“拓跋朔”三字。我怔怔地望着那名字,心中暗惊不已。我到底在期待些什么?为什么会写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