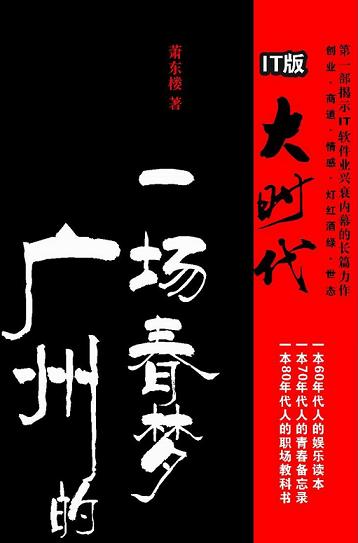充满奇想的一年-第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自童年起,人们就一直教导我,碰到麻烦的时候,去看书、学习,把麻烦找出来,去看看书中是怎么说的。要找的主题已经确定了。悲哀是最为常见的痛苦,但关于它的文献少得可怜。有一本叫《遣悲怀》A
Grief Observed,爱尔兰作家克莱夫·斯特普斯·刘易斯(Clive Staples Lewis,1898…1963)的作品。的书,是克莱夫·斯特普斯·刘易斯在他妻子去世之后写的。还有一两本小说偶尔也能见到相关的段落。例如,托马斯·曼的《魔山》就描述了黑曼·卡斯托普的丧妻之痛:〃他的精神出问题了;他的内心坍缩了;他头脑麻木,做生意折了本,致使卡斯托普父子公司损失惨重;而第二年春天,他在寒风凛冽的栈桥上视察仓库,染上了肺炎。心魂俱碎的他承受不了这疾病,虽然得到海德金德大夫的悉心治疗,还是没过五天就死了。〃在古典芭蕾舞剧中,往往有这样的时刻:某对恋人,女的行将香消玉殒,男的试图将其挽留人间,此时蓝色的灯光亮起,白色的裙子飘动,他们会跳起预兆到死亡终究会来临的双人舞:影子之舞。还有一些诗歌,实际上是很多诗歌。有那么一两天,我反复念诵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英国诗人。的《被遗弃的人鱼》:
孩子的声音本应
(再呼唤一次)动摇母亲的心旌
孩子的声音痛苦而悲哀
她肯定将会归来
有好几天我反复念诵奥登 Wystan Hugh Auden(1907…1973),美国诗人。的诗,剧本《攀登F6高峰》中的《悼亡诗》:
停止时钟的转动,拔掉电话的线路
让狗儿别吠叫,用一块美味的肉骨
不再弹奏钢琴,也已没有鼓声
将灵柩带出来,请来致哀的人
在我看来,这些诗歌和影子之舞最为贴切。
除了这些对悲哀的痛楚和暴烈的抽象描述,还有一些通俗读物,一些如何对付这种症状的指南,有的〃具备实用价值〃,有的〃富有启发性〃,但它们全都毫无用处。(别喝太多酒,别用保险赔偿金来重新装饰卧室,加入一个互助团体。)然后还有专业文献,弗洛伊德和梅兰妮·克莱因之后的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工作者所做的研究。很快,我发现自己转而求助于此类著述。我从中看到很多我业已了解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让我心安理得,证明正在发生的情况并非是我想象出来的。例如,从国家科学院医学研究所1984年编辑的《丧亲的反应、后果及其照料》这本书中,我得知人们对亲友死亡的即时反应通常是震惊、麻木和难以置信:〃主观上,活着的人可能会觉得他们被裹在椰壳或者毛毯之中;在别人眼里,他们也许能够节哀顺变。因为死亡这一事实尚未进入到他们的意识,活着的人可能会显得完全能够接受这种丧亲之痛。〃
所以,在这里,〃非常冷静的人〃的效应就出现了。
我继续看。马萨诸塞州综合医院哈佛丧亲儿童研究所的威廉·瓦登让我得知,人们曾观察到海豚在丧偶之后拒绝进食。人们观察到,野鹅在丧偶之后会不停地飞翔,不停地哀鸣,不停地寻觅,直到它们本身失去方向感,迷失了道路。我看到人类也显示出同样的反应模式,而这我早已知道。他们寻觅。他们绝食。他们忘记呼吸。他们因为缺氧而晕倒,他们没有流出的眼泪阻塞了静脉窦,他们往往带着难治的耳部感染疾病去看耳科门诊。他们无法集中注意力。〃我隔了一年才能看报纸的标题。〃有个三年前丧夫的朋友告诉我。他们丧失了所有层次的认知能力。和黑曼·卡斯托普一样,他们也在生意上折了本,蒙受惨重的财务损失。他们忘记自己的电话号码,到了机场却没有带有效的身份证件。他们生病,他们卧床不起,他们甚至,也跟黑曼·卡斯托普一样,撒手人寰。
一篇又一篇的研究报告都记录了这〃导致死亡〃的一面。
我开始在每天早上去中央公园散步的时候带上身份证,以免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
我在沐浴的时候,如果电话响起,我再也不会去接,以免在地砖上摔死。
我得知有些研究非常著名。它们是此类文献的经典,我看到的每篇文章都有引用。例如扬格、本雅明和瓦利斯1963年发表于《柳叶刀》第二期第454至456页的文章。他们在英国对4486名当时丧偶不久的寡妇进行了为期五年的跟踪研究,研究表明〃寡妇在丧夫之后前六个月的死亡率明显比已婚妇女要高。〃还有利斯和卢特金斯1967年发表于《英国医学杂志》第四期第13至16页的文章。他们对903名丧亲的人和878名没有丧亲的已婚男女进行了为期六年的跟踪研究,研究显示〃丧亲的夫妻第一年的死亡率显著增高〃。医学研究所1984年编撰的那本书对这种死亡率的增高给出了功能性的解析:〃迄今的研究表明,和其他多种压力源一样,悲哀通常会导致内分泌、免疫、自主神经和心肌系统的改变;所有这些基本上都受到脑功能和神经递质的影响。〃
我还从这类文献中得知悲哀分两种。较轻的一种是〃不复杂的悲哀〃或者〃正常的丧亲反应〃,和〃成长〃以及〃发展〃有关。根据第十六版的《默克手册》,这种不复杂的悲哀通常表现为〃焦虑症状,例如初次失眠、慌乱不安和自主神经系统亢奋〃,但〃一般来说,除了在那些情绪容易波动的人中之外,它并不引起临床抑郁症〃。第二种悲哀是〃复杂的悲哀〃,在这类文献中,也被称为〃病理学的丧亲反应〃,据说它发生的情况多种多样。发生病理学丧亲反应的一种情况是……我反复地看这一段……生者与死者原本有着异乎寻常的相互依赖。〃丧亲者的快乐、生活费用或者声望真的非常依靠死者吗?〃这是哥伦比亚大学精神病学系的医学博士戴维·佩雷兹提出的一个诊断标准。〃当被迫分开的时候,丧亲者失去死者之后会觉得无助吗?〃
我思考着这些问题。
1968年,有一次我突然得在旧金山过夜(当时我去办点事,雨一直下个不停,将一次傍晚时分的采访推迟到隔日早晨),为了能陪我吃晚饭,约翰从洛杉矶飞过来。我们在俄尼餐厅用晚餐。饭后,约翰花了十三美元,乘坐太平洋西南航空公司的〃夜间飞行者〃回到洛杉矶国际机场。在当时的加利福尼亚,花二十六美元就能买到从洛杉矶到旧金山、萨克拉门托或者圣荷塞的双程机票。
我想起了太平洋西南航空公司。
该公司所有的班机都在机头上画着一个微笑。机上的乘务人员都穿着鲁迪·葛因雷希风格的红色和橙色相间的性感超短裙。在我们的生活中,太平洋西南航空公司代表了一段岁月;当时我们做的多数事情似乎都没有准备,没有结果,只顾率性而行,想都不想第二次就为吃一顿晚饭飞七百英里。这段岁月于1978年结束。当时太平洋西南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27飞机在圣地亚哥上空撞上了一架塞斯纳172型飞机,致使一百四十四人丧生。
空难发生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原本竟然没有料到太平洋航空公司会发生这种事情。
现在我明白了,这类错误并不仅限于太平洋西南航空公司。
金塔娜两三岁时,我们会带她乘坐太平洋西南航空公司的班机,到萨克拉门托探望我母亲和父亲。当时她管这叫〃乘坐微笑〃。约翰常常用面巾纸把她说的话写下来,把它们放进他母亲给他的一个绘有图案的黑色盒子中。这个盒子,连同它里面的面巾纸,仍在我的客厅的一张桌子上。它上面画着一只美国老鹰,还有〃合众为一〃的字样。后来,他把一些她说的话用在小说《小戴切·谢伊》中。他把这些话给了戴切·谢伊的女儿凯特。凯特和她母亲在伦敦夏洛特大道的一家餐厅吃晚饭时,被爱尔兰共和军的炸弹炸死。下面是他所写的一部分:
〃你去哪里了?〃她会说,还会说〃早晨哪里去了?〃他把它们全都记下来,把它们塞进一个秘密的小抽屉,小抽屉所属的枫木桌子是巴里·斯塔金送给他和李当结婚礼物的……凯特穿着格子尼校服。凯特会把洗澡说成〃沐浴〃,把幼儿园试验用到的蝴蝶说成〃蝶蝴〃。凯特七岁的时候写下了她的第一首诗:〃我就要嫁给/一个男孩,叫哈里/他骑马/劝夫妻分离。〃
破碎先生在抽屉中。凯特用破碎先生来称呼恐惧、死亡和未知的事物。她会说,我做了一个有关破碎先生的噩梦。别让破碎先生抓到我。如果破碎先生来了,我将会爬上篱笆,不会让他把我带走……他在寻思破碎先生在凯特死之前有没有时间去吓唬她。
现在我明白了1982年《小戴切·谢伊》出版时我没能明白的事情:这是一本有关悲哀的小说。这本书接下来会提到戴切·谢伊正在经历一种病理学的丧亲反应。病征如下:他总是想着凯特去世的那一刻。他一次又一次地重演那个场景,仿佛重演它能够得到一个不同的结局:夏洛特大道的餐馆,苦苣色拉,凯特的淡紫色帆布鞋,炸弹,点心推车中的凯特的头。他不停地用同一个问题折磨他的前妻,也就是凯特的母亲:炸弹爆炸时,你为什么会在女厕所呢?最后,她告诉他:
你从来不把我当凯特的母亲,但她确实是我养大的。她第一次来月经的时候,是我照顾她的。我记得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她管我的卧房叫做她温馨的第二房间,管意大利面条叫做细面条,管到那座房子的人叫做喂。她说你去了哪里,说早晨哪里去了,还说你这个婊子养的告诉塞耶说你想找个人来记住她。她告诉我她怀孕了,她说那是一次意外,她想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走进了女厕所,因为我知道我会哭起来,我不想在她面前哭,我想把眼泪擦干,以便能理智地对待,然后我听到爆炸声,当我冲出去的时候,她的身体已经一部分在果子冻里面,一部分在大街上。而你,你这个婊子养的,你想找个人来记住她。
我相信约翰会说《小戴切·谢伊》是一本关于信仰的小说。当他开始创作这本小说时,他已经知道这本小说最后的一句话将会是什么,那不仅是小说最后的一句话,也是戴切·谢伊举枪自杀之前最后想到的一句话:〃我信凯特。我信上帝。〃我信上帝。天主教教义答问的第一句话。
这句话是关于信仰,还是关于悲哀呢?
信仰和悲哀是一回事吗?
在我们游泳,看《点呼》,到摩通餐厅吃晚饭的那个夏天,我们异乎寻常地依赖对方吗?
或者我们只是异乎寻常地幸运?
如果我孤单一人,他会乘坐微笑回来找我吗?
他会说在俄尼餐厅订了位子吗?
太平洋西南航空公司和那个微笑已经不存在了,前者卖给了美国航空公司,后者被油漆涂掉了。
俄尼餐厅已经不存在了,但希区柯克曾经将它虚构出来,它在《迷魂记》中短暂地出现过。詹姆斯·斯图亚特第一次见到金·诺瓦克就是在俄尼餐厅。后来她在圣胡安巴蒂斯塔San
Juan Bautista,即圣徒洗礼者约翰,该教堂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始建于1797年。教堂的钟楼(也是虚构的效果)坠落身亡。
我们结婚的地方正是圣胡安巴蒂斯塔。
当时是一月的下午,花儿在101高速公路旁边的果园盛放。
当时101高速公路旁边仍有果园。
不。人们只有在倒车的时候才会擦伤车身。101高速公路旁边果园中盛放的花儿不是正确的道路。
事故发生之后好几个星期,我反复对自己念诵《露丝·埃尔默》那首诗的最后两句,努力让自己停留在正确的道路(也是一条狭窄的路,一条不会回到过去的路)上。那是瓦尔特·塞维奇·兰多尔Walter
Savage
Landor(1775…1864),英国诗人、作家。1806年写的悼亡诗,哀悼埃尔默勋爵年方二十却死于加尔各答的女儿。自我在伯克利念大学以来,我一直没想起过《露丝·埃尔默》,但此刻我想起的不仅是这首诗,还有大部分我在课堂上听到的对它的分析。上那节课的老师曾经说,《露丝·埃尔默》之所以能够打动人心,是因为前四句对死者大加吹捧从而毫无意义的赞扬(〃啊,出身尊贵的家族/啊,相貌美艳/品行端正,举止优雅/露丝·埃尔默,这全都是你的优点〃),通过最后两句〃备极哀怨的名言〃转变成一种突然的、甚至令人震撼的解脱。后两句非但点名了哀悼的地位,还指出了它的极限:〃我将献给你/一个夜晚的回忆和叹息。〃
〃一个夜晚的回忆和叹息,〃我记得那个老师重复说,〃一个夜晚。一个夜晚。本来可以说所有的夜晚,但他没有说所有的夜晚,他说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