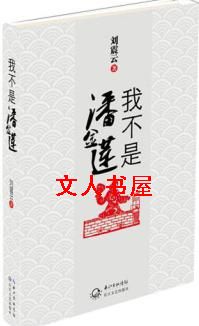我不要你死于一事无成:给女儿的17封告别信-第2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第二天上午,我们乘坐公交车前往波勒霍姆里,即巴格兰省的首府。阿富汗公交车上的秩序非常混乱,哈米德和我爬上车后,等待其他乘客向亲戚朋友做最后的告别,或是与司机理论,或是往本已装载过度的车顶塞一件行李。车外,有一名街头小贩在兜售当地奶酪特产,那也是许多阿富汗人最喜欢的野炊菜品。和大多数孕妇一样,我也很喜欢吃这种奶酪,于是就让哈米德去买。他真是个好丈夫,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等他买回来后,车子刚好启动。他气喘吁吁,手里拿着一小块白色奶酪。我尝了尝,味道很淡,有嚼劲,与莫泽雷勒干酪无异。但是,很有骑士风度的他匆匆忙忙冲出去给妻子买奶酪的时候,竟然忘了买葡萄干——通常,这种奶酪配上葡萄干才能带出味儿来。尽管我并不是不感激,但多少有些失望。车子快要开了,根本没时间回去再买。我正要决定将就着吃的时候,被车窗上的一阵敲打吓住了。我转过脸,以为这一定是塔利班来威胁乘客了。但是,出乎意料的是,我遇上了一双慈祥的眼睛,是那个卖奶酪的老人。
“给你,妹子,”说完他便递给我一个小塑料袋,“你丈夫忘了买葡萄干。”换成是塔利班,我们早就被当成罪犯,而在这里,我们遇到的是客气、礼貌和尊重。这是人类最普通的一个善举,不多不少,但它就是令人出乎意料地感动,我的双眼不禁流出了眼泪。
经历了这件事,我心情也好了许多,欣赏起了沿途的风景。山峰开始褪去雪夹克,斜坡上新长出了草儿和花儿。此情此景,让我看到了阿富汗的希望。无论塔利班是多么冷酷无情,我坚信,总有一天,它也会像雪一样融化。
在波勒霍姆里,我们投宿哈米德姑妈家。姑妈姑父曾经来我家商谈哈米德跟我的婚事,我非常喜欢他们。当然,我也清醒地知道,做个他们心目中满意的媳妇不容易。邻居们都知道哈米德家给了我两万美元的彩礼,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他们一定很想见见我,看看我值不值这个价。于我,这是个很高的期望,毕竟,几个月来我承受了不知多少压力,又奔波了好几个星期,再过几个星期就要生孩子,我不禁觉得很难达到他们的期望。
哈米德的姑妈人很好,她完全理解我的感受,还准备让我好好沐浴。所谓的沐浴,就是将一桶水放到火上烧热,然后拿来洗澡。经历了一番舟车劳顿之后,你筋疲力尽,汗水灰尘满身,这时,你用搪瓷瓢从一个盛得满满的水桶内舀出一瓢瓢烧得热乎乎的雪水,淋到头上来,那种感觉和在五星级酒店做豪华水疗的享受没差别!一瓢瓢的热水浇下来,冲走了我长期以来在塔利班统治之下的压力、焦虑和污秽。几天之前,刚离开喀布尔的时候,他们甚至把我看得连狗都不如。此刻,每一瓢水下来,我仿佛渐渐恢复了人性,也捡回了自我价值,现在我唯一担心的是邻居怎么看我。细心敏感的我也发现,塔利班的高压统治反而让我内心坚强了许多,而这一点也是我刚刚才意识到的。我不再是之前那个年轻天真的新娘,而是经受过激进主义暴政的妻子、跋涉过千山万水的孕妇、充满理想和希望的女人,终于在脚下发现了成熟的土壤。
然而,当我一出来,看到他们脸上的那副神情就知道,他们觉得哈米德的那两万美元花得真不值。他们甚至懒得掩饰弯起的眉毛和撅起的嘴唇,我还能想象得到他们回到自己家之后会说怎么我。
只剩下我们俩的时候,哈米德笑了。他轻轻地吻了吻我的前额,叫我不要在意他们说什么想什么。我们拥有彼此,这才是最重要的。
休息一晚之后,我们接着赶路往北方走。到了塔拉坎,我们不得不租一辆吉普车,因为冬雪化水之后形成洪水,冲毁了我们的下一站必经之路——启山的部分道路。从那里开始,我们要改乘货车回到巴达赫尚省的首府法扎巴德,这不是我所希望听到的消息。坐货车在阿富汗是最基本的交通方式,通常是库奇族人(阿富汗的一支游牧民族)的专利。我让哈米德去找轿车,找了好久也没找到。
看到货车之后我真的一点儿都不想上去。再怎么说,我也是出身高贵,受过教育的都市女性,而那辆货车通常是用来载山羊的。那一天,车上堆满了一袋袋的大米。如果坐这辆车逃离喀布尔,我是一百个愿意,但此刻我已逃离他们的魔掌,自信心也开始恢复了,真的放不下这个面子。哈米德给我下了最后通牒:这是最后一辆开往法扎巴德的车子,如果再不走,就要滞留在启山。我没得选择,只能放下自尊,上了车。蒙面长袍我也穿了,为的是保暖,还可以挡灰尘。尽管有了这个做掩护,在接下来的4个小时里我还是把头低下来,靠近大腿,生怕遇到熟人认出我。我偶尔抬头看看风景,可是搭乘山羊货车担心被人看到的羞愧心理始终挥之不去,所以又赶紧把头低下来。
路,陡峭崎岖得出奇。就在我们往最危险的一段路卡拉克马爬坡的时候,车子突然失去了动力,停了下来。由于在下坡路段刹车过于频繁,刹车片发热,失灵了。这时货车开始倒退,往身后的河流倒去,我不得不抬起头来观望,我们的车子越来越快的,朝湍急的雪水洪流滑去。这时,我脑子里闪过一幅画面:冰冷的雪水浸透蒙面长袍,很快将我拽入急流,撞上岩石。
我吓得闭上了双眼,手指深深插入米袋子,以求保护。货车的轮胎向后滑,想往前爬上光滑的石子路面,却怎么也抓不上力,车上的乘客和司机随着车子蹦跳摇晃,发出阵阵尖叫。突然,车子在离岸边几米远的地方停住了。我转过头去看哈米德,他的手被我攥得快要残废了。我们相视而笑,终于舒了一口气。司机按下喇叭,仿佛是在庆祝,乘客们欢呼“荣耀归给真主”。从货车下来之后,我双膝发软,但高兴的是又可以走路了,经历了生死边缘之后,什么尴尬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刹车出问题,再加上天色也暗了下来,所以车子哪里都不去了。因为快到法扎巴德,我再也不想回到货车上去,而是沿着河边的石头走来走去,尽情地欣赏着风景。我已经逃离了塔利班的统治,不再有遭鞭打的威胁,也不用担心哈米德遭到迫害,如果我愿意,也可以不用穿蒙面长袍。那一晚,我们就在货车上过夜。我也不再担心被熟人看到,明天就可以到达法扎巴德。我在故乡的夜空下安然睡着了。
亲爱的舒拉和莎哈扎德:
还是个农村小姑娘的时候,我渴望能够上学。那时我觉得自己脏兮兮的,不讲卫生。衣服也不多,脚穿的总是惠灵顿长靴,围着的红色大围巾,老是拖在地上,鼻子里还挂着鼻涕。
现在,看到你们姐妹俩穿着时尚衣服,梳着时髦发型,我真的很开心。你们是在首都喀布尔长大的,是地地道道的城市女孩。如果你们看到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的那个样子,一定会吓一跳。
我知道,在那段我带你们回到巴达赫尚省住的日子里,你们觉得很难适应,因为村里的孩子们和你们大不相同。
但是,女儿们呀,我不想让你们成为势利小人,或者说看不起别人的人。我们来自穷苦的乡下地方,比这些衣衫褴褛的孩子们好不到哪里去。万一哪天形势不好,你们俩都有可能回到那里过穷苦日子呢。
请记住,如果你们需要回家,你们的家乡将永远张开双臂随时欢迎你们回去。
挚爱你们的妈妈
两个女儿诞生
1998~2001年
哈米德和我很快在法扎巴德安顿下来。能和家人亲戚团聚,我无比高兴。我同父异母的姐妹们,全部嫁给了当地人,都留在了本省,许多同父异母的兄弟也都留下来躲避战争。多少年没见面了,如今再次相逢,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我的姐妹甚至都不知道我已经结婚怀孕了。
法扎巴德再次成了我的避难所,就像童年的时候一样。当时,为躲避游击队员,我也是到这里逃难。我几乎都快忘了这是个漂亮迷人的城市:海拔高,空气清新,一条碧绿的河流从城中贯穿而过。这里还有古老的集市,商店里出售的商品应有尽有。
我们租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哈米德可以继续开展金融业务,他还在大学里兼职。我也可以好好休整,等待生产。和许多初为人母的女人一样,我也很紧张,不知道生孩子的时候会怎么样,只知道很痛。法扎巴德的医院卫生条件很差劲,所以我宁愿在家里生,也不愿意躺在肮脏的公共病房里,病床外形怪怪的,铺的垫子薄如纸片。
我的第一个女儿于1998年7月8日出生。那天我应邀到哈米德的一个亲戚家吃午饭,到了那里后,整个人非常不舒服,食物碰都没碰。下午3点钟,我回到家,到了晚上10点,小天使就诞生了。
生产过程短暂而艰难。接生的是一个女性医生朋友,没有给我采取任何止疼措施。在我们的文化里,大家都希望女人生的第一个孩子是儿子,可我并不在意婴儿的性别,只要健康就好。婴儿生下来之后,先被送去洗身子,穿上襁褓。没有人告诉我孩子的性别是男是女。
接着,哈米德被允许进入产房。在伊斯兰教社会里,男人通常不能出现在接生现场。他来到床边,抚摸着我的头发,擦去我前额的汗水,轻声说:“是个女儿,我们有女儿啦。”他一点儿都不介意我没给他生个儿子。婴儿4。5公斤重,完全符合标准,我们两口子乐得合不拢嘴。她跟哈米德一样,长着乌黑浓密的头发。
出生后的几天里,我跟所有其他初为人母的女性一样,拼命学习如何母乳喂养,如何度过一个个疲劳的无眠夜晚。为此,我还真费了不少心思。看着她微小的体型,我恳切地祷告,希望她所生活的世界、生活的阿富汗能够越来越好,不要像其他女人一样遭人歧视和厌恶。将她抱在怀里,贴着乳防,我能感觉到她就是我的整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什么都不重要,唯有她。我自己的穿着,外表,微不足道的自私欲望都算不了什么了。
我要和家人理论,让他们尽快允许我给孩子母乳喂养。在巴达赫尚省,孩子出生后满三天才可以开始母乳喂养,因为有这么一种观念,认为在最初的几天里,母乳中含有一些对婴儿不好的成分。由于我在大学里学过医学,知道母乳喂养的好处,其实在最初的几个小时内,母乳里所含的初乳是婴儿的免疫系统不可或缺的物质。
刚生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如果没有食物,婴儿就会变得虚弱、畏寒。如果母亲不直接给孩子喂奶,母亲就会增加感染乳腺炎等疾病的风险,甚至导致她将来不能如期产奶。这种不立即喂奶的观念也是导致我们省份产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居高不下的另一个原因。
为了给婴儿喂奶,我要跟姐妹们讲道理。她们想竭力阻止我,大声警告我说,如果这么早喂奶,就是在害婴儿。我则向她们解释说,这是为了婴儿好,可她们就是听不进去,带着谴责的眼神看我,好像我是个坏母亲。在她们眼里,传统和她们听到的所谓经验远比她们的妹妹在大学里学到的知识重要。
但是,在其他方面我的姐妹们待我很好,要我保持暖和,裹好毯子(虽然那时正值7月,太阳炙热),还给我煮最好吃的饭菜,好让我尽快恢复体力,还不让我做家务。有了婴儿我当然很高兴,可是一想到死去的母亲,我心里泛起一阵苦楚。多么希望她还健在,看到自己的外孙女出生啊。那样,她就会知道另一个我来到了这个世上,另一个坚强有决心的女人出生了。
生完女儿后的第6天,哈米德和我举办一场大型聚会庆祝。我们邀请了镇上一半的人来,播放起音乐,还拍了录像,婚礼时不被允许做的事我们这会儿全补上了。在某种程度上,这次聚会就是我们的婚礼,这纯粹是庆祝我们夫妻俩的恩爱和小家伙的诞生的。
我决定再去教书,于是发出了广告,自称是一名英语老师,然后在镇中心租了间房子做学校。不到一个月,我就招收了300名女学生,有年轻女孩,有医生,有大学生,还有老师。为了弥补自己的教师培训时间不长这一缺点,我特地从国外订购音频视频资料。这些东西在法扎巴德从来没用过,我的学校也因此赢得了现代、专业的美誉。真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运气,收入不错,月入600美元,干的还是自己喜欢的事业。我还把婴儿带到课堂上去,学生看了喜欢得不得了,有些还跟我成了亲密的朋友。这是我人生有史以来第一次经历的真正意义上的独立。
我依然每天穿着蒙面长袍,奇怪的是现在并不介意穿。巴达赫尚省没有塔利班的硬性规定,也没有法律强迫我一定要穿。然而,这里的大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