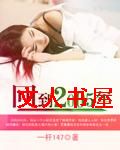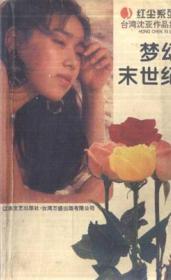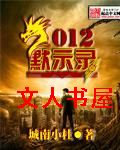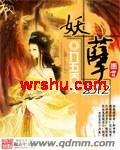20世纪最伟大的心理学实验-第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海―avid Rosenhan)假扮精神病人,探讨精神疾病的诊断过程。在今天看来,这个实验宛如一出异想天开的黑色喜剧。时至今日,我们理当发展出更客观完备的标准用于诊断这些“疾病”。那么若再进行一次罗森汉的实验,结果会有不同吗?即使欠缺充分明确的病原学或病理学基础,我们是否仍能界定异常和正常?心理学有两项主要的研究方法,一是客观的统计归纳,二是主观的演绎诠释,这些方法算得上是科学吗?所谓科学,从某些方面看,不也是研究者的主观诠释?
早在19世纪末,现代心理学之父冯特(Wilhelm Wundt)设立了世界上第一所心理学实验室,实验室配备了各式各样的科学仪器,目的是以实证定量的方式研究心理学,科学的心理学自此诞生。然而种种实验显示,心理学这门学科先天不良,只有虚幻空泛的形体与松散连结的四肢。这个怪物在以后的一百多年间不断成长,时至今日,已经长成什么样子了?本书虽然不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但读者可以通过阅读书中这些实验,而对上述问题有一番深刻体会。
综观本书,读者可以发现,心理学研究日益偏重生物层面,这俨然是大势所趋。我们已经了解了神经元的内部机制,也知道基因如何通过影响蛋白质的组成,从而决定生理特征与思维能力。我们不仅能解释思想形成的过程与机制,也知道思想如何引发行为。
但人为何有思想?为何受特定思想左右?为何会记住或遗忘?这些记忆有何意义?对人生有何影响?对于这些问题,我们还没有令人满意的解释。换言之,我们可以用生理学观点界定记忆的本质,但这些本质最终会以何种形式呈现,带有何种意义,仍由个体所主导决定。
对我来说,描述这些实验等于是科学与艺术的写作练习。我不仅得知实验结果,也借此了解这些研究者的人格特质及因人而异的研究动机,以及实验过程中经历了哪些曲折才获得最终结果。我也看到这些资料在当时激起的反响,对后代的启发以及是否获得了应有的重视与应用。总之,本书让我得以回顾过去,思索未来。21世纪的心理学会有什么样的发展?我心中已略有概念。巴甫洛夫摇着铃,外科医师继续深入探究复杂的脑部。
现在,请翻到下一页!
第1章 打开斯金纳箱斯金纳与新行为主义
引言
斯金纳是美国新行为主义的代表人物。放眼20世纪,招致最多抨击与非议的心理学家,非他莫属。他的动物实验不仅广为人知,也让世人见识到“报酬”(rewards)与“强化”(reinforcements)对于塑造行为的重大影响,同时奠定了他在心理学界的领导地位。
1904年3月20日,斯金纳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东北部的一个车站小镇。他从小就喜爱发明创造,富有冒险精神。15岁时,斯金纳曾与几个小伙伴驾独木舟沿河而下,漂流300英里。他还试制过简易滑翔机,曾把一台废锅炉改造成一门蒸汽炮,把土豆和萝卜当炮弹射到邻居的屋顶上。
斯金纳在实验中设计出研究操作性条件反射的实验装置——“斯金纳箱”,巧妙地安排食物、控制杆等刺激,使老鼠受到情境暗示,进而出现我们原本认为是自主自发的反应。斯金纳因而认为,人类向来珍视的“自由意志”其实并不存在。他主张通过正强化作用来训练人类或动物完成指定的任务,即所谓的“操作性条件反射”。他毕生致力于钻研操作性条件反射理论,务求其周延完备。
你也许听过“斯金纳”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好像注定要遭人厌恶。叫这个名字的人仿佛生性就该残忍,他一手拿刀,一手抓鱼,毫不留情地刮去鱼鳞,只见鱼身几近透明,内脏依稀可见,他顺手把鱼丢入滚烫的油锅,热油四溅,噼啪作响。
现实中的斯金纳,满头花白乱发,对心理学极度狂热。据说他曾将还是婴儿的女儿养在实验箱里,训练她学会各种技能,好像马戏团里训练海豹用鼻子顶球。斯金纳一心想“塑造”人类行为,这与纳粹所为颇有异曲同工之处。他以齿轮、箱子、按钮组成实验装置,依据严密准则给予强化物,操控动物行为。人性在他的手中化为乌有。
我曾调查过20位具有本科学位的民众,请他们说出对“斯金纳”的看法。其中有15人形容他“恶毒”、“邪恶”。10人提到他把女儿养在箱子里的实验,虽然没有人知道小女孩的名字,但他们却信誓旦旦地说,女孩因父亲的实验而身心受创,后来她在旅馆房间以手枪和绳索结束了生命,细节就不清楚了。我们知道,女孩名叫德博拉(Deborah),斯金纳想训练她,所以把她关在箱子里整整两年。在这个狭窄的方形空间里,装设有响铃、食物托盘及各式机关,斯金纳还会适时地给予惩罚与奖赏。他站在网架后观察女孩的进步。女孩长大后饱受精神疾病的折磨,31岁那年,她向法庭控告父亲虐待,但败诉了,最后她在蒙大拿州比灵斯市一家保龄球馆举枪自尽。枪声响起,似乎宣告行为主义的全盛时代就此结束,此后的批评质疑始终未见消退。
1960年,斯金纳接受传记作家伊凡斯(Richard I。 Evans)访问时,坦承自己在社会改造方面的成就与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不无关联,且可能成为独裁者的工具。我们还是忘记他这样的人比较好,但我们做不到。1971年,《时代》(Time)杂志将斯金纳誉为当代最具影响力且尚存于世的心理学家;1975年,一项研究称他为美国最著名的科学家。时至今日,他的实验仍受到诺贝尔心理学奖得主的推崇,他的发现依然适用。他到底做了什么?
我在搜寻引擎中输入关键字“斯金纳”,成千上万的资料出现在眼前。有位愤怒的父亲谴责斯金纳害死了一名无辜儿童;某个网站首页以骷髅图片搭配俄裔美国女作家兰德(Ayn Rand)的言论,“斯金纳极度憎恶人类的心智与道德,此种意念偏执强烈,终至自取灭亡,到头来只剩下灰烬与若干呛鼻的煤块”。一句“德博拉,我们的心与你同在”算是纪念已于20世纪80年代过世的德博拉。还有一行红色小字写着:“斯金纳之女德博拉的相关资料,请点此处。”我照做了,看到一张棕发中年妇女的照片,图释写着:“我是德博拉,谣传说我已经自杀身亡,其实我还活着。斯金纳的箱子并不像你们所看到的那样,我父亲也不是你们所想的那样,他是位聪明的心理学家,也是位慈爱的父亲。我只想破除那些不实的传说。”
种种传说、故事,到底有几分真实性?也许要想了解斯金纳的实验,关键在于能否详查细究,我们不能把事实与争议混为一谈。心理学家兼史学家米尔斯(John A。 Mills)曾说:“斯金纳是个神秘人物,他被一层层的谜题包裹着。”
我决定循序渐进,一步一步解密斯金纳。
对心理学无比失望的斯金纳
斯金纳生于1904年,这点毋庸置疑。除此之外,他简直集所有矛盾于一身。他是美国行为主义的先锋,个性严谨,工作时书桌上必定一片混乱,休息的地方是一间明亮的黄色的小卧室。他谈到自己的生平时说:“许多平凡无奇的琐事,却造就了重大改变,实在神奇……我从不认为生命在我掌控之中。”但他在著述中常自比为上帝,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人类的救世主”。
在哈佛大学念书时,斯金纳认识了一位女孩,后来成为了他的妻子。每到星期五晚上,他们会开着黑色敞篷车,前往缅因州蒙希根岛上的海鸥湖,沿路听着爵士蓝调音乐。一到湖边,两人脱掉衣服,跳入水中,让瘦削的躯体感受湖水的拍抚,呼吸着夜晚的冰凉空气,仰望夜空中皎洁的明月。我还在图书馆地下室找到一份布满灰尘的文献,里头说斯金纳每次训练鸽子后,会将它们放到笼子外,让鸽子站在他手上,用食指轻抚鸽子的头。
1928年斯金纳进入哈佛大学心理学研究所。不过他最初的志向却是成为小说家。他在家中阁楼闭关18个月,致力于写作。他为何从写作转为研究强化作用,虽然确切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他提到过他23岁时曾在《纽约时报杂志》(New York Times Magazine)上读到英国科幻小说大师威尔斯(H。 G。Wells)的文章,威尔斯在文中写道,如果在俄国科学家巴甫洛夫与美国作家萧伯纳之间只能救一人,他会选择前者,因为科学比艺术更能拯救世界。
当时的世界确实需要拯救。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将近10年,越来越多经历残酷战争的退役军人身心受创,深受幻觉与抑郁折磨,精神病院人满为患,迫切需要其他新的治疗方式,舒解这一窘境。当时精神分析风靡一时,治疗方式是让精神病患躺在皮革沙发上,追忆过往,挖掘陈年琐事。那时的心理学界由弗洛伊德称霸,而学识地位崇高的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William James)写的《宗教经验的类型》(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旨在探讨内在精神状态,书中完全没有任何公式。斯金纳初入心理学界时,这门学问与数学全然无关,与哲学相通之处多过生理学。当时的心理学首要回答的问题应是:人类具有何种本质,让我们意识清醒时能观看、感受、思考;沉睡时暂停一切,死后便万事皆空了?
斯金纳最先接触到的心理学,就等于内省'1'、唯心论的同义词。这位削瘦的年轻人,顶着头盔般夸张的油亮卷发,湛蓝的双眼好像景泰蓝瓷盘碎片。他所写的文章透露出想改变世界的愿望。他认为世间万物不只要用心去感受,更要亲手去碰触。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山雨欲来,置身这样一个时代,斯金纳也许已“感受”到,若想改变心理学界、产生重大的影响,必须采取行动。他一定会抗议我用“感受”这种虚幻的词汇来形容他。自此他刻意摒弃一切“虚无”的事物。他改修生物学家霍格兰(Hudson Hoagland)的生理学课程,研究青蛙的反射作用。他用针刺青蛙光滑的皮肤,测试青蛙腿部抽搐与跳跃的动作。尽管弄得双手粘腻,但他却兴致勃勃。
“斯金纳箱”的诞生
斯金纳刚进哈佛大学不久,便参与了一场在爱默森楼举行的心理学研讨会。现场他看到各式各样的仪器、锡片、锯子及放在锡制盒子里的钉子、螺帽,一时技痒,打算做一件伟大的杰作。斯金纳向来手巧,善于操弄工具,且以精准闻名。他在一家小型工厂中,以废弃的电线、生锈的铁钉、发黑的金属片,打造出那个家喻户晓的箱子(如图1—1所示)。
图1—1 斯金纳箱
斯金纳预料到他这项作品会对美国心理学界造成巨大的冲击吗?他是将心中构想付诸实现,还是任凭灵感恣意发挥?最后,当他看到这个由锡片和线圈组成的作品时,自己都忍不住惊叹!这个箱子以压缩空气为运转动力,由各式零件齿轮组成机械装置,可依实验者设定,释放出特定的奖惩物。尽管这个箱子看似平淡无奇,但很快就成为了众所瞩目的焦点。此时,斯金纳说道:“(我)心中迸发出莫名的兴奋,这里的每样东西都让我联想到更多崭新可行的研究主题。”
深夜里,斯金纳阅读着两位心理学大师的著作,俄国心理学家巴甫洛夫对他影响最为深远,创立行为学派的美国心理学家华生就稍显逊色了,但仍有其重要性。巴甫洛夫以研究为志向,几乎以实验室为家,他偏爱以金丝雀为被试,投入多年时间研究唾液腺,他发现唾液腺反应可能会受铃声控制。斯金纳对此极感兴趣,不过他想研究的不只是这层薄膜,而是整个有机体。唾液腺还不够迷人。
巴甫洛夫的发现称为经典条件反射(classical conditioning),简言之,即动物既有的本能反应,如:眨眼、惊吓、流口水等,可用人为的方式加以控制,使其伴随新刺激出现。在巴甫洛夫著名的实验中,铃声是新刺激,狗听到铃声,就想到食物,所以一听到铃声就会流口水(如图1—2所示)。时至今日,我们或许不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但这项发现当年广受各界瞩目,讨论的热烈程度不逊于原子融合、太阳位置恒定等重大科学突破。在此之前,人类从不知道,许多我们认为受心智主导的反应其实与生理学有着密切关系,我们以前总以为与生俱来的动物本能无法改变,事实上却具有高度可塑性。巴甫洛夫流口水的狗,颠覆了长久以来被你我视为理所当然的两个观念。
图1—2 巴甫洛夫的经典条件反射实验
斯金纳在房中沉思,箱子里空空荡荡,目前名声还未传开,或者说还没那么恶名昭彰。哈佛校园里松鼠随处可见,斯金纳看着松鼠,心想既然可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