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我们都不曾忘记-第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一生只有七天。看似漫长的人生其实很短,它正好是一个礼拜的过程,爱我们的人,已经用祈祷铺好了你要经过的每一条路。
那么,揣好我们的爱,上路吧。
请传递给下一位
◎孙道荣
一场大雪,将我们困在了沪浙皖高速上。
七个多小时过去了,车龙动都没动一下。又饥又寒,我们一家三口,蜷缩在小车里。为了省油,车早熄了火。
儿子又喊饿了。还是早上吃过一点早饭,我们也饿,可是,车上仅有的几盒饼干已经吃完了,只剩下几袋方便面和冰冷的矿泉水。妻子只能无力地安慰儿子。
我下车看了看,车龙前不见首,后不见尾。路面上的积雪已经有十几厘米厚,而且结了冰,踩在上面,很滑,根本不能行走。高速路外,完全被大雪覆盖,甚至连个村庄都看不见。儿子在车里嚷,会不会是“后天”降临了啊。《后天》是一部美国电影,里面有很恐怖的场面。
我回到车上,打开收音机,调到交通频道,收音机在反复播放:因为骤然而至的大雪,高速都已经封道了。我们这条沪浙皖高速也封了。政府正在组织抢修。
突然,前面的小车车门打开了,走下来一个中年男人,只见他扶着车子走到车头,接过一个袋子,又扶着车子走到车尾,在朝我打手势。
我下了车。中年男人大声喊,这是前面送过来的盒饭,你帮忙往后传一下。
我小心翼翼扶着车子,挪到车头,伸出手,将他手里的袋子接了过来。疑惑地问他,怎么回事啊?
他说,我也不知道,袋子里是盒饭,是我前面的车子传过来的。
听他一说,我抬头往前一看,果然前面每辆车子边都站着一个人,在摸索着传递。中年男人大声说,可能是有人将盒饭送上了高速,路太滑,没法一辆辆送,才想出让大家互相传递的办法吧。
我明白了。扶着车子,我慢慢挪到车尾,喊我后面的驾驶员。后面是辆大货车。我将中年男人的话重复了一遍,请他将盒饭往后传递。
又一袋盒饭传了过来。中年男人问我,车上有老人和孩子吗?有的话,先拿一份盒饭给他。我感激地冲他笑笑。
就这样,大雪纷飞中,一袋袋盒饭从前方传来,又从我的手上,传到后面车上的人。几次听到惊叫声。路太滑了,虽然扶着车子,一不小心,还是会摔倒。雪飘落在每个人的头上,脸上,身上。我前面的人,后面的人,都像个雪人。
终于,后面的货车司机告诉我,不用再传了。后面的人,都已经接到盒饭了。
这一袋盒饭,是我和妻子的。坐在车里,打开盒饭,还飘着温温的热气。
几个小时后,高速终于恢复了通车,长长的车龙在缓慢地向前移动,每一辆车,都打开了双跳灯,温暖的橙色,在冰天雪地的高速上,汇成了一股暖流。
我们缓慢而温暖地,走在回家的路上。
惟有相思最难忘
你是我的朱砂
◎毕淑敏
我上学的第一任老师,是位美丽的女子,那时候她还没有孩子。没有孩子的女子,对别人家的孩子,要么是厌烦的,要么,是喜欢的。我的老师,是喜欢的那一种。
喜欢孩子的人,要么是特别的和蔼,要么是特别的严厉。我的老师,是两手都硬的那一种。
我1959年就读于北京海淀区建设小学,入一年级一班,班主任是白玉琴老师。一天上语文课,白老师讲“小猫钓鱼”。她把课文念完之后,提问大家谁能复述一遍?这对刚刚上学的我们来说,有难度,课堂里一时静若幽谷。我那时梳着齐眉娃娃头,一缕湿发遮住了眼帘。汗水淋淋的我顺手捋了捋头发,白老师立刻大声说,好啊,毕淑敏愿意来回答这个问题,请起立。我魂飞胆战,当下想以后哪怕是头发把眼珠刺瞎了,也不再捋头发。我恍若慢镜头一样起身,企图拖延时间以想它法。也许因为我动作太慢,白老师在这个当儿另起了主意。她说,毕淑敏站到讲台上来,面向大家复述课文。
天啊!
没有任何法子对抗,我只好拖着双腿,像老爷爷一样挪向讲台。咬牙切齿痛下决心,以后剃成个秃瓢,永不留发。从课桌到讲台的那几步,是我七年人生中最漫长的荆棘之旅。然而无论怎样蹒跚,总有到了尽头的那一刻,我只好战战兢兢地开始了回答。
如何下的课,全然忘却。以上是我开蒙之后记忆最深的一件事。
开蒙,古时指儿童入书塾接受启蒙教育,现如今泛指儿童开始上学识字。我觉得像读书识字这类属于心智萌发的事件,应该有一个庄严的启动仪式,[小说网·。。]让小小的心灵里,刻骨铭心于这一瞬的惊诧和感动。可惜现在的孩童,多半很早就稀里糊涂乱七八糟地开始识字了。或许是多嘴多舌随心所欲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或许是望子成龙崇尚笨鸟先飞的父母,在孩童猝不及防的时候,就轻易地开始教他们识字。闹得孩子们对于字,就像少年面对随意暴露身姿的异性,难以建立起斩钉截铁的敬畏,淡薄了欣喜若狂的爱惜。甚者如那没有成年就发动的早恋,在初春就消耗了夏天的炎热。
早年的开蒙礼,也称“破蒙”。“蒙”是“蒙昧”之意,指未开化状态。一个带有裂帛之声的“破”字,仿佛不识字是一顶坚硬的钢铁帐篷,压抑幽暗,需一柄寒剑横空刺穿,透进万千气象。据说开蒙礼上,要由礼官为即将入学的孩子们,在额头点一粒大大的朱砂眼。点眼的具体位置是在鼻根上方印堂的中央,名曰“开智”。象征着这孩子从此脱离了茫昧的混沌,睁开了天眼。朱砂色艳如血,闪金属般的光泽,美艳无比且触目惊心。之后是孩童学写“人”字、谢师恩、开笔石上练字,初背三字经……破蒙如同破晓,人生从此曙光乍现。
为什么要用朱砂点化出一只新眼?朱砂原是一味药,能镇惊安神祛风避邪。这第三只眼,到底是个什么性质的器官呢?倘取一把解剖刀,从人的额头探进脑腹,深入两寸,会见到一个貌似松果的东西,重约三两,现代医学就称它为松果体。松果体是重要的内分泌器官,更有人说它就是人类灵魂居住的地方。有研究认为,松果体内有退化了的视网膜,具有呈像功能。即使闭上双目,它也仍在活动,仿佛液晶电视的屏幕,显现奇异风景。
古人最初设计开蒙礼的时候,为什么选了猩红的朱砂和神秘的额头中央?或许指的是人们识得了文字,从此可以阅读古今中外圣贤之言,便为灵魂塑造了一只穿云破雾洞察秋毫的心眼。于是它身居要位,统摄周身。
“小猫钓鱼”后,我听白老师对别人说,他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好记性的孩子,居然把整篇课文复述得几乎一字不差。几十年后我重回母校,有年轻老师对我说,白校长(白老师已成为校长)至今还会说起当年的你,是多么聪慧……
时至今日,我常在想,自己并不聪明,那一日的捋发,看似偶然,也许是心中的蠢动,跃跃欲试使然。细心的白老师看穿了一个畏葸的女孩乔装打扮后的渴望,她温暖地推动了孩子的尝试。老师的鼓励,让一个不自信的幼童,感觉到了被重视被喜爱的欢欣。这种获取知识的快乐,将伴随终生。
我上学时没有举行过开蒙礼,白老师就是我的朱砂。
父亲的秘密
◎周海亮
假期里,父亲和他八岁的儿子去森林里游玩。他们往密林深处不停地走,不知不觉迷了路。
四周的古树遮天蔽日,像一只巨大的笼子将他们困在中间。父亲背起疲惫的儿子,试图走出去。可是他无奈地发现,自己能够做的,只是每隔一段时间,重新回到原地。那里有一个废弃的木屋。木屋里也许住过守林员,也许住过伐木工人,现在它空着,破烂不堪,仿佛随时可能倒塌。可它毕竟是一间屋子,这给他们父子俩带来了一些安全感。
晚上他们挤在里面,生起一堆火。外面传来野兽的叫声,似乎距他们很遥远,又似乎近在咫尺。儿子呜呜地哭起来,他说我们会不会死在这里?父亲用力拍拍他的肩膀,说儿子别怕,我们会走出去的。
可是第二天,他们仍然围着木屋不停地画着圈子。让父亲稍感欣慰的是,木屋外面有一口水井,水井里面有干净的水。他小心地踩着井内壁的缝隙下去,用随身携带的军用水壶,打上一壶水。可是他们已经没有任何可吃的东西了,恐惧的乌云笼罩着他们。
第三天,父亲放弃了那种徒劳的尝试。他对儿子说,这里有木屋,有水井,这很可能是一些过路人的临时驿站。我们只要等在这里,就肯定会遇到人……你留在这里等我回来,我到附近找些吃的。儿子问附近有什么吃的?父亲就笑了,说森林里还能饿死人吗?你难道忘了野生蘑菇很有营养吗?他为儿子打上一壶水,然后一个人离开了木屋。他一边走一边回头对儿子说,守着屋子,千万不要乱走……等我回来,我们一起吃晚饭。
父亲并没有马上去寻找蘑菇。他把衣服撕成布条,系在木屋周围的树干上。系完,仔细检查一番,调整了几个布条的位置。他想如果有人经过,就会发现这些布条,再发现小屋,再发现小屋里的他们,并将他们带出森林。他想这可能是他们唯一的机会了,他不敢有丝毫马虎。
那天父亲很晚才回来,他拣回了一小把蘑菇。虽然仍然走不出去,仍然没人发现他们,可是有了蘑菇,他们就有了活下去的希望。儿子问这蘑菇不会有毒吧?父亲说不会……在走出去之前,我们天天喝鲜蘑菇汤。儿子问这附近蘑菇多吗?父亲说不多,也不少。儿子说明天我也去拣。父亲说不行,你得守在这里,万一有人经过怎么办?我们的目的是走出森林,不是在这里吃蘑菇宴。父亲朝儿子做了一个鬼脸,儿子发现父亲的脸,有些浮肿。
父亲出去的时间一天比一天长,拣回的蘑菇却一天比一天少。每一次回来,他都是筋疲力尽,脸色蜡黄,像大病初愈的样子。儿子问怎么了?父亲说没事,有些累。儿子害怕地哭起来,他说爸爸,我们是不是真的走不出去了?父亲说不会的,只要我们坚持住,就会有人发现我们……
终于有人经过。是一位猎人。是父亲的布条把他引到了小屋。猎人把他们带出森林,他们再一次回到了城市。
那以后,每次谈起这次经历,父子俩都心有余悸。家里的饭桌上,从此没有蘑菇。甚至,儿子说,哪怕在菜市场见到了蘑菇,他都想吐。
可是时间会改变一切。十几年过去了,有一天,儿子回家时,竟提回一小袋蘑菇。他告诉父亲,这是真正的野生蘑菇,是近郊的农民在大山里采的,刚才在街边叫卖,他看着不错,就买来一袋。十多年没吃蘑菇了吧?儿子对父亲说,我想您可能都忘记蘑菇是什么味了。
父亲笑笑,没说话。他似乎对蘑菇并不反感。
父亲把蘑菇倒在水池里仔细清洗。突然,他低下头,从那些蘑菇里挑出两个,扔进旁边的垃圾桶里。儿子问,爸您干什么?父亲说,这两个蘑菇,有毒。
有毒?儿子怔了一下,您怎么知道?父亲得意地笑了。他说,还记得十五年前我们的那次历险吗?那几天,我可能尝遍了世界上所有的蘑菇……
寻找冬日的灯盏
◎吴佳骏
时令渐入冬季,该静的,都安静下来了。
每年的这个时节,我的心,都有种被静谧抚慰过后的透彻。尽管,寒冷会使我的生活秩序,或多或少遭受一些影响。
城市钝化了人对自然变化的敏感。无论是走在喧闹、拥挤的大街上,还是站在家中孤悬的阳台上,我的目光都是那样惊悚不安。我看到很多的老人,待在屋子里,偎着个电火炉,和一只猫说话,和一只狗谈心。我看到更多的年轻人,坐在街边的餐馆里,谈工作,谈爱情。每个人都有自己过冬的方式,都有独自抵御寒冷的办法。
季节的冬天来临了,一些人的冬天,也在来临。
入冬那天,我回了一趟老家。临走前,我在城里买了两件毛衣,两瓶烧酒。毛衣,是买给母亲的。在我的记忆里,母亲很少穿毛衣。我五岁那年,父亲从远方回来,买了一件黄色毛衣,作为礼物,送给母亲。可母亲一次也没穿过,她将那件毛衣拆成线团,改织成了一条围巾和一件小毛衣。后来,那件小毛衣,穿在了我的身上,而那条围巾,套在了父亲的脖子上。
烧酒,是给父亲准备的,晚年的父亲,把酒视作他精神上的一盏灯。没了酒,他会很寂寞。酒,是支撑父亲过冬的良药。唯有酒,才能使父亲的人生明亮。
乡村的冬天,多了些宿命的意味。
落光了叶子的树枝上,挂着两个空鸟巢,像两顶乡村老人废弃的旧毡帽。村头的那条河流,变得比以前浅了,瘦了,沉静中透着忧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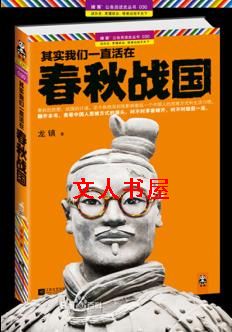

![最佳恶毒女配[原来是美男]封面](http://www.aaatxt.com/cover/5/5069.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