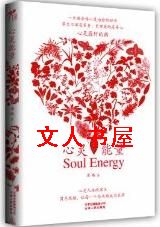心灵的焦灼-第2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极度心烦意乱的 情况下,在这儿踱来踱去达两三十小时之久,瑟瑟缩缩地躲在这寒伧的小城 花园的树荫里,平时夜里只有当使女的和她们的情人在这儿幽会。他大概估 计我只陪了康多尔一小段路,送他上火车站以后就马上回到兵营里来了;而 我却毫不知情,让他在这儿等了又等,等了两三个钟头,我自己在这段时间 里和康多尔正好坐在酒店里。这个生病的老人就像从前等他的债户一样执拗 地等着,耐心地,不屈不挠地等着。他的这种狂热的顽固劲里有些东西使我 恼人,同时也使我感动。
“情况再好不过了,”我安慰他,“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有充分的信
心。明天下午我把更多的情况告诉您,我一定非常仔细地把每句话都向您报 告。可是现在咱们赶快去上车吧,您没看见,咱们可不能再浪费时间了。” “是的,我就去。”他挣扎着,不让我扶他走。我催他走了十几二十步。
然后我感到吊在我胳臂上的分量越来越重。
“呆一会儿,”他嗫嚅着说道,“让我在椅子上呆一会儿。我??我走 不动了。”
果然如此,老人像个醉汉似地晃来晃去。我不得不使出全身的力气,在
黑暗之中,把他一直拖到椅子旁边,耳旁隆隆的雷声已经越来越近。他跌坐 在椅子上,沉重地呼吸着。显然,这等可把他给等坏了,这毫不奇怪:这个 心脏有病的老人踱来踱去足足有三十小时,他直着两条疲惫的腿,站在他的 位置上东张西望,惶惶不安,足足有三十小时。现在他运气好,逮着了我, 他才意识到刚才过分用劲。他精疲力竭,靠在这穷苦人坐的椅子上,就像给 打倒在地。每天中午工人们坐在这椅子上吃他们的干粮,下午养老院的老人 和怀孕的妇人坐在这里。夜里,妓女在这儿招徕士兵,而这个老人,全城最 大的财主在这儿等了又等,等了又等。我知道,他在等些什么。我立刻预感 到,我是没法把这顽固的老头从这条椅子上弄走的(倘若我的一个伙伴撞见 我这样和他呆在一起,亲热得出奇,将是多么叫人恼火的情景!),除非我 能使他内心振作起来。我首先得把他安慰一番。于是同情心又从我心里涌起。 那股该诅咒的热浪又一次在我内心翻腾起来,这股热浪每次都使我无力抗 拒,毫无主意。我俯下身子,向他凑近一些,开始给他打气。
我们身边狂风怒号,喧嚣不已。可是老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对他来 说,既无天空,也无乌云和暴雨,在这世界上只有他女儿一个人和女儿的康 复。面对这个因为激动和忧虑而浑身发抖的老人,我怎么忍心只是干巴巴地 把真实情况——康多尔对这事还并不觉得满有把握——说给他听就完了呢?
老人是需要有样东西能让他牢牢抓住,就像先前他要跌倒的时候,他抓住我 扶他的那只胳臂一样。所以我把费了午劲从康多尔嘴里掏出来的那点使人安 慰的材料急急忙忙地拼凑起来:我告诉他,康多尔已经听到了一种新的治疗 方法,这是维埃诺教授在法国试验过的方法,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我立刻就 感到我身边有什么东西在暗处窸窸窣窣乱动。他刚才还软绵绵地靠在椅子上 的身体这时向我身边凑了过来,好像他想靠在我身上取暖似的。其实我现在 应该适可而止,不要许愿许得太多,可是我的同情心使我走得更远,超过了 我可以负责的程度。我一而再、再而三地鼓励他:是的,这种治疗方法会取 得不同寻常的成功,不出三个月就可以得到出乎意料的疗效,并且说不定—
—不!甚至可以说,这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这种方法在艾迪特身上不会失败。 渐渐地,我自己心里也对这种言过其实的报道产生了兴趣,因为这种安慰的 效果实在妙不可言。每次,他贪婪地问我:“您真的相信吗?”或者“他的 确说了这话吗?”而我由于内心焦急、一时软弱,总是热烈地句句肯定。这 时,他身体倚在我身上的压力仿佛轻了一些。我感觉到,我这番话一说,他 的自信心迅速增长,在这一小时,我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体会到,一切 积极行善之举,部含有一些使人陶醉的乐趣。
当时,我在那把穷人坐的椅子上到底都跟开克斯法尔伐许了什么愿,作 了什么承诺,我现在已经不知道了,而且永远也不会知道。因为,正像我说 的话使他贪婪地听起来无比陶醉,同样,他无比幸福地侧耳细听也激起我的 兴趣,使我向他许的愿越来越多。我们两个都不注意在我们身边闪着蓝光的 闪电,不注意越来越紧的隆隆雷声。我们两个紧紧地靠在一起,一个说,一 个听,一个听,一个说。我以最诚实可信的口气一次又一次地向他保证:“是 的,她的病会治好的,她不久就会恢复健康,肯定会恢复健康!”只是为了 一次又一次地听他嗫嚅着说:“啊,是吗,谢天谢地,”感受极度欢快之际 的那种心神皆醉而又令入陶醉的强烈兴奋。谁知道我们在这种状况中又坐了 多少时间,蓦然间,那决定性的最后一道狂风吹来。这道狂风每次总是刮在 奔腾而至的暴风雨之前,仿佛是为风暴荡平道路。树木一下子被吹得纷纷弯 腰低头,枝桠折裂,劈啪作响,栗子吹落,像阵阵弹雨打在我们头上,身上, 旋风卷起灰尘,宛如一股其大无比的浓云把我们裹在里面。
“回家,您必须回家。”我使劲把他扶起,他也不作任何反抗。我的这
番安慰给了他力量,使他振作起来。他已经不像刚才那样走起路来摇摇晃晃。 他跟我一起,脚步凌乱,急急忙忙地赶到那停着等他的汽车旁边。司机帮他 坐进车里。这时我才感到一块石头落地。我知道他已安全上车。我已经安慰 过他。现在他终于可以回去睡觉了,这个心灵受到强烈震撼的老人,他会睡 得香甜安宁,满怀幸福。
我还想赶快把毯子盖在他的脚上,免得他着凉,可是就在这短促的一瞬 间,发生了使人吃惊的事情,他突然一把抓住我的双手,紧紧地抓住我左右 两手的手腕,我还没来得及挣脱,他已经把我的双手拉到他的嘴边,吻了我 的右手,再吻左手,再吻一次我的右手和左手。
“明儿见,明儿见,”他喃喃他说道。汽车疾驰而去,仿佛被此刻刮来 的那股冰冷的疾风吹走。我呆呆地站着,惊讶不已。可是这时,第一批雨点 已打将下来,像鼓点,像冰雹打在我的军帽上,来势汹汹,声如轰雷。通向 军营的最后四五十步路我是在倾盆大雨之中跑完的。等我浑身湿透,刚刚跑 到军营门口的时候,一个闪电劈了下来,把沉浸在风雨之夜里的整条街都照
得通亮,紧接着闪电响起一阵雷鸣,仿佛把整个天宇都一起扯了下来,这阵 霹雳一定打在附近,因为脚下的地面震得摇摇晃晃,窗玻璃克郎克郎直响, 像被雷声击碎了似的。尽管我的眼睛被这突如其来的电光耀得发呆,我可并 没有像一分钟之前,老人感激涕零、抓住我的手亲吻不已时吓得那么厉害。
二十一
经历了强烈的激动之后,睡眠也会变得香甜深沉。一直到第二天早上, 从我醒来的模样,我才觉察到,那阵暴风雨来临之前的郁闷,以及那番夜谈 时的电流似的紧张情绪已经完全把我麻醉。我仿佛是从难以测量的深渊里跳 了出来,首先陌生地呆望着我熟悉的这间军营宿舍,白费力气地努力思索, 我是什么时候跌进这深渊般的黑甜梦乡的,又是如何跌进去的,然而要想有 条不紊地回忆追思已经没有时间。我的另一种记忆力,有关公事的记忆力—
—这种记忆力似乎和我有关私事的记忆力截然分开,在我头脑里像军人一样 严格地起作用——使我立刻想起,今天安排了一种特别的操练。楼下已经号 角齐鸣,战马踏着马蹄,清晰可闻,从勤务兵一再催促的样子我看出,想必 已到动身出发的紧要关头。我猛地一下子穿上已经摆好的军装,点上一支烟, 一阵风似地冲下楼梯,跑进院子,一转眼就已经和列队待发的骑兵中队一起 催马出发了。
骑着马走在队伍里,你就不再作为你个人而存在:几十匹马发出嘚嘚的 马蹄声,使你既不能头脑清晰地思索,也不能白日做梦。其实我在刺耳的马 蹄声中没有感到别的,只感觉到,我们这轻松自在的一队人马正策马疾驰, 赶上一个美好的夏日。人们想象中十全十美的夏日就是这样:苍穹为雨水洗 净,没有一丝云翳,烈日当空,可是一点也不闷热,四外田野轮廓分明。你 的眼睛一直可以看到远方,每幢房子,每株树,每块田地都看得那么真切清 晰,仿佛都搁在你的股掌之上。窗前的每一束鲜花,屋上的每一缕炊烟,都 因为颜色浓烈、色泽鲜明而显得生意盎然。我们一周复一周以同样的速度, 朝着同样的目标奔驰而过的那条无聊乏味的公路我几乎认不出来了。两旁的 树丛仿佛新上了油漆,在我们头上汇成一个穹形的屋顶,翠绿显得更加浓郁, 枝叶显得更加茂密。我坐在马鞍上轻松愉快,俗虑顿消,最近几天、最近几 星期压迫我神经的一切焦的不安、滞重烦恼的事情全部一扫而光。我觉得我 执行我的勤务再也没有比在那个阳光灿烂的夏日上午更出色的了。干什么事 都得心应手,轻松自如,自然而然,什么都办得成,什么都使我心旷神怕: 天空,草地,热血奔腾的优良战马,大腿一夹缰绳一紧,它们就顺从地作出 反应,甚至我自己的嗓音在我发号施令的时候也叫我听着高兴。
强烈的幸福感也像一切使人陶醉的东西那样同时含有麻醉的作用。拼命
享受眼前的一切每每会让人忘记过去的种种。因此,当我在马鞍上度过了使 人心情舒畅的几个小时之后,下午又沿我熟悉的道路出城前往府邸去的时 候,我只是朦朦胧胧地想到咋夜的邂逅。我高兴的仅仅是我心里这种强烈的 轻松愉快的感觉和别人的快乐。一个人自己兴高采烈,想起所有其他的人来, 也会觉得他们心里快活。
果然,我刚在那座小型府邸的极其熟悉的门上一敲,仆人就开门迎迓。 他平时毕恭毕敬,举止收敛,此刻嗓音听起来显得特别开朗明快。他马上就 催我:“我可以用电梯送少尉先生上塔楼去吗?两位小姐已经在上面恭候。” 可是为什么他说话的时候两只手这样躁动?为什么他这样喜气洋洋地凝 视我?为什么他马上这样风风火火地冲到前面去?我一面开始沿旋转梯一步 步登上露台,一面下由自主地问我自己,他到底怎么啦。他今天出了什么事 啦,这个老约瑟夫,他急不可耐,只想尽快把我送到塔楼上去。这个忠厚老
实的老小子,他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可是,快乐的心情,使人胸怀欢畅,在这么一个阳光明媚的六月大,迈 动两条年轻有力的腿爬上这曲曲弯弯的楼梯,透过四壁的窗户,依次望见东 南西北,看到伸向无边无际的遥远地方的夏日田野风光,也是一种赏心悦目 的乐事。最后只剩下十一二步楼梯就到露台了,忽然有件出乎意料的事情使 我站住脚步。因为说也奇怪,在昏黑的楼梯间里忽然传来一缕舞曲的旋律, 轻柔悠扬,如真如幻,小提琴奏出主旋律,大提琴伴奏,飘荡在琴声之上的, 是微弱的女声动人心弦的花腔。我不胜惊讶。从什么地方飘来这阵音乐!近 在咫尺,同时又远在大边,悠扬婉转,恰似天国仙乐,同时又是尘世之音, 是喜歌剧中的一支流行曲,仿佛是从天上飘落人间。莫非是在附近什么地方 的一家酒店里,也许有个乐队在演奏,微风把这即将消逝的旋律最后最轻柔 的震颤吹送过来?可是过一会儿我就听出,这支轻悠的管弦乐队是从露台上 把乐声送来的,它不是别的,只不过是一台普通的留声机。我心中暗忖,我 这人真傻,今天到处感到万物着魔,到处期待奇迹发生,怎么可能把整个管 弦乐队安排在这么狭窄的塔顶露台上!可是我刚走了几步,心里又变得惶惑 不安:在上面奏乐的,毫无疑问是留声机,然而——那唱歌的声音,这嗓音 听起来是那样的自由和逼真,不可能来自一只轧轧作响的小匣子。这是两个 真正的女孩子的歌声,唱得天真、欢快、热情奔放!我停住脚步,竖起耳朵, 更加仔细地倾听。那丰满的女高音是伊罗娜的声音,音色优美,音量饱满, 丰腴柔软,就和她的胳臂一样;可是和她一起唱的另外一个嗓音又属于谁呢? 这声音我不熟悉。显然,艾迪特请了一个女朋友,一位非常年轻活泼、动人 心弦的姑娘。我实在好奇极了,急于见一见这只啁啾的小燕子,它如此出人 意料地栖息在我们的塔楼上。因此,当我刚一踏上露台,发现只有两个姑娘 坐在一起,艾迪特和伊罗娜,而在那儿用一种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