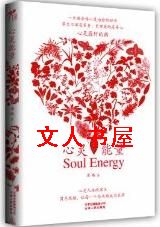心灵的焦灼-第2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是才几个星期吗,而我给 她治病已经有五年之久了。”
突然他停住脚步。“我干脆把实话说给您听吧——我根本没有取得什么 实质性的进展,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成效,问题的关键不就是在这儿吗!我在 她身上来回试验,来回折腾,活像个澡堂里的按摩师,漫无目的,徒劳无功。 到现在为止,我毫无进展。”
他的火气吓了我一跳:显然我伤了他做医生的自尊心。于是我设法安慰 他。
“可是封·开克斯法尔伐先生向我描述过。电疗使得艾迪特的精神大大
振奋,特别在注射了??” 然而康多尔猛地一下停住了脚步,把我说了一半的话硬给打断了。 “胡说!纯粹是胡说!这老傻瓜说的话,您一句也别相信!您真的相信,
这样一种麻痹症用电疗一类的玩意儿可以消除吗?您难道不了解我们大夫惯
用的老策略?如果我们自己已经山穷水尽,那我们就设法去赢得时间,用各 式各样的荒唐花招去折腾病人,不让他看出我们束手无策。幸运的是,在大 多数情况下,病人的天性也跟着我们一起撒谎,成为我们的同谋犯。她当然 觉得好多了!每一种治疗方法,无论您是吃柠檬还是喝牛奶,洗冷水还是洗 热水,首先总会引起身上有机体的变化,产生一种新的刺激,永远乐观的病 人便把这种刺激当作病情好转。这类自我联想是我们最好的帮手,它甚至对 最最愚蠢的庸医都帮了大忙。但是这事有个麻烦的地方——只要这个新招的 刺激一旦消退,立刻就有反应。这时候就得尽快改变花样,假装再采用一种 新的治疗方法。我们这号人在毫无指望的情况下就用这种骇人的把戏巧妙地 七拖八拖,直到哪一天也许碰巧有人找到了正确的方法,有效的方法。千万 别说奉承话,我自己最清楚,我在艾迪恃身上原来希望收到的效果,真正取 得的是多么。微小!到目前为止,我试过的一切办法——这点请您不要弄错
——诸如电疗、按摩之类的骗人把戏并没有真正帮助她霍然痊愈。” 康多尔这样气势汹汹地攻击自己,连我都感到需要为他辩护几句,以解
脱他自己良心的谴责。所以我怯生生地补了一句: “不过??我可是亲眼看见,她能靠身上的机械走路了一那个伸屈
器??” 可是现在康多尔不再是说话,而是干脆对我大吼大叫了。他嚷得那样怒
气冲冲,毫无顾忌,以致在空旷的胡同里两个深夜还在街上走路的夜行人好 奇地扭过头来。
“骗人的把戏,我已经跟您说过了,是骗人的把戏!这是给我造的助行
器,不是给她造的!这种机械是瞎忙活的玩意儿,纯粹是瞎忙活的玩意儿, 您明白吗???不是那姑娘需要这机械,而是我需要它,因为开克斯法尔伐 一家再也不愿意忍耐下去了。只是因为我顶不住他们的催逼,我才不得不给 这老人又打一针强心剂,增强他的信心。我除了给这失去耐心的姑娘加上一 百磅重负之外,还有什么法子,就像给拼命挣扎的俘虏套上脚镣一样??这 就是说,也许这机械多少可以增强一点脚上的筋??我当时实在没有别的法 子??我不是得争取时间吗??可是我对这些花招、这些骗人的玩意儿一点 也不感到羞愧,您已经亲自看见了它的成效——艾迪特说服自己,说她自从 戴上机械以后,走起路来利索多了。做父亲的洋洋得意,说我帮了他女儿的 大忙,大家都对这个了不起的、天才的奇迹创造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您自己 也把我当作万能博士来请教!”
他停住口,摘下帽子,用手拭擦一下湿漉漉的额头,然后不怀好意地从 旁边瞅着我。
“我怕,这番话您不怎么爱听!您过去把医生看做救星,看做真理的化 身,这幻想现在破灭了!您青春年少,热情洋溢,把医学道德完全设想成另 外一个样子,而现在??我已经看见??有点冷静下来,甚至对这类行医之 道大倒胃口!但是,遗憾的是——医学和道德是毫不沾边的:每种疾病本身 就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行动,是对大自然的叛乱,所以可以采取一切手段来 对待它,什么手段都行。不,千万不要同情病人——病人已经把自己置于法 律之外,他破坏了秩序;而为了恢复秩序,也就是为了使病人康复,就必须 像对付每次叛乱一样,不顾一切地采取果断的行动——手头正好抓着什么就 使用什么,因为单凭善心和真理,从来没有把人类治愈过,也从来没有把某 一个人治愈过。如果一个骗人的把戏把病治好了,那它就不再是可鄙的骗人 把戏,而是第一流的特效药了。碰到一个病例,只要我在医学上已经无能为 力,我就必须设法帮助病人拖延时间。一连五年之久,老要想出一个新的招 数来,特别是他对自己的绝招也并不怎么信服,少尉先生,单单这一点也已 经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了。反正一切恭维奉承,我都敬谢不敏!”
这个矮胖子无比激动地站在我对面,仿佛我只要稍加反驳,他就打算对
我诉诸武力似的。这一刹那在乌云密布的天空闪现出一道蓝色的闪电,宛加 入身上的一根血管,接着轰隆隆响起一阵沉重的闷雷。康多尔突然哈哈大笑。 “您瞧瞧——天公的怒气作了回答。喏,您这个可怜的人啊——您今天 真是倒媚透顶,幻想一个接着一个被解剖刀割去,首先是关于匈牙利显赫贵 族的幻想,然后是关于关心体贴、万无一失的医生和救星的幻想。不过,您 必须理解,这个老傻瓜的赞歌是多么叫人恼火!恰好在艾迪特这个病例上, 这种温情脉脉的无谓之举特别使我反感,因为进展如此缓慢,我在她的病例 上还没有找到,也就是说,还没有发明出决定性的特效药,这使我的内心一
直十分痛苦。” 他默默地走了几步。然后转过脸来看我,脸色变得和蔼了一些: “话说回来,我不愿意您认为我心里已经放弃了这一病例,这是我们医
生用的一种漂亮的说法。相反,恰好这个病例,我绝不撒手,哪怕还得再拖 一年或者五年。再说,事情也真叫奇怪——我刚才跟您提到过那次报告会, 就在我听了那次报告的当天晚上,我在巴黎的医学杂志上找到一篇文章,描 写的是一个瘫痪病例的治疗法,非常古怪的病例:一个四十岁的男子,已经 足足两年,全身瘫痪,卧病在床,四肢全都不能动弹,维埃诺教授为他治疗
了四个月,病人又能生龙活虎地爬六层楼了。请您想想看:四个月工夫就取 得这样的效果,和我碰到的这个病例完全相似,而我在这里瞎忙了五年,白 费力气——我读到这条消息,简直喜出望外!当然,这个病例的病原学,以 及治疗的方法,我都不十分清楚,维埃诺教授似乎独树一帜,把一系列治疗 方法部结合起来加以运用,在坎纳进行一种日光浴,装上一套机械,再做某 种体操。病历写得十分简单,我当然无法想象他的这种新方法是否有一部分 适用于我们这个病例,究竟适用到什么程度。可是我立刻亲自给维埃诺教授 去了封信,希望得到更详尽的数据。就是为了取得我们自己的数据,我今天 才对艾迪特这样仔细地又检查了一遍。我总得要有互相比较的可能性啊。所 以您瞧,我并没有挂上白旗宣布投降,相反,正在抓紧每一根救命草,也许 在这种新方法里的确有一种可能性——我只说也许,我并没有说更多的,其 实我已经胡说八道讲得大多了。现在别再谈我这该死的职业了!”
这时,我们已经离火车站很近了。我们的谈话很快就会结束;所以我急 急地问道:
“这么说,您认为??” 可是这一瞬间这个矮胖子一下子站住了。
“我什么也不认为,”他粗暴地对我吼道,“也根本没有什么‘这么说’! 你们大伙到底要我怎么样?我跟天主又没有电话联系。我什么也没说。什么 确定的话也没说。我什么也不认为,什么也不相信,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 许诺。我本来就已经胡言乱语说得太多了。现在该结束了!谢谢您送了我一 程。您最好还是赶快往回走,要不然您这身军装会给雨浇得透湿。”
他不伸手和我握别,显然十分生气地(我不理解,他为什么生气)迈着
他的两条短腿向车站跑去。我觉得,他有点平足。
二十
康多尔看得很准。人的神经早已感觉到的那场暴风雨显然已经来临。厚 厚的乌云宛如一个个沉重的黑箱子隆隆作响,在骚动不宁、震颤不已的树梢 顶上堆积在一起,有时候被一道闪电的人星照得通亮。潮湿的空气不时被阵 阵狂风猛烈摇撼,发出烟熏火燎的焦味。我快步往回跑的时候,整座城市似 乎变了样子。大街小巷看上去也和几分钟前换了一副模样。那时一切还都凝 神屏息地沐浴在黯淡的月光下。可是这时,商店的招牌被吹得叮叮当当、噼 噼啪啪直响,仿佛被一个恼人的噩梦吓得瑟瑟直抖;房门不安地乒乓乱响, 烟囱呼呼直叫,像在叹气,好几家屋里有人惊醒,好奇地亮起灯光。接着便 可以看见有几个窗口上闪现一个身穿白衬衣的人赶在暴风雨之前,未雨绸 缨,先把窗户关紧。少数几个晚归的行人好像被一阵恐惧的疾风所驱赶,急 急忙忙地从拐角处跑过;连宽阔的主要广场,平时即使在夜里也还比较热闹, 这时也一片荒凉,阒无人迹;市政府那架被灯光照亮的大钟瞪着傻乎乎的白 眼,呆望着眼前这一片异乎寻常的空漠。然而要紧的是:多亏康多尔的警告, 我得以趁暴风雨来临之前,及时赶回家去。只要再拐过两个街角,穿过军营 前面的市营公园,我就可以呆在我的房间里,把我在这几小时里听到的、经 历的一切出于意料的事情彻底思考一遍。
我们兵营前面的这座小花园完全淹没在黑暗之中。在骚动不宁的叶丛下
面,空气凝聚得滞重郁闷,有时嘶的一声,一阵短促的疾风像蛇也似的从树 叶中间钻出来,这被疾风激起的声响接着又返回一片更加使人毛骨惊然的寂 静之中。我越走越快。我差一点就走到兵营的门口了。这时树背后有个人影 一闪,从树荫里走了出来。我愣了一下,但是并没有停注脚步咳一声,这大 概只是个妓女,这帮妓女通常都是守在这儿暗处等士兵的。可是使我生气的 是,我感到身后有个陌生人的脚步轻手轻脚地跟随我紧赶慢赶。这个死不要 脸的婊子这样无耻地缠着我,我打算臭骂她一顿,便扭过头去。正好在这一 刹那打了个闪电,把四周照得通亮。我在亮光中看见一个脚步蹒跚的老人气 喘吁吁地跟在我背后,使我大吃一惊的是,他没戴帽子,露出光秃秃的脑袋, 金丝边的眼镜一闪一闪地发光——原来是开克斯法尔伐!
起初,我在惊愕之余,自己都不相信自己。开克斯法尔优跑到我们兵营
的花园里来了——这是不可能的事啊。我在三小时之前才跟康多尔一起在他 家和他分手,他当时已经疲惫不堪。是我眼花,产生了错觉,还是这老人神 经错乱了?他是发着高烧,翻身起床,现在穿着单薄的衣衫,没穿大衣,也 没戴帽子,在这里到处梦游?可是,这就是他,不会是别人。我即使在成千 上万的人群当中单凭他瑟瑟缩缩地走过来时那种缩着脖子、弯腰曲背、心惊 胆战的样子,也能把他认出来。
“我的天,封·开克斯法尔优先生,”我不胜惊讶他说道,“您怎么跑 这儿来了?您不是已经上床睡觉了吗?”
“没睡??或者说??我睡不着??我还想??” “可是现在快回家去吧!您没看见,暴风雨随时可能到来。您的车不在
这里吗?” “就在对面??它停在兵营左边等我。”
“太好了!那么赶快吧!要是开快点,还能及时把您送到家里。走吧, 封·开克斯法尔伐先生。”他还在迟疑,我就干脆抓住他的胳臂想把他拖走。
可是他用力挣脱身子。 “就走,就走??我这就走,少尉先生??可是请您先告诉我:他说了
些什么?” “谁?”我的问题,我的惊讶都是真挚的。在我们头上,狂风怒号,越
来越猛,树木叫唤不己,低头弯腰,似乎想把自己连根拔起,暴雨随时可能 瓢泼似地落下。我不消说只想一件事,只想最自然不过的一件事,那就是如 何。把这个显然神智昏乱的老人弄回家去,他似乎丝毫没有注意到暴风雨已 经逼近。可是他几乎愤怒地结结巴巴他说道:
“康多尔大夫呀??您不是送他了吗???” 现在我才明白,这次在黑暗中相遇,不消说,并非偶然的邂逅。这个焦
躁不安的人,等在这儿军营门口,只是为了赶快获得确切的消息。他就在这 大门口守候我,我从这里经过,必然逃不过他的眼睛。他在极度心烦意乱的 情况下,在这儿踱来踱去达两三十小时之久,瑟瑟缩缩地躲在这寒伧的小城 花园的树荫里,平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