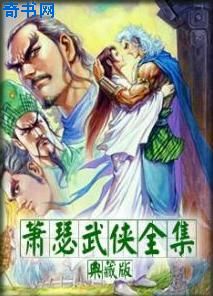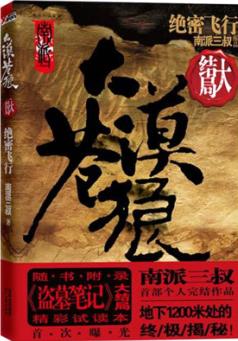��Į��-��24��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Ҳ���ǹ֣���һ����Ѿͷ����һ����Ѿͷ���Ǹ���������Թ�Ҳ��������ӡ����룬ɶ�������ӣ��Բ������¸�Ѿͷ���ӣ��Ҿ�����Ѿͷ�����¸��������ӣ��Ҿ��������ӡ�Ů���ǿ�أ��Բ���������Ц��������ѽ���㲻�Ƕ��𣿻���ɶ�����ͰѴ�����Ƕ����������Լ�Ҳ�붮�벻������������Ǹ�Ⱦɫ���̸��һ��ѡ�Ů�˵����ӱ������ˡ��������´��ȣ�˵����������˼����ӡ���Խ˵����Խ��Ϳ����ֱ˵�������˾���������Ů�˾�����������Ц���������ˡ������ⲻ�Ͷ��ˡ������������������������ӣ�����û���¡���ʵ����û���¡��²��ϸ����֣���������������˵�ⲻ������ԩ���𣿡�
��Į�����������֡���Į���������£�10��
������Ϸ���������е�ԩ������Ҳ���㣬�����ֲ��ã���Ϊɶ��������֣����ܸ�ɩ�Ӷ���������ȣ���Ϊɶ����С���ӵ��������أ���������Цһ����������һ���������Ͳ���һ����������Ϊɶ������Ϊɶ�����ֲ��Dz�֪�������������Ǹ��ϻ����۸���ʱ����Ҳ�ϻ��ۣ��úܡ������ˡ�һ���������������������˵������Ҫ���������������ġ�һҹ���ް��ն����������������ƨ�������ĸ�����ն�ȥ����
һ����ȥ�����Ӿ����������ˣ�###�����˵������ѽ����顣����ƽ�������Ҵ���ʱ��������������Ҫ��Щ�ܻ����Ц����ʱ�������ֱ¶�ý��������졣���Ӻ�˫��Ů����һ��֮ǰ�������ҹ�����Ҫ����Ʒζ��������³��ĺܻ��ɧ�Ļ�����Dz��į���˿���һ�Σ����ӱ㲻�����ˡ�����һ���ӱ���Ϊ���ѡ��ܴ������£�����Ϸ�����ޣ�������������һ�ۡ�
˵Ц���䣬���ӱ��dz��š�������ƣ��Ϯ������ͷҲ��ζ�ˣ�������ȥ���Ǹ�Լ�ᣬ���Իؼ�˯�ˡ�
��5��
�������磬������쳹���ӡ�����֪������ѧУʦ��ȥ˫�������ҡ�������ҹ��һЦ�����룬��֪������ȳɸ�ɶ�����ټ����棬���ٲ��˰���˵����ˤ���ʲô����й���ء������ֹ���ȴ�����˿����ֵ���ȥ˫���ҡ�
˫��Ժ��������Ϣ�ˡ�һ����Ѽ���ӵ������ڽ����������ǡ����ڵ���������ǧ�֮��ĸ�л˫���Ļ��������ϳ��������ϵĸɲ�����˵�ܽ���������ѧУ�ܡ����˽�����Ұ��һ��һ��ģ���ζ��Ũ�����磬���ϰ��ճ��һ�һ㶡����Ӽ��������仰�ͳ�һ��˫��Ů�ˡ�˫��Ů���������Ź⣬һ���ܵ�����������̬�����Ӻ����������ӡ����������ϸɲ���˫��Ů����һ�֣�Ҫ������զ��ôʹ����˫�����������Ӳ�����ǣ����Ǹ��������Ů������˿������������ҹ��ʧԼ����������ʹ�ࡣ�����û�����������ϡ����ң������ϵ���̬�ַ������ֳ���˫���ܸɵĿ϶������Ӻ�������
���������ʦ̧��д�š��ݼ�ɣ���������������鷿�ſڡ�����ܺ졣���ǽ�ɫ�ģ�Ϊ�Ǹ�Ѱ�����Ż���ɫ���١����Ӳ���ɣ����ʲô��˼����֪��˫����˫��Ů�˺ʹ�����Ҳ�϶���֪������ʵĺ��壬�����������Ǹ��ôʡ�˫��Ů��Ҳ�϶�֪�����Ǹ��ôʡ��������Ǹ�ث�������ӷ߷ߵ���һ��Ů�ˣ�ȴ����ش������ϲ�ס�˱��ݵĺۼ����ԣ����ݡ�����������Ϸ������������ֵ����������¶���˿�����˭���أ��������������ӡ���ô������˭���������ϰ�ү�������ѶϢһ����Ѱ��Ů�˵�������Ȼ��������Ů���۽ǵ�����������������ɨ�ӿ����ֵ�Ů���ǡ�ÿһɨ�ӣ�������DZ���Ӧ�ظ�����������Ц�����������ˡ������ñ������Խ���������ĵĐj�̡���������¶�����С��
���ϸɲ�����һ�ӳ���ͷ�ֽ��Ž�����˵��
���š�����˫���Ǹ��������ĵ��ˣ����˻����������ǡ�������Щ�����֡�����Ǯ�ˣ��۾����ˣ��ϲ������ˡ��ţ����ϲ��������ǣ�������Ҳ�ϲ����㡣���Ǹ��ţ��ţ������м�����Ǯ�˫���ɲ��������ˣ��������뵽����ɶ���ţ���ѧУ�������ޣ�����������ѡ���˵���������ѣ������������ѡ��ţ����Ѻð����Բ��ԣ�˫���Ǹ������ĵ��ˣ������ġ��ţ������ľͺá����Ҿ�˵��Щ����
��Į�����������֡���Į���������£�1��
���ͷ˵һ�䣬������Цһ����Ժ��Ц�������ӿ���˫��Ů��Ҳ���˿�Ц����Ц�ŶԵ������Ǹ����֡������IJ������ˣ���Щ�����ҹ��ʧԼ�������ô��������ۣ�
��˫�����ﵰ�����̺��ˣ�һ���־���������������
�������ﵰ����Ź֣��ɴ���������Ʊ��ү�ţ����붼�����ġ��������ǡ���˵�˼�һҹ��һ���ƻ���Ů��һ���־��������ǧ�ġ�������ɶ���˼Ҳ������μ�������ѡ���
�����Σ�ƾɶ���ٺ٣��˼�ƾɶ����ѽ�����ǵģ�����Ϊ�˼������⼸�����ͳ���⵰�ˣ���
��Ҳ������ѽ��Ϊ���Ǽ�����Ǯ����үү�������̣�����̨�ӣ������װ�������������������ң����
����ѽ��Ҳûɶ��˼���������������ô����ɶ���۾�һ�գ������Ǹ��յġ���
���Ӹе���Ц���룬Ҫ��˫��������Щ����զ�룿��һ����Ϊ�����ǻ�Ϊ������ж������ء���ʵ��˵ɶ����û���أ��������㻹���Ƹ�ɶ�أ���������˫��Ů�ˡ���Ҳ���÷���������Ŀ�����һ�£�������ɨ�˹�ȥ��һ˿�������ŭ�����������ϵĵ�����顣���������ں��ҡ��������롣���ܸ�����һ���֡�
�ý��Ļ��������ˡ�������������������Ǻ������������Ժ�䱻�������ijŵþִ������ࡣ���ֵ������������ӣ���ȥ����ͷ�ոո�������١����������ϸɲ�����˫��Ů��˵��Ů��һ���µ�ͷ�����ӹ��������ܻ�ع�ͷ������һ�ۣ�����ȴû���������룬����Ҫ�Ľ����Ǹ����ˣ����ģ����ѵľͳɡ�����˵���IJ����ǹ����������յ�һ��ţ����ţ��ؼҡ�
��ͷ������������������ӣ�˵�������ã��㵽����ȥ����һ�¡��������ﲻ����������Ӽ���ͷ��ɫ���ƣ�����һ����˵����զ���⸱ث���ˣ�����ͷ������ûɶ��������ҹ�������ˡ�������˵�����Ͻ��Ը�ҩ������ͷ˵�����ֲ�������ġ���˵���Ǹ����Ե����𣿡�������Ȱ�˼��䣬ȥ�˾��ϡ�
��ͷ�е���ƣ�������߲�������ʹ�����ɵ��鷿��ɳ����ЪϢ�������������ϵIJ��¶�����������Ҳ���Զ��ۣ�ֻ������������˺ͻ������������ڶ������롣��ʱ���ˣ�������Щ��ϰ�ߡ�ż��һ������������������ֱ��������̣������е�������г�����⣬���ڳ�����æ�������Ҳ�����������������ɳ�ѣ�Ө��ȥƽ�أ����ӵ����ϣ�����һ���˳����������졣����Щ������˼�ˣ����������ȱ�ˮ�����˳���������˵�����裬��ȥƽ�ء�����˵�������ˣ�ЪЪȥ�����˼����ˡ��ǵ������Ǹ�ȥ������ͷЦ���������ֲ��dz���չ���Ъɶ����˵������һ��¿�������˵��ײ�ס������˵��������ȥ�͵��࣬����Ȧ��һ�¡�����ͷӦ�������š�
��ͷ������ˮʱ�������߲���˺�Ѱ���۸У�����һ��û�ԣ�ǿ���������ࡣ�豧����ݣ�������ӣ������ͺ��ࡣ�����ͷ��ʱ�ָ��߲������ʣ���զ�����������û�Ȼش𣬱㾪�е�������ѽ������ɫզ�����ѿ���ɷ��ɷ�Ƶġ�����ͷ����Ц��������զ�ġ���һ�㡣�����������ӹ����£�ִ��Ҫ��ȥҩ�̿�һ�¡���ͷ��Ӧ�����Ȧ��ȥ��
�������Ȧǽ�ϵ�ȱ�ڣ�������ǽ�Ǵ�����������ѭ����ȥ����һ�������Ũ�̡����Ż��ˡ�����ͷ����һ������������ȥ��ȴ��ȳ��ү�Ķ������������Ż�����ִ�Ц��ȼ�ŵ���һ����ն⡣����Ů�˾�էէ������������������ǰ������Ȼ�Ǽɵ����ӡ���ͷ��˵���Ӿ��������ˣ���Ů�ˣ�����ƻ������ӷŵġ�����æ��������ʣ�µİ�Ͱˮ�������ѡ�����ͻ�����̵�����������ֻ������Щ�������ֱ�ȼ������
����ȥ���ˡ�����ͷ���Ǽ��������˵�Ů�˺�һ����Ů���Ǿ�����ȥ����ͷ��֪����ػλ����е�Ͱ�ӣ�֪��������ȡˮ���������㽫Ͱ���ӵ�һ�ԣ���һ��ճ������£���������������Ҳ��Ժ��ȡ���£�һ�������������ƽ������ˣ��ն�ʣ��һ��Ũ�̡�
ѭ�����������Ƕ��Ѵ�����ˮ��������ϡ������������������ͷ�����а��»��֣����»����������½���Щʪ���ܺڻƼ��ӵ������̯������
��ʱ�����˿��������Dz��������ӿ��ĵ�Ц������ͷ�������ӣ�ҡҡͷ��̾������ʲôҲû˵����˵������������Ҫ��û�ˣ����ǰѷ���Ҳȼ�ˣ���
������¿�յġ�������˵�������ƣ�����Ц�ء���
����ɶ��������˵�����˼����Ӳ���ɡ���ȳ��Ҳ�����ƣ���
�����ˡ�������˵����˵�ǵ������ݣ����ö�Ǯ����������˵������Ǯ���ܴչ���ȥ��������̸�䣬�������������Ů�����˷���������������§סһ��Ů�ˣ��������ҽС��������ְ˽����������������û������Ӽ��������˼�ȭ��ȴ�����¿����һ����ûһ�㷴Ӧ��
�ӳ����ͷ��һ�۹�����˵����ȥ�������Ӹ�ȳ��ү��ȥ�����������ŵ㡣��Ȼ�������¿ɵ����������ֶԹ���˵���������ȳ��ү��Ǯ�����Ļ����һ���Щ������������ȥ����ץ������������Ӧ�����ͼ���Ť�����ӡ�
��Į�����������֡���Į���������£�2��
��1��
��ٲ�֪����Į������������ˡ�
���Ǹ�����Ϊ̫����ɹ�ʶ�������ȷ��������ˣ������������Ӱ�����ݵIJ��ġ�����ͷ�������������dz�������ɫƤ����ͷ�������Եش�����ñ��ñ�������ˣ��ڲ��˶������⣬�ұ����ܷ紵�÷����ˡ��紵��������������ĺ��ӣ������˼���Ʈ�ݡ�
��Ⱥɢ����ɳ�������Щ����˪�ӹ��IJݡ�ż���������������㣭���㣭�����Ľ�������ɳ������Щ�������������˲п����ɱ����پ���������������������ķ·�Ҳ����������ů�硣�ǵģ�����������к�������ͺܰ��ơ�����������лƲԲԵĴ�Į������Ⱥ�����Ǹ�����������������ˡ�����������һ�����������ش��������������ֵֺܹľ���
������ӣ���������������ټ��ϵĺ����ʡ�
���������Ҳ��ͬ���������ʡ�
˭Ҳû��Է��Ļ������ʻ���ֻ��һ���к���ʽ��
��������������������չ֣�����һ���ļ�������ëҲ�����š�զ����ӵļ�����أ���
���������ˡ������˵������һ������������Զ�ˡ���
�ϰ�үϵ�ſ������ɳ�ݡ�һ�������ˣ����ͽ��ˣ���Ӵ���հ�ͷ���㻹û��ѽ����
������Ц�ˣ�������Ǹ��հ�ͷ�����˺��⣬û��������������ϱ�����Ϸţ����Ķ���ѽ������ѽ��������������𣿡���������˼��Ц�ˡ���Ȼ��������ٵ����ϰ�ү�������ˡ��������ӵ��棬˵��үү���������Ϸ������ƺ�������ͳ��
�����ǵġ���
���ޣ��Ǿ�ûɶ����װ������û��������������˵�����������������š�ûɶҲ�ɣ��ɲ���û�����ȡ���˵������ط���ʮ����¼����ϸ���Ӱ��û�̳飬��������ѽ����
���Ǿ͵��������̵�¿���ˡ����ϰ�үЦ���ͳ��̹���������һ�����ˣ�װ�̵��������һ�ڡ������ú��³�ʱ����������ѱ����˳ɵ��������ˡ�����ѽ���㵽������ȥ�ˡ���������˵��
������Ҫծ�����٣������̣������̡���ɶҲû����ƫƫ�������ˡ������֡�������������һ�ڣ������ڷ��������ã���˵��
�ϰ�үֻ��Ц����������������·��½���������⡣������Ҳ���ں����Ƿ�������ֻ�DZ����̹�����һ�ڣ�˵һ�䣬��Юһ�²˳�һ�ڷ��Ƶġ�
���浹û���á��������ֲ���¿�������峦�������֡�������װ���ǽ������ǹȿ��������̷Ÿ�ƨҲ�ܿ������ϡ�����˵������ˮ������һ����
������˭Ҳ�������߳�����������ٸе���Ц�����룬Ҳ������ƽʱ�ѵ�˵������ʱ�Ź��ɡ�
�ϰ�ү����Ц�ˣ�������հ�ͷ�������ҵ�������Ҹ�˵����һ�䶼���ҡ�����˼Ҽ���ϱ�����ϣ������ˣ��Ž�ɳ�ѡ��Բ��ԣ�����հ�ͷ����
��ƨ����������Ц������ɶ��������ѽ���ƹʱ�������ϱ�����֣���˵��Ӵ������������٣����ֵ�Ȼ�࣬������������ӡ���˵���������ƵĿ���Ц�ˡ�
���㾭������Ȼ֪�������ϰ�ү�ٺ�Ц������Ҳ�����������İ�����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