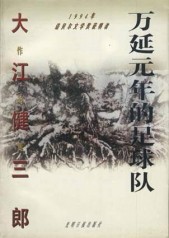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第3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走到村公所前面的广场,我立刻便把超级市场的天皇一行人认出来了。他们正经过超级市场,在石子路上走着呢。超级市场的天皇是个大块头,黑色外套长达脚跟,下摆甩来甩去,正迈着军人一样正规的步伐走将过来。他的那张圆脸上扣了顶大口袋似的鸭舌帽,离得很远,也看得出他脸上气色不错,肌肉丰满。身前身后的几个小伙子,也一律膀大腰圆,大步流星地走着。他们穿着粗劣的外套,光着脑袋,学着头儿的模样,挺胸昂头地只管径直往前走。一时间,我清楚地记起了占领军坐着吉普车第一次开进山脚那天的情形。超级市场天皇的一群人马,与那个夏日的清晨沉稳地炫示胜利的外国人何其相似啊。那天早晨,山脚的大人们第一次亲眼认证了国家的战败,他们无法习惯被占领的感觉,故意不理睬外国的大兵,只顾忙于自己日常的劳作。然而那〃耻辱〃,却已经渗入了他们整个的身体当中。只有孩子们迅速适应了新的情况,他们跟在吉普车后面疯跑,在国民学校接受临时教育时哈啰、哈啰地叫个不停,也不惮于把外国兵递来的罐头饼干接到手中。
今天,在石子路上倒霉遇见超级市场天皇一行的大人们,也是把头埋得低低的,或者干脆背过脸去,活像群一心找个窟窿爬进去的耻辱难当的螃蟹。〃暴动〃那天,他们直面这〃耻辱〃,于是才获得了一种破坏力量,彼此团结在一起了。而今,山脚的村民已经屈服,他们对这〃耻辱〃懊恼不已,这再也无法成为仇恨迸发的契机。这〃耻辱〃现在变得阴湿可厌,疲弱无力。超级市场天皇和他的属下,便是踩着山脚村民〃耻辱〃的踏石,傲然显示着威风。那个不穿衬衫、只穿件晨礼服的阴惨〃亡灵〃,与现实的超级市场天皇反差竟如此巨大,这使我徒然地幻想,真该让那个扮成〃亡灵〃的山脚青年来迎候正走在石板路上的超级市场天皇。于是,我自己几乎也骤然觉得了那尖锐的〃羞耻〃。山脚的那群孩子远远跟随着这一队人,然而他们也全部默不作声,仿佛森林高处打着旋儿怪叫着冲将下来的狂风,摄走了他们的精神。像我们在童年的时候一样,他们虽然一定能最先适应山脚下的新情况,可是他们也曾经投身于〃暴动〃当中。因此,他们童稚的头脑所能包容的〃耻辱〃,一定同样令他们懊恼难言。
超级市场天皇很快把目光投到我的这边来。想来这是因为我是山脚唯一一个毫无惧色地直面着他的人吧。超级市场天皇,在长相明显与他种族相同的那群青年的簇拥下,迎着我站住,他丰满的脸上,一双悠然的大眼睛定定地看着我,眉头皱着,仿佛只是要表示集中了注意力。他一声不响,下属们也都一声不响地盯视着我,嘴里吐出粗重的白气。
〃我姓根所。我就是和你做过交易的那个鹰四的哥哥。〃我讲话的声音嘶哑,这绝对非我所愿。
〃我嘛,叫白升基。〃超级市场的天皇说。〃就是白色的升再加个基础的基。令弟的事,真够遗憾的。我很痛心,他真是个独特的青年哩!〃
我不禁带着感动和疑惑,端详着白先生定定地盯住我的那一双忧伤的眼睛,以及那从上到下肌肉饱绽,神采奕奕的脸。鹰四从没与我和妻子讲起过这超级市场天皇到底是怎样的人,而通过装扮超级市场天皇卑微的〃亡灵〃,他不仅把我们,也把山脚的村民诓骗了一场。其实,他对这朝鲜人倒是印象很深,也许还要朝着他说,你真是个独特的人!眼下,超级市场的天皇也用上同一个词来形容,我觉得他这是在暗中对死去的鹰四给他的称赞所做的回报。那白先生眉毛粗重,鼻梁挺直,潮红的薄嘴唇纤细得像女人,耳朵鲜嫩得如同鲜草。他的整个脸,都洋溢着青春的生机。见我默默地打量着他,他纯真善良地泛出一阵微笑,露出了一口白牙。
〃我这次来,是有事要求您的。〃
〃我正要到仓房去看看呢。算是吊唁一下令弟吧!〃白先生皱着眉头,只顾微笑。
〃那间独间儿,就是这孩子一家住的。现在他妈妈病了,先生能不能缓一缓再让他们从独间儿里搬出来?〃
〃病人入夏之前就一天天地瘦下去,怕是就要死了啊!〃阿仁的儿子补充着我的解释。〃吃罐头把肝也吃坏了,瘦得没有从前的一半大呢!现在,她什么也不吃了!怕是活不长了!〃白先生收起微笑,注意地观察阿仁的儿子。少年不像我是个外来户,在山脚呆不长久。于是,他一改与我讲话时的那种社交口吻,对少年表现出一种道地的关心。然而,他立刻像责备自己似地皱了皱眉,重新换上了一丝宽宏的微笑。
〃要是碍不着拆除仓房和搬迁的话,独间儿的人就先住下去好了。施工的时候,麻烦怕是少不了,你们只好多克服点了。〃说到这里,那白先生稍稍停了一下,像是要阿仁的儿子记得清楚些。然后接着说:〃可仓房的施工结束以后,要是你们还想留下,我可不给你们动迁费的!〃
听了这话,阿仁的儿子怒火顿生,像公鸡一样昂着头,转身跑走了。他在心里恐怕又想与超级市场天皇干上一场了。我没有反驳白先生的话,阿仁儿子的背影便是在向我炫示最后一点友谊的结束罢。
〃仓房的一部分墙壁已经坏了,得察看一下拆除的事。〃白先生和我一起目送着少年远去,一面道:〃我带来了几个建筑系的学生。〃
我们一同走上去仓房的石子路。那几个学生壮实得活像摔跤选手,脑袋硬得像炮弹一般,满脸雀斑,一声不响,甚至不曾彼此窃窃私语。走进前院,白先生道:
〃仓房里要是还有什么重要物品,请搬出来。〃
我纯粹形式地把约翰·万次郎留下的那个字迹已经模糊不清的扇面拿了出来。一个小伙子把扛在肩上的麻袋里边的工具往仓房前面的地上一倒,看热闹的孩子们立刻往后退,仿佛那麻袋里装着什么武器一样。刚一开始,青年们卸下房门,把屋里的草席之类的东西搬出来的时候,他们的神情举止,近乎虔敬。然而干到一半儿,白先生用朝鲜语下达了命令之后,他们的作派中便立即充满了破坏性作业的气氛。他们砸坍了一楼面朝山脚那边的墙壁,弄得这百年老墙墙基的干土和烂掉的椽头板条飞扬起来,落到旁边山脚的孩子和我的头上。他们轮番挥着鎯头,毫不留意拆除了仓房的支架和墙壁后的平衡问题。白先生全然不顾扬起的灰尘,兀立着指挥他们,对这些问题他也是不屑一顾。我觉得,这对山脚村民来说无异于一次使用暴力的积极挑战。这仓房的墙壁,是山脚现存的日常生活最为古老的表现,而今它叫白先生这伙人用鎯头破坏无遗。在我的眼里,他们毋宁是在炫示:如果愿意,他们尽可以把山脚村民整个的生活破坏净尽。孩子们屏住呼吸盯着他们干活,也分明能感觉到这一点;而大人们,尽管尘土像洪水一样涌向山脚,他们竟没有人过来提一点抗议。这百年高龄的仓房摇摇欲坠,房顶上依然残留着瓦片,可墙却已被掏空,那残垣断壁显然无法负重,仿佛一阵狂风就足以将它吹塌。我突然觉出了一种不安。我怀疑白先生甚至无意将仓房房梁等重木结构运将出去,到城里再建房子,他只是为了在山脚的村民面前拆房取乐,才把仓房买下来的。过了不久,面朝山脚那边墙壁的三分之一,便从天棚到地板统统给拆除了,那一堆风吹不掉的墙土,也用铁锹给清理得一干二净。我站在白先生身后,和孩子们一起盯着那照得通明耀眼的仓房内部。我觉得,它简直像朝向山脚的一部舞台布景。这种印象,很快就在我的梦里获得再生。它显得异常狭窄,整个内部歪斜不堪, 却分外鲜明。业已消失的百年来微明的印象连同对僵直地躺在房里的S兄的记忆,如今都已经淡漠下去。那拆去的墙面,竟从一个奇特的角度展现了一幅山脚远眺的画面,那是鹰四教山脚的青年训练足球的操场,以及积雪消融之后重现冬日旱情的褐色河床。
〃没有铁棒吗?〃白先生同那帮刚干完活的建筑系学生用朝鲜语讲完话,便朝我走了过来,逼得围观的孩子们怯怯地向后退。他粘着灰尘的眉宇依然皱着,同时露出了一个微笑。
〃我想把地板取下一点,看看地下室的情况。这种地下室墙面和地面都是石头铺的,要运出来还得加人手呢。〃
〃哪儿有什么地下室。〃
〃地板修得这么高,就是因为有地下室嘛。〃一个脸色苍白的建筑系学生肯定地说。他一下打消了我的自信。
于是,我带着他去仓库,取些山脚人倾巢出动修理石板路时用过的修路铁棒。在仓库的门口,还放着一堆鹰嘴样的武器。那是鹰四自杀后的第二天早晨,离他而去的少年们扔到前院被我拾起来堆在这里的。我们从仓库的地板下面,把生满红锈的铁棒拽将出来。直到这时,我仍不相信会有地下室,便和白先生站在一起站在仓房的门口,看那伙青年把地板橇下来。那地板已经朽腐不堪,很快就破裂了。我们这些在旁边围观的人为躲开新腾起的灰尘,只好把身体转来转去。突然,一股潮湿纤细的黑灰,犹如水下摄影的电影里乌贼的墨汁喷出了墨囊一样,登时从仓房里面涌将出来,朝着我们缓缓地移动。就在我们躲闪不迭的时候,青年们还在继续橇动地板裂缝,发出吱吱咯咯的声响。过了一会儿,等灰尘散尽,我和白先生走进仓房的时候,看见从门口横框到房里的地板已经开出了一长条裂缝,缝里面露出了黑暗的空间。一个青年带着天真的微笑,从里探出头来,明快地用朝鲜语向白先生喊着什么,还把一张朽黄的书籍封面递给了他。
〃他说,地板底下真是一个挺不错的石砌仓室!你真的不知道?〃白先生兴高采烈地说。〃说是有好多立柱,简直转不过身来。可是里屋外屋都是通着的,外屋还有便所和井哩。他还说,这样的书籍废纸堆了不少呢。难道这里住过什么疯子或者逃兵不成?〃
我从他拿的那张污损的书籍封面上看到《三醉人经论问答大全》和东京集成社发行的字样。我茫然失措,顿感自己在一股强烈的冲击波中飘摇沉浮。这冲击使我的内心扭曲失衡,而且迅速扩大,随即化成了一个启示。这个启示直接关涉着眼下在地下室里过夜的我脑海里的一切。
〃石墙那边开了几个窗子照明用,可从外边看不见。〃白先生把钻到地板下面的另一个青年的话翻译给我听。〃不想下去看一看?〃
那分明具体起来的启示令我心旌摇动。我说不出话,只是摇了摇头。那启示的中心,便是曾祖父的弟弟在万延元年的暴动之后,并没有丢开同志,穿过森林跑到新世界去,这个发现,立刻变得铁证如山。他没能阻止同志们惨遭屠戮的悲剧,却自行惩罚了自身。从暴动溃败的那一天起,他便把自己关在地下室里。尽管他采取了这种消极的姿态,却矢志不渝地终其一生,保持他一贯的暴动领袖身份。他遗留下来的那几封信札,想来一定是他在地下室里耽读之余,追思自己青年时期冒险的幻想和现实凄苦的梦境,想象在别处生活时可能会寄出这样的信件,才把它们写下来交给来地下室送饭的人们。在地下室发现的那页书籍的封面,正表明了曾祖父的弟弟在信中所引有关宪法文章的出处。所有的信札都没有注明发信地点,是因为信札的作者就在这地下室里,他不曾离开这里半步。同样,曾祖父与他的联系,想来也是全靠书信进行的。在地下室里,他只能够熟读送进去的书报,他把自己幽闭起来,只能展开想象的翅膀,编出些横滨报上的赴美留学广告、小笠原岛附近的捕鲸作业之类的故事来打发日子。对这样的一个人来说,一旦涉及现实问题,哪怕是确认一下他藏身之处的近旁发生着一些怎样的事情,都是艰难至极。在地下室里,他徒然地竖起耳朵,企图了解一些情况,对于那近在咫尺却无法见面的侄子,他又急切地耽心其在战场上的安危,于是才会在与地面的联系信札里写上:〃乞复帖速告其安否借帖有达乞速致仆以观焉。〃
这些水落石出的新情况令我头脑热胀。我正要转身回上房,白先生却突然谈起1945年夏天的事情来。他一定是以为,如果单单是因为找到地下室而紧张兮兮,则未免过于沉重偏激,所以才一面窥察我沉默和紧张的缘由,一面想重新拉起话来的罢。
〃关于令兄复员后在部落里死掉那件事,好像还闹不清楚是我们杀了他,还是日本人杀了他。两方的人乱成一团,拿棒子乱打一气,就他一个人毫不武装、毫无装备,垂着胳膊站到中间去,还能不给打死吗。说起来,是我们和日本人一起把他打死了!那个青年,也真是个很特别的人呢!〃
白先生停下嘴来,等我的反应。我依旧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