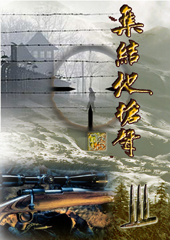运河枪声-第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凌所长,妈的小日本欺负到你的头上来了,奶奶的,我们今晚干掉他个狗娘养的。”一个粗大的满脸胡子的伪警气愤地说。
“是啊,所长,我们都听你的。”几个伪警喊起来。凌云知道现在不是他公开出场的时候,也不是他几年来用心血和汗水灌输的花朵过早开花的时候,他必须忍耐,于是很感激地向弟兄们点了点头说:“别喊了,我心里也不好受啊。弟兄们跟我直不起腰来,我们现在只有忍着。”他怕活多有失,转身走出了大门,独自来到戏院。戏院门口大多是携妻带妾而来的日伪高级官员,他随着人流走进去,找了个空位坐下。台上的戏还没开,他眼看着戏台,心里却想着别的事,他把日伪高级官员一个挨一个地在心里捋来捋去,觉得都不合适。无奈只好走出戏院。起风了,风一吹,吹起了他的头发。他一手提着帽子,一手叉在裤兜里,猛地想起了司令官的顾问官小腾一郎的勤务员寇志国,他经常和小腾一郎在一起,和寇志国很熟。寇志国是北平高等学府的毕业生,留学日本,是小腾一郎的得意学生,中日战争爆发后,他随小腾一郎来到了祖国,当了小腾一郎的勤务员。凌云想着,长长地舒了口气,心里的石头落下了,心情也立时开朗了。于是他吹着口哨大步回到伪警察所,刚坐下,敌人的夜间口令传了下来是“青年”两个字。他立即根据这俩字编成两句话,随即提了瓶酒和两样菜去找寇志国。
寇志国三十来岁,戴一副白色眼镜,给人的印象是干净利落。见凌云走来,他从屋里迎出来说:“嗬,你老兄真想得出,我还没吃饭,正想找你喝两口呢,你倒来了,好,好,咱哥俩在这儿喝点。”
凌云放下卧牛大曲,摊开一包牛肉,一包猪头肉,叹了口气。
“咋了?为啥不高兴,和嫂夫人吵嘴了?”寇志国忙问。
“不,不,”凌云沉思了会说,“我的脚气病又犯了,想找桥头所的一位朋友,给弄点治脚气的药,听说他知道一个很灵的秘方,现在不能出城,打电话又不方便。”
“哎,你这就把我当外人了,打个电话算个屁事。走,我带你去。”寇志国听了不以为然地说着,站起身来到电话室,一下子就把电话接通了。凌云忙接过话筒,先向姜赤文问了声好,说:“请(青)给我弄点治脚气的药,年年我这脚气病都犯。”随后又说了几句家常话,放下话筒,对站在一旁的寇志国说:“走,咱哥俩好好喝几盅。”
天黑了,姜赤文从桥西县大队驻地匆匆赶回伪警察所,一看表,差十分钟不到八点,他抹了下额头上的汗,饭也没吃,大步走到电话室。电话室值班的伪警正无聊,见他进来,立即拉住他说:“来,来,陪我喝几盅。”俩人刚坐下不久,电话铃就响了,那伪警不耐烦地说:“妈的,晚上也不叫老子安静点。”说着,不情愿地站起身要去接电话。姜赤文一把拉拄他说:“我去接吧。”站起身走到电话机旁拿起了话筒。他接完电话看了看表,他知道县大队急需口令。这些天,城里的特务队太疯狂了,经常深入乡村,化装成各种人员,骗取我党的情报,抓捕我党的特工人员和干部。为了打击敌人,县委决定进东光县城端掉敌特的老窝,也好使那些特务们心里有个怕字。通过情报和凌云同志的城区敌防布置图,他们选准了刚刚成立的特务大队。这个大队人多,枪多,可战斗力非常差,大多是短枪,纪律更差;他们大多没经过什么训练,是一群游手好闲,吃喝玩乐,惹祸招灾之徒;警惕性更差,是一个个民族败类,有奶便是娘的汉奸。要除掉这帮祸害,必须有确实的把握。从驻地看,特务队远离大队部,远离宪兵队和伪军大队;靠近公园,远离城中心区,打可以有依靠,撤可以有障碍。姜赤文斟满酒和值班的伪警喝起来。不一会儿,张光前和几个队员一身特务打扮闯了进来,俩人忙站起身点头哈腰地说:“长官,你们是……”
“没长眼吗?我们是城里的特务队!”张光前蛮横地说着,一把拉住姜赤文,“你不老实,跟我出来。”
“长官,长官,我哪里是不老实。”姜赤文装作害怕地随张光前走出屋,立即把口令告诉了他,并问:“同志们都来了吗?”
“来了。”张光前轻声说,“现在你必须牢牢掌握住桥头的伪警们,如桥西的伪军有行动,你必须阻止他们,不过那儿也有咱们的人在配合你。好,再见。”说完带领几个队员大步走了出去。
张光前和队员们来到城边的油口村,队员们早到齐了。走进屋,县大队高大队长正站在桌边看着地图,俩人握了握手便把口令告诉给了大家。
“好,你们干得漂亮,铁扇公主本事再大,孙悟空也能钻到她的肚子里去。”
已是半夜时分。天空无数颗星星在闪烁,风从运河刮来,刮得树枝哗哗作响。大地处在沉睡之中,显得是那么寂静。县大队和区小队个个精神抖擞地出发了。张光前和几个区小队员走在前头,黑沉沉的大地到处是青第十章县大队深夜袭击了特务队后,东光最高司令官召雄大佐便调集了孙镇、连镇、泊头、南宫、阜城、古城、崔庙的敌人,并从德州调来一个中队的日伪军,对这一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清剿,又增加了小高、大杨、芦集等十四个据点,拉网似的把这一地区严密封锁起来。一时间,进出阜东县的通路牢牢地被日伪卡住了,五区小队为了打通通往德州的道路,必须先通过小高据点,五区区小队员们个个找准了目标,开展了和敌伪炮楼拉关系的活动。
这天中午时分,在通往小高据点的大路上,张光前装扮成一个商人模样,看上去有50岁的年纪,手里提一只很讲究的手提包,身后还跟着一位年轻人,手里提着黑色提包,另一只手里提两瓶二锅头。他们是去小高据点的,据点里住有一个中队的伪军,伪军中队长孟兆五,是个比较顽固的家伙,此人中等个子,一双大眼睛,外表给人的是柔和、善良,可内心很狡猾。他原在崔庙据点当伪军小队长,小高据点建成后,他被调到小高据点当了中队长。为了牢牢控制住小高据点为我所用,张光前多次打听,终于弄明白了他的身世。他排行老五。父亲年青时也和孟兆五一样漂亮,能干,性格比较温和,善于逢场作戏,对人对事很圆滑,在天津、北京结交了一批名流人士。但他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家乡感很重,不管老家的远近人找到他,他都慷概相助。去年南宫街上一个地下党员被捕,还是他花重金保出来的,为此在南宫老家博得一个孟善人的美称。孟兆五可以说完完全全地继承了他父亲的遗传,对南宫的大人小孩都高看一眼。张光前决定利用认识他父亲的有利条件与孟兆五拉关系。
路旁的沟里有水,一只小兔子趴在水边喝着水,也许它刚刚吃饱了鲜嫩的草儿,见路上走来俩人,立时竖起双耳,转动圆圆的双眼,甩了甩尾巴,转身跑进玉米田里去了。玉米田已半人高了,整个大地到处是郁郁葱葱的庄稼。田里刮来一阵风,打着旋儿,旋起几只干枯的枝叶。前边就是小高据点了,高高的炮楼顶上,一面太阳旗在中午的阳光下有气无力地飘动着。旗下站着一个伪军,抱着大枪,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他嘴里叼一支烟,见路上走来一位头戴礼帽身穿长袍的商人,后边跟着一个提兜的小跑腿的,认为一定是个有钱的主儿,立时来了精神,拉了拉枪栓,大声地吆喝道:“喂,干什么的,走过来。”
张光前抬起头,装作没听到似的大步走着。站在吊桥边的两个伪军见了,大声地喊:“站住,干什么的?”
“弟兄们辛苦了!”张光前说着乐哈哈地晃了晃手里的兜,来到吊桥边,不慌不忙地吸着高级烟,大声地说:“你他妈的少费话,放下吊桥,快领我去见你们孟队长,要不你就叫他快出来见我。”他见俩伪军互相看着,眨着眼,又大声地喊道:“怎么,你俩没听到,怎么还不快去!”
“唉,妈的,看样子来头不小。”
“是啊,这年头和当官的沾上点儿亲戚,说话就气粗。”俩伪军说着,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慢腾腾地放下吊桥,不凉不热地说:“我们也是例行公事,快请吧,把心放到正地方就烧高香了。”
张光前看一眼身后的队员,大步走过吊桥,随伪军走过一个院门,来到一间很凉快很干净的房间。屋里有一张大床,被褥很干净,一张很新的办公桌,几把很新的椅子和沙发,屋里没人。一个小勤务员忙走进屋,很客气地让坐,拿烟递荼斟水。坐了不大会儿,孟兆五大步走进来。张光前从办公桌边站起来,扔掉嘴里的烟,上上下下打量着孟兆五,故意乐哈哈地说:“我没猜错的话,你就是孟哥常说的小五子,嗬,和孟哥长得一模一样,很漂亮,一看就是个说话办事干净利落的人。”说着他跨前一步,拉住孟兆五的手说:“我和你家老爷子是在北京、天津经商时多年的交情了,知道你到这儿来了,特地来拜访你,也好尽到我这做长辈的地主之谊。”不等他缓过神来,转身便和另一个区小队员一起从提兜里掏出菜,摆了满满一桌子。俩人坐下,张光前撕了一只烧鸡腿递给孟兆五,又斟上一杯酒,举着酒杯说:“来,孟队长,干一杯。”说着很大方地一昂脖喝下去,又自我介绍说:“我们是北边大高村的人,刚从天津经商回来,不想去了,想回到家里享几年清福。来,孟队长,你年轻有为,前途无量啊,再干一杯。”喝完又说:“有机会请到家作客,草屋茅舍的还有几瓶好酒,不过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话你就尽管说,我们又不是外人。”
孟兆五转动着一双大眼睛,望着热情的张光前,心里想,这些天四处公路经常被破坏,电话线常常被割断,经常和四周据点联系不上,我正在担心城里上司知道不好交差,为地方上没有一个自个儿的人着急,如今老天有眼,给我送来一个父亲的老朋友,立时觉得肚里有了点儿底。他叹了口气说:“大叔,我这个中队长也不是好干的,个人有个人的苦啊,唉。”
“哎,我说孟队长,有难事尽管说。”张光前拍着胸脯,慷概地从兜里抓出一叠票子说,“要钱花,咱有的是,这点钱你先用着,等明天我亲自给你送过来。”
“唉,我说大叔啊,不是缺钱,而是经常和四处失去联系。”孟兆五因多喝了几杯酒,脸有点儿红了。
“这好办。”张光前故意四周看了看,低声说,“孟队长啊,你担心的事也是我老早就担心的事。”他站起身又往前凑了凑说,“你初来乍到,要想在地方上站住脚跟,就得处处多长几个心眼,心眼也要活一点,用咱这儿的话说,就得找个靠山,不然的话,八路那边可是不好对付的呀。”说到这儿,见孟兆五有些紧张了,立时改口,显得很自然地说,“这没关系,在咱这地面上,我可是人地两熟啊,是可以帮忙的。”
“真的?”孟兆五来了精神,这几天他正为此事焦急,又怕出事向日本人交不了账,如今听张光前这么一说,仿佛吃了定心丸,连连道谢:“大叔,请你老多多关照。”
“好,就这样吧。”张光前又一拍胸脯,对孟兆五说,“那么我就不多呆了,赶紧回去活动活动,晚上你到我村北大杨树下去一下,我给安排一下。”说着站起身和区小队员走出了炮楼。
孟兆五站在吊桥上望着渐渐远去的张光前二人,久郁的心病现在全好了,他得意地笑了笑,点燃一支烟,望一眼炮楼顶上的太阳旗,嘴里哼着小调,回到屋里。勤务兵正在收拾桌上的东西,他端起水杯喝了口说:“小六子,剩下的半瓶酒你喝了它算了。告诉伙房叫他们晚上早早做饭,我还有事出去。”说完躺在床上。
天快黑了,小勤务兵端来水,拿来毛巾。他从床上爬起来,洗了脸,刷了牙,换了身崭新军装,扎上皮带,挂上枪,站在镜子前上下左右地照了照,他知道见面的一定是共产党的大干部,要给对方一个好的大大方方的印象。他见小勤务兵端来饭菜,边擦手边坐到桌边说:“你也来一块吃,吃完跟我出去。”他了解这小家伙,在崔庙据点时,一次随日军扫荡,发现这孩子在一条小河边的死人旁哭泣,不知是为啥他起了侧隐之心,也许是心血来潮,便把他收在了身边,给他起名叫小六子,从此他身边多了个机智灵活有说有笑的小家伙。
天黑了,孟兆五和小六子走出据点。天上一轮半圆形的月儿,路边有蛐蛐在叫,田里偶尔刮过阵阵轻风,给人幽静之感。前边不远就是大高村了,村子被周围的树木包裹着。孟兆五下意识地摸了摸腰间的手枪,心里不由自主地狂跳起来。一时间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