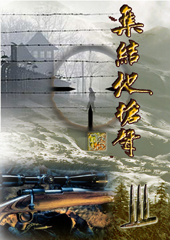运河枪声-第5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鸣着汽笛从河里由南向北行驶着,艇上一挺闪着蓝光的机枪对着前方,一个二十多岁的兵士紧紧抱着。他有一张娃娃脸,眼睛里闪动着幼稚、单纯,更多的是无知。从船舱里探出头来的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军官,他满脸胡子,一双不大的眼睛给人的是阴森,奸滑。一只太阳旗吊在船头,如同孩子的破尿布,疯狂地摆动着。船后的河水翻着浪花,两岸是郁郁葱葱的花草,各种颜色的花朵含着微笑,默默地望着汽艇。多美的风景。突然船头的机枪响了,一串子弹从她的身旁飞过。她立时拔出手枪,躲在一棵大树后,又无可奈何地把抬起的枪口放下,长长地叹了口气。她在为自己国家的前途担心,为死难的兄弟姐妹悲伤、哀叹,更为自己流落异国他乡而苦恼。家乡是多么美好啊!可有多少兄弟姐妹有家不能回,有多少兄弟姐妹的家被毁,被一个个强征来做了无畏的牺牲品。她站在堤岸上,风从远处吹来,吹着她头上的头发。
“你的什么的干活?”一队兵士突然大踏步地走过来,见松川美子站在河堤,他们嚎叫着围了过来,一双双色迷迷的眼睛望着她:“花姑娘的,大大的美丽。”一个小队长龇着满嘴黄牙凑上来,“中国的花姑娘,我们的统统地受用。”他凶恶地挥了下手。
“啪啪”,松川美子狠狠地给了他两记耳光,愤怒地用日本语骂了他们几句。他们仿佛接受到命令似的,立时规规矩矩地站在她的面前,同时那个小队长忙立正敬礼。松川美子狠狠地瞪他们一眼,骂道:“败类,纪律的大大的不行,你们统统的开路,我的有事的干活,你们统统的破坏了。”说着怒气冲冲地从衣兜里拿出特别证件晃了晃,又拍了拍怀里的双枪,扭身走下河堤,向城南门走去。
城南门楼脚下,增加了岗哨,一个个进出城的人们正接受着检查。仿佛发生了什么事似的,便衣特务也布满了门口内外。不好,他们一定有什么行动或正在抓捕一个什么人物,莫非是王宁小队的人,还是区小队张队长他们?她的心提到嗓子眼上来了。她总觉得面前这场即将发生的事和自己有关似的。她四周看了看,见没人注意她,悄悄地打开机头,随时准备用她的血甚至生命来保护她们。
人们一个个从城门口走进走出,有男人有女人,他们一个个小心翼翼,提心吊胆。在几个伪军的身后,站着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他满脸黑色胡子,一双小眼睛瞪得大大的,如同一只狼盯视着一个个进出城的人。这个人一定是共产党的叛徒,正在等待出城的某个人。松川美子想到这儿,眼前出现了漫河村惨案的场面,不行,一定要救出这个还没露面的人,我必须马上进城。但转念又一想,自己站在人群面前也不会知道他们要抓的是哪一个,自己脸也上没写着是救他们的,而对方身上也没有标志。她为难了,站在不远处望着一个个进出城的人。天空一只雄鹰在飞翔,它扇动有力的翅膀。“怎么办?”松川美子紧锁双眉,久久地沉思着。她没有想到,站在特务们身旁的人是城里小卖部里的老板,地下共产党员尹久山,他出生在上海一个富商家庭,参加过北伐战争,上学时多次接触马列主义,参加过反饥饿反迫害的学生运动。他的两个哥哥,一个参加了新四军,一个参加了国民党。由于在北平他暴露了身份,组织上及时安排他来到这个小县城做地下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北平来的一个特务认出了他,没几天他便被抓了。敌人想从他嘴里掏出情况,起初他什么也不说,敌人引他看了各种酷刑,他胆颤了。当他来到一间小屋,见一位三十来岁的八路军战士,被高高地吊在梁上,打得遍体鳞伤,他吓得闭上了眼睛。再问他,他还是不说。敌人恼了,一壶辣椒水下肚,他顶不住了,便把知道的情况全说了。敌人如同一群疯狗,一下子抓了好几个党员。我党及时得到消息,把一部分联系点撤掉了,才使大批的地下党员和干部躲过了敌人的大搜捕。敌人知道城外的共产党还不知道,便在几个联系点上布满了敌特抓捕来联络的人。前天一个书生打扮的人突然闯入,来人很机警,发觉情况不妙,又见几个陌生人出现,立时开了枪,以他的勇猛、机智和灵活的身手逃走了。敌人也猜到我党必将派人出城报信,但从哪儿出城不知道。这些天敌人四门都增加了岗哨,把几个叛徒统统分派到四门,以便认出党员和干部加以诱捕。松川美子望着城门里的敌人,焦急地想着应对的办法。天渐渐地黑了,她远远地发现一个头戴礼帽的教书先生模样的人走来。她知道,他们大都是这身打扮,无论是与不是,决不能使他落到敌人的手里。她沉不住气了,猛地大步向城门走去。这时一位四十来岁的女人,挎着一篮子水果来到城门口,当她发现了特务身旁的人时,转身向回走去。
“就是她,快抓住她!”叛徒大喊一声,呼啦啦特务们扑了过去,她被敌人抓住了,她挣扎着。
“叛徒,我让你出买同志!”松川美子不能等待了,但她没想到敌人抓的和她判断的竟是两人。她火了,她不能眼睁睁看着一个女人落在他们手里,立时拔出双枪冲了过去。敌人没有防备,还没闹清是怎么回事,便大部分倒下了。她冲到被抓的女人面前大喊:“我掩护你,你快跑。”突然一颗子弹打中了她的胸部,敌人喊叫着围了上来,两人被包围了。“同志,你、你!”那女人扶她躲在一座土砖门楼旁,责备地说:“你太胡闹了,这不是白白牺牲自己吗?我们的党还需要更多的同志。”
“我,”松川美子强打精神,推开她,翻身向冲过来的敌人射击。“我是日本人,叫松川美子,认识你们党的好多人。我来救你,你快走吧。千万别管我,我不行了。”说着她的双枪又响了。
“你们投降吧!”敌人开始射击了,她的胸部又中了两弹,血从她的胸口流下,染红了她身下的土地。一个日本正义的女人,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干部,洒尽了热血,闭上了一双美丽的眼睛。“美子,美子!”中年女人双手抱住她,血染红了她的衣服,她轻轻地摸着松川美子苍白的脸,捋了捋美子额前的头发,轻轻地把美子放平,慢慢地脱下一件上衣,小心地,轻轻地给她盖到身上,又慢慢地转过身,望着逼近的敌人,突然抓起美子的双枪,连同整个身子向敌人扑去。
“抓活的,快抓活的!”敌人乱喊叫着,忽啦啦向她冲来。
“狗日的杂种!”她的枪响了,一个敌人到了,又一个倒下了,枪只响了几下,子弹打光了。她把枪甩到一旁的房顶上,迎着敌人的枪口冷冷地笑了。
她面对敌人的枪口,向周围的群众大声喊道:“乡亲们,我们共产党人是抓不完的,为了民族的独立,为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我们会一直战斗下去!”
“八格!”一个日本军官大步跨到她的面前,“啪啪”就是两记耳光,“统统的快快的带走!”
“啪”,她又回敬了对方一耳光,冷冷地说,“强盗,中国人是杀不光的,叛徒是得不到好下场的。”
日军小队长发怒了,猛地抽出战刀。叛徒走过来,媚笑着说:“太君,太君,她的八路交通员的是,情报她大大的明白。”
“你的明白,功劳大大的!”日军小队长拍着他的肩哈哈大笑了。
“呸,你这个叛徒,民族的败类,人民会惩罚你的。”她被敌人捆绑起来了。她怒视着敌人大声地喊着:“老乡们,我们只有团结起来。”她被敌人推着打着,“刘向南这个软骨头,叛变了革命。我们要记住松川美子小姐……”她的话没有说完,几个特务把她的嘴堵上了。此刻她望见了远处的县委书记,他望着她,用信任鼓励的日光。她装作没看见,怕叛徒认出了他,立即昂首挺胸地向前走去。
县委书记难过地低下了头,他随着人们走向松川美子的尸体,他作为一县之长,要看一看这位伟大的日本女人,要叫我们的党记住她,为她竖起一座丰碑,世世代代永远怀念她。
第三十四章敌人残酷的屠杀和镇压,使大部分村庄被毁,房屋被烧,树木被砍,村庄处在一片碎砖烂瓦之中,毫无生气,到处是面黄肌瘦的农民,没有了狗的叫声、牲畜的叫声。整个田野里的庄稼经过几次大战斗,大都倒伏,如同一个美丽漂亮的女人穿上破烂的衣服。本来今年是个好年景,却被鬼子和特务们破坏了。李越站在村边,望着青纱帐,望着弯弯的田间小路,望着高高的运河大堤,不觉长长地叹了口气。最近的形势越来越紧张了。上级党组织任命他为五区区长。他想到了尤区长的牺牲,区小队被打散,好几个小区的干部被杀,工作已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了。他倒背着手,皱紧眉头,一步一步向深深的田间走走。他知道这时间田间人很少,没人打扰他,他要静一静,认认真真地想一想,思考一下怎样才能更好地开展工作,把工作搞好搞活起来。看得出农民心中的恐怖和担心。我们党的干部有的叛变投敌,出买了同志,用同志们的鲜血作为进身的价码。一个个革命同志被敌人杀害了,他们面对敌人大义凛然,宁死不屈,多好的同志。区里一时失去了指挥,使大部分农民感到失去了依靠,心里空落落的。一时他觉得身上的担子加重了。他慢步走着,来到一片很整齐的玉米田边,扶着一棵粗壮的玉米,摇了摇,觉得沉甸甸的,一阵风吹来,刮得玉米叶子发出哗哗啦啦的响声,仿佛有人在跑动,他一愣,是啊,快秋收了,庄稼人一年的血汗快到手了。我们的战士们打仗行军需要吃饭,百姓缺粮,面对快熟的庄稼他们没有行动。敌人也需要吃饭,需要粮食,他们必定要来抢粮。我们必须要快打快藏快快地征收送入部队。必须组成一个强有力的班子,配齐人员,保卫秋收,保证顺利抢种,这就需要人和武装。现在要人没人要枪没枪,时间紧迫,刹那间他浑身急出了汗,不能再沉着了,必须发动群众,组成武装人员着手护秋工作。
夜已经很深了,小船似的弯月斜挂在天空,在一片片的浮云中航行,天是那么的静,四周没有一点儿声音。整个田野如同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沉默着。只有蛐蛐伏在田野宽阔的胸怀里幸福地欢唱着,给田野增加了一点儿生机。这时区小队长徐光军从韩村开完会走出村庄,心里久久地不能平静,他觉得肩上的担子沉重。为了保护秋收,新上任的李区长和他们一块研究了整整一天,把各种有利的和不利的都估计到了,到如今还有没有给敌人造成有利可逞之机呢?他的脚步显得沉重起来,下意识地摸了摸腰间的枪,一旁的通信员仿佛也产生了感应似的,也下意识地摸了摸腰间的双枪,睁大眼睛仔细地望着四周。田里到处黑沉沉的,只有风儿轻吹,到处灰朦朦,冷清清,远处仿佛有一片乌云压了过来,像人像鬼,在晃动;这环境,这气氛,这形势,不能不使两人心里上产生一丝阴森、恐怖和压力,更使两人增加了百倍的警惕。两人谁也不和谁说话,四只眼睛闪动着,两人的脚步一时显得轻快起来。人也许是一种怪物,当他仿佛意识到什么后,整个身躯,思想,行动,都会处在一个高度紧张、机智、灵活的状态。突然一只野兔从一旁的田里蹿出,很快地钻入另一块田里不见了。“有人。”徐队长轻声地说了声,两人同时跳到路旁的沟里。这儿有一个深深的被雨水冲刷出来的沟,两人握紧枪,注视着四周的田野。四周蛐蛐起劲地唱着,风在吹,偶尔传来一声野兔的叫声和响动。“队长,没啥事吧?”通信员闪着一双大眼睛望着自己的队长。他知道:队长在勃海支队当过战士、班长、排长,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有指挥才能和组织能力,遇事沉着果断。徐光军扭头望一眼小通信员轻声说:“别说话,注意观察。”
通信员伸了下舌头,扭头望着弯弯的小路,小路如同一条白带,从青纱帐的怀抱里伸展着。徐队长把耳朵贴在路边,仔细地听着,又仔细地看了看四周:“有动静。”通信员也学着队长的样子听了听,才隐约听到轻微的脚步声。他敬佩地看了队长一眼。这位十八岁的小伙子,也是勃海支队的一位小战士,人虽小,但大大小小的战斗也打了不少。他是徐队长收的兵。那天部队路过一个小村子,这个十五岁的孩子,站在路旁,眼泪鼻涕地要求参军,由于年龄小,部队首长不同意。当时徐队长带领全排做收容队,望着这个机灵的孩子,高兴地摸着他头,笑着说:“小鬼,为啥哭鼻子,这不叫这么多叔叔笑话吗?”
小家伙见有人主动和他说话,立时止住哭,睁着一双乌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