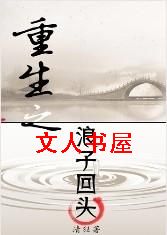回头无岸-第2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卖也卖不卖也得卖!”他们狼笑着扑上来。
我憋狂了,一步跃上窗口,仰天长啸一声,一个跟头栽下去,一时天旋地转……
真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想,钱啊钱,你这个魔鬼!我起身来到阳台,让凉风吹干了我浑身的虚汗。我想来想去,决定还是去找王文革借点,他小子既然极力纵恿我下海,总不该见死不救吧。还有赵卫彪、贾卫东他们那里没准也会拉兄弟一把。
我第二天早上找到了位于滨河路王文革的“爱心花店”。他刚开门,那个在舞厅上班的妞儿正和他一起把花盆往外搬,一边浇些水。我向他倾诉了贷款遭遇,满脸通红地提出了我的要求。朋友就是这样,绑他玩蹭他吃理直气壮,借钱真是羞于启齿。好在王文革慷慨地掏出五百元塞给我并对我说:“别跟我提借钱,这五百元算我赞助你的。实在不好意思,你看,生意秋,费用高,我手中也紧。”
我还是坚持给他写了张借条。他也不容易。我找到贾卫东和赵卫彪时他们面有难色。贾卫东解释说:“太不凑巧,我们刚换了一台新冰箱和消毒柜,原来那台冰箱是从我家借来的,上月房租都还欠着呢--没办法,现在是欠帐成风,饮食诈骗犯又多,真是赔本赚吆喝!”
“朋友分为可以借钱的和不能借钱的。”我恬着脸激他们。
“你他妈的什么意思?连我们都信不过?”赵卫彪也诅咒发誓,“我他妈谁骗你谁是汪国真!”贾卫东这时灵机一动地向我建议:“说实话,你找我们借钱真是找错了对象,白成富才是大财主,不是他来照顾咱们,恐怕早就关门了,你去求求他,没准看在舒怡的面子上,一高兴扔给你万把块的,连条子都不带打的。对,你去找他绝对没错!”
“呸,老子就是落得个乞丐,也绝不会上他的门。”我勃然大怒,掉头就走。
“别发火呀,等这月底来看看吧。”他们在后面嚷。
此后一段时间我百无聊奈,就和王文革沆瀣一气,白天帮他送送花,晚上常常和他喝得烂醉如泥不省人事。但被麻醉的神经一旦清醒,我便感到加倍的空虚。看来他的生意的确不行,上门买花的寥寥无几,他雇的那个小工沿街叫卖常常半天不开张,他的女朋友的舞厅只用可反复使用的塑料花,这样,主要希望便落在电话、传呼订购上了。这几天他把中文传呼挂在我身上,由我来充当护花使者。若有生意,我便会收到客人或王文革的指令,将某花在某时送到某地某人手中亲收并传递某某口信。但令我们沮丧的是,在蒙城这座缺乏情调的城市,他的生意显然有些超前了。尽管他一再追加广告费用,广播、电视、报纸、传单、海报轮番轰炸,一齐上,极尽煽情献媚炒作之能事,可依旧是对牛弹“情”--在讲求实惠的蒙城女士小姐们看来,与其花十几二十元买束鲜花送她,还不如请她下馆子一顿海吃划算呢。
“傻男人!还没结婚呢就奢华上了,一束花可以买两双长统袜呢,趁早吹灯!”一个瘦骨嶙峋的娘们在签字领红玫瑰时嘟起嘴抱怨。
“十元?太贵了!现在猪肉才五元一斤哩。”一个肥婆子暴跳如雷。
“小姐,你说的也是。依我看,若买槽头肉可以买七八斤,够一家人狠吃一个月呢。不能这样算帐,猪肉有价,情调无价嘛。”我一时兴起多嘴了一句被她恶狠狠地白了一眼,连几毛钱小费也免了。
还有一个住院的老太太索性拒绝签字领康乃馨,还骂我棒老二活抢人,直到把我轰出了病房……每天没卖完的高档花只好扔掉,我们痛心得直骂蒙城俗气的娘们。
但始终有一个每天买花的忠实顾客,那就是白成富,全是送给舒怡的,只是我从来不去送,那几天我没勇气去见她,但我无时无刻没惦念她和她渴望的钢琴。
生意每况愈下,王文革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我想来想去,觉得没有理由老是混他的饭吃蹭他的酒喝,他连小工都辞了,而且那张双人床也容不下三个人分享。我趁着他还没有烦我便不再去找他了。
十五
余下一段日子我又相继策划了几笔生意,开服装店、皮鞋店、礼品屋、体育用品专卖店、冷饮店、休闲屋、电子游戏厅、台球室、贩大米、倒麻袋……皆因为资金不足而化为泡影。何不利用自己的专业呢?可当时蒙城的外资企业几乎为零,国际旅行社揽的大多是国内活儿。所以,那家经济开发区给我颁发的英语翻译聘书和国际旅行社给我的特约导游证均因为没有底薪而完全成了一张废纸。那么我办个英语培训班吧,这倒花不了几个钱,无非是教室租金和资料印刷费,成本很低。可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广告张贴出去还不到两天,便有一帮捞外快的中小学退休英语教师联名把我告到市教委、工商局、消协、税务局、市长热线办、信访办、电视台、报社、打假办、严打办、派出所、居委会、联防队、小脚侦缉队,还油印散发了几百份致学生家长书,说是有个被单位开除的社会闲散人员、严打嫌疑分子居然、竟然、悍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擅自搞什么英语培训,误人子弟,他们出于职业的道德,家长的信赖和社会的良心,强烈要求有关政府机关严厉查处,公开曝光,将李犯亚非捉拿归案,为民除害,绝不手软。还教育一片净土,还教师一个清白!……该犯鹰勾鼻、络腮胡、尖嘴猴腮、贼眉鼠眼、头发卷曲、面黄肌瘦……警惕啊!善良的人们云云……
后来我想我的特长是侃,何不玩空手道再邀约几个侃爷开一家洗脑公司?这个思路倒很前卫!国外就有,有点心理咨询、心理诊所的性质。现在人们面临日趋激烈的生存竞争,心理压力越来越大,有心理障碍、心理疾病的人大有人在,这是个不可限量的市场。关键是几乎不用什么大的硬件投入:几间小屋、几张桌椅、几个茶怀、几盒清凉油、几盒润喉片、几张毛巾(供嚎啕大哭、觅死觅活者)、几个沙袋(供勃然大怒、无处渲泄者)、几件“自慰器”(供性压抑者)--齐活啦!开张啦!来的全是客,全凭嘴一张!侃呗!直到侃晕、侃舒坦,侃得一通百通、一了百了,侃得顾客拼命自个儿掏银子还感激不尽为止。结果工商局根本不给我注册发执照--他们不无嘲讽地说,在我国现行法律允许经营的范围中,根本就没有这个荒唐的野鸡项目!心理咨询?可你又没有行医证。唉,真是有钱就是男子汉,没钱就是汉子难!
正当我一筹莫展烦躁不安之际,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光顾了我,原来我托武汉的一个亲戚为我在深圳找工作的事有了着落。一个在深圳的台湾公司在武汉又和他们单位办了家合资公司,我前不久寄给他们的个人资料他们比较满意,但据说由于港台对大陆文凭和学历历来都不承认--据说是高文凭低能力。加之近年来“克来顿大学”在沿海频频出现,更加剧了他们固有的成见,所以台湾老板要求面试,若合格就正式聘用。我避开家,跑到邮局,花了三十四元和那个台湾老板的助理孙仁先生通了电话,谈话间他用一种洋泾滨把他管理的公司说成了大陆青年没有理由不立即投奔的圣地,他还以不屑的口吻说了不少大陆国有企业的坏话。我不敢不迎合他。客观地说,他说的也不是完全没道理:产权不明、体制不顺、机制不灵、管理不善、奖惩不严、设备不新、素质不行……
我估摸着卫超可能已经收到了我的信了,就立即再给他打了个电话。我给他讲了我的打算,他鼓动我立即出发,机不可失,吃住他暂时可以解决。他还警告我,不久又是大学毕业时间,又有一大批学生涌到深圳,竞争会更加激烈。他还建议我乘飞机去,别舍不得六七百元钱。我答应尽快行动,到成都买了机票再给他拨电话,他好准时到机场迎接。
我兴奋之余不禁又忧愁起来,虽然对家里人我可以不辞而别,但舒怡又怎么办?难道她也愿意和我一起浪迹天涯?我想起那晚上白成富的妈说要帮她改行,不知这一段时间又对她许诺了什么。王文革曾警告我白成富追女人有苍蝇觅食般的勇敢,他要取胜的办法令我一想起来就心惊肉跳。我料定这段时间白成富绝不会闲着,我宁愿相信天上掉馅饼,也绝不相信世上会有白吃的午餐!他一定……想着想着我就坐不住了。我来到一个磁卡电话亭给她打电话,女校长照例说上班时间不许打私人电话就挂了。我等了一会又拨通,捏了鼻子拿腔捏调地说我是市教委的,女校长一听立即笑嘻嘻地讨好买乖地问我是谁,她好象不认识我。我说我是刚从山药县调来,舒老师的大学同学。蒙城上上下下的权力均为山药人掌握,这点她深信不疑。在蒙城,如果要进衙门就象到了山药县办事,到处都是操浓重山药腔的人,如果操一口山药腔,你顺利得多。果然不到三分钟,舒怡就过来接电话了,劈头就说:
“我就知道是你。”
“我正式下海了。”我说。
“真的呀?什么时候?”她大吃一惊。
“前几天,手续都办了。”
“你这一段时间在干什么?怎么没见到你?”
“看了几家门面,没谈成,我想暂时开家小吃店,积累点资金再说。”我说。
“你疯了!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也不和我商量一下?”她骂我。
“对不起。我早就说过,你以为我是说着玩的?”我又问道,“怎么,你有何感想?”
她缄默了一阵,只说了一句:“忍看朋辈成新鬼!”
“我想晚上见你。”我说。
“没时间!”她生气的语气。
“是不是白大公子有什么节目呀?”我笑嘻嘻地问。
她并不回答,只说:“你九点以后来吧。”
我正要问为什么,她却把电话挂了。
我九点钟敲开舒怡的家门时,她母亲似乎冷淡了许多,既不打招呼,也不正眼看我,甚至连笑容都消失了。我硬着头皮兀自走进舒怡的小房间,她正坐在那里对着墙发愣,连我走近她身边她都浑然不觉。我一眼就瞥见花蒌中又多了许多束花,就说:“今天晚上我真不该来,让你们扫兴了,早知如此我就不来了,不好意思。”
“来都来了还说这些话。”她转过身子。
“白大公子待你不薄呀!买这几束花得花我一月的工资吧?何况天天送,真气派嘛!不过这对他来说也不算什么,别人通常抽极品云烟,最次也是玉溪嘛!我吃了上顿愁下顿,他却奢华成这样。”我转悠到花蒌旁,嗅了嗅,又说,“牛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伤害劳动人民感情嘛。”“我才不稀罕他的花呢?”她冷漠地说。
“那还留在这里干什么?”我不解地问。
“我不让他送,他不听。”她说,“天天送,讨厌!”
“真的?”我一边问一边恶毒地亵玩猩红的花瓣,“那么我帮你个忙好不好?”
“什么?”她不解地看我。
我取出鲜花打开窗户,一下子扔了出去。
她大吃一惊:“你干什么?”
“怎么?舍不得?可惜了?那种酒囊饭袋也想玩点贵族情调!”我冷冷地骂道,“一九四九年起就没有贵族了,贵族装是装不出来的,谁也甭想在我面前冒充大尾巴狼。”
“你这个人才多管闲事瞎操心呢,别人送花给我,我喜不喜欢是我的事,你着什么急?莫名其妙!”她盯着我笑。
“那好,现在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就算我多管闲事自作多情莫名其妙,我现在就出去给你捡回来,总可以了吧?”我说完往外走。
“过敏症,等着,我们出去走走。”她一把拉住我的衣襟,娇嗔道。她穿上高跟鞋,整理了一下房间,就和我往外走。
她妈当着我的面责怪道:“这么晚了还要到哪里玩去?你明天还有早自习课,早点回来!”
直到我们下了楼梯她妈都还在絮絮叨叨地叫她早点回家。下楼后我就看见那两束玫瑰花躺在那里,我一时火起,几步走上去,用那双破皮鞋狠狠踩了几脚,嘴里骂道:“还想玩情调!草包!草包!连西方都说培养一个贵族需要整整三代人的努力,何况这是在中国!他什么东西!才穿上皮鞋几天,就想来点罗曼谛克!非洲人跳芭蕾!不合国情!”
然后我们向小松柏林走去。舒怡在一旁笑:“现在是你着急呢还是我着急?花你可以扔下来,钢琴你又怎么扔呢?”
“什么?他要送你钢琴?”我惊呆了,“是不是你让他买了?”
“我没说。不知他从哪里听说的,可能是贾卫东赵卫彪那里。我不要,他执意要送,也怪我妈背着我答应了人家。我想了想不要白不要,反正别人有的是钱。”她说。
“你敢要!”我大声说。
“那是我的事,你管不着。”她摇着膀子踮着脚尖说。
“我就要管!”我大声嚷道,血往脑门上冲,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