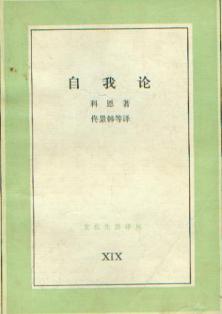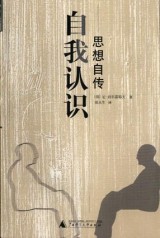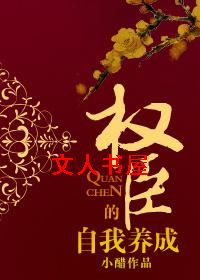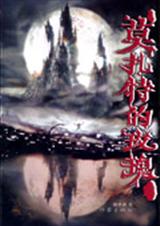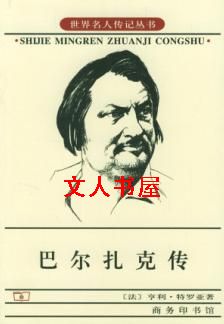���ҵ�����-��44��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ѣ����������IJ��쳣������ij���������ϵ��������������¡���ʵ�ϣ�����ķ���۵������������Ȥ�����⣺��dz���������һ��������֢������ɵ���������������ڴ˵�������������֢���̵Ľ���أ�����ǣ������ڷ�dz������������ȱ����ȡ������������������
������������������ġ������������������۲�Ľ����Ρ���Ϊ����IJ��˳���Ҫ����������ԶԴ���һ���۲�����������ġ������dz����Ĺ��̷�չ�ú���ȫ����ȻҲ�Ͳ���������ƵĶ�������������еû����������������ǻ�ϣ�����Լ���һ�������ģ���Ϊ�������ܵ������ϵ��ϰ����Լ������ϵķ���ʧ��������֮���ţ������Ծ������á��������վ���������Ҳ������ʶ���Լ�ÿ�����µ����Σ�����˶���з��š��ڷ����У�ʹ���Dz�����һ��ӡ��ģ�����������һ������ĵĹ۵������������������Խ�ֹ�ڱ����϶��ѣ��ƺ�ȱ���������ϵĺ����ģ������һ�Դˣ�����ǻ�����Ľ��ͣ�ֻ�Խ�Ǯ�������йص���������Ÿ���Ȥ��������Щ�����������������Dz����ϵĸ���Ҫ�㡣������ǰ��������ȴ��һ�㲽���������������������ഺ�ڻ����ഺ��֮��������һ������һ�ν����ʱ�ڣ��������й������ķܶ�������������ijЩ����ϵ�ʹ�ࡣ�ⲻֻ�DZ�ʾ��������IJ�������Ҫ�ȸ���ķ�����ŵ�Ҫ��Щ������Ҳָ�����������ʱ�����Ե���������֢�Ľ����
��������������ʱ���ͻ����ֳ��������ǵ��λ������ѵ�����֮�����һ�����Ե�ì�ܡ����ǵ������ر�������е��������ҡ���Щ�γ������¶�����������صı������Ժ���Ա��˵����ޡ�������ʧ���ͽ��ǡ����仰˵�����볣�����������£���������ij�ͻ����̵���С���������ͼ�������Ƕ���Щ�ε���Ȥʱ�����ǻ����������ǵ����������ƺ�������������ȫ������������ϡ������������˽⣬��Ȼ������ν�߳��ķ�dz�Դ��ڣ�������ȴ�Ǻܿ�����Զͣ�������������Լ�����������С����Ƕ�������Լ��Լ��ĸд�ֻ�ǴҴ�һƳ��Ȼ���漴����˫�ۣ�һ��û�������κ�����һ��������Ϻ��ڵ���У����ɱ������������ӿ�������ѵ������ϣ�ijЩ�����ʹ�����ǿ�����ijЩ������ڽ����Ҳ������Ȼ���ֳ��������漴�������ˡ����ڵķ��������ȷ������Щ�۲죬ȴ�롰Сë�������ֹ������ì�ܣ�����ָ�������Ǿ���Ҫ�����Լ������˸�����ġ�
����dz�����Ϊ������֢���̵IJ��ҽ�������Ԥ�������ƴ����˽��ֹ۵�չ����Ŀǰ������dz������Ƶ������ʱ�����ܽ�֮��Ϊһ���ϰ�����ֹ���ļ�����չ����õ��൱���۵ġ�����Ԥ����������һ������֢��Ԥ������������й��ⷽ��Ĺ�������Ҫ���������ϣ������Եģ��ر�����ѧУ����Ҫ��������Ԥ��������
������ȴ�͵IJ��ˣ����ȱ��轫���������Ϊ������֢���ϰ������ɽ�����Ϊ�ǹ��еĻ�ϵ�����ɵ����Զ����Ժ����ˡ����ߵĹ����ʾ�˴������������ת��ģ��������������ھ����ҽʦ���ܽ�������⡣��������������֢����ϲ������˽⣬��֮�ϲ�������������Ȥ��������Ҫ�ж����ڴ��ֹ������������������ϰ������ѹ�Ƹ��˵������ȴ���ֵ��൱�����ԣ���˽ϲ�����Ҫ�����ơ���һ���ɣ������ɴ˱��������Ĵ��ϰ���ȴδ�����뵽��˻��������йأ����У������ҽʦ����ȫ��Ϥ��Ψһ���أ����ǡ����������ϵ��������������ȴ����һ�ְ�������Ĺ��̣��������Ͼ����������������������ѡ�ֻ����ȫ�˽����������Լ������������̵�ǰ��仯�����ܳɹ��ؽ����Щ���������ѡ�
���ġ���
���ˡ���
���顨��
���ݡ���
������
��˵����
���¡���
���ء���
��������
��ʮ���¡��˼ʹ�ϵ�ϵ������ϰ�
�������ĵ��Ը�ϵͳ������֢��Ҫ���Լ��������ã�����֢���߲�ֻ�ͳ�ͻ�Ե��۹��������Լ��������ԡ��������ġ���ԭ�����������ˣ����DZ��˵�����Ť���ˣ��������Ҳ�Եø��ް�ȫ�У��Եø�Ϊ��������������
����Ϊֹ��������Ȼһֱ��ǿ�������ڵĹ��̣��������ǵ������У�ȴ���ܽ���Щ�������˼ʼ�Ĺ��̸��������Dz�������������Ϊ�����ֹ�����ʵ�ϱػ�˴��Ӱ��ġ�������һ��ʼ�������ǽ��ܡ�����֮̽��ʱ�����Ǿ��˽�������Ԫ�أ�������Ҫ��������Խ�Լ���Ҫսʤ���˵ȣ�����ֱ���й����˼ʼ��ϵ�ġ������ڵ���Ҫ������������֢Ҫ����Ҫ������������˵ģ����Dz���ֻ��������֢���Ը����������ǵ��������㣨�����ܹ����ԣ����������ϵ�����е�Ӱ�졣����������ÿһ��һ���������ɱ������ơ�������Ҳ֪�������������θ������������Ǵ��˵�̬�ȡ��������Ҳ���۹���ÿ�����ڳ�ͻ����Ҫ��������������ϵ�������ֵ����ֽ��������ʽ���ڱ����У��������Щ����ķ���ص����ձ��Եķ��棬�����Ը�ϵͳ��ԭ���������Ӱ������������˵Ĺ�ϵ����һ��Ҫ��ϵͳ���о���
���ȣ��Ը�ϵͳʹ����֢���߱�á�������Ϊ���ġ����������ӱ�������ȥ��Ҫ������⣺��ν���������ġ����Ҳ�����ָ��˽�����Ҵ��꣬����ָֻ���Ǹ����Լ���������ԡ�����֢���߿������������˽�ģ�Ҳ���ܼ��䲻��˽�����ⷽ�棬���е�����֢������ν�������ԡ��������Ǽ������������ĵģ�ֻȫ���ػ����Լ����ѣ�Ȼ�������ڱ����ϲ������û����Եر��ֳ��������������Ǹ��¶���̰�����ˣ�Ҳ����Ϊ�����˶����������������Σ�����ƾ�������˵������������뻯��Ӱ������ع������Լ���ԭ�����ġ�Ӧ�á����������Լ������Ը�����ǽ�ڣ�С�������ط����Լ����Եֿ������Ļ����ڵ�Σ�ա����������ֻ�����й��������Ҹ����ڽ�������Ϊ���뼺��ͬ����������Ȩ���ĸ��塣������������������Ҫ����������ϵ�����Լ���
��ˣ����˵�������ģ���ˣ�����δ��Ť����Ȼ�����Ը�ϵͳ����������һЩ���أ������ҵ�ʹ���������˵�ʵ����״���������ˣ���ȴ�����ؽ����ǵ�����Ť���ˡ����Dz��ܴ��ݵ�˵�����ǶԱ��˵Ŀ�������ͬ�������Լ��Ŀ�������ģ��������ͷ�����������⡣��Ȼ���������ǶԵģ����������ڵ�����⣬��Ϊ������˶Ա��˿���������Ť������������Լ��Ŀ�����֮�Ƚϡ��������ע���Ը�ϵͳ������������Ť�������أ������ǿ��Ի�ö���Ť�������Ҹ��㷺�Ŀ�����
��ʵ��Ť��֮�γɣ�һ����������Ϊ����֢�������Ը�ϵͳ�У������Լ�����ɵġ���Ҫ���������ˡ���Щ��ҪҲ��ֱ����Ա��ˣ����Ǽ�ӵ�Ӱ���������ǵ�̬�ȡ���֮��Ҫ���ͣ�ʹ��������ת��Ϊ���������Ĺ��ڣ�����֮��Ҫ����İ������츳�������������ħ��������Ҫ�Լ���ֱ��������DZ�Ϊ�����ڷ���������ȱ��ģ�����֮��Ҫʤ�����������ǿ��������Լ�����ͽ������У�����֮��Ҫ�˺����Ƕ���Ϊ���ܳͷ�����ʹ���DZ�Ϊ������֢�ġ�������֮��Ҫ����Լ���ʹ��������ת�����ΰ�ˡ�
������͡��������á����۹������ˣ������������ҵ����뻯����ȴ���������뻯�ˡ���δ���ܵ��Լ��ı��У�ȴ�����˱�Ϊ�DZ���������Ҫ���������������Ժ����ƣ�����Ժ�ռס�����ƣ��ұ�Ϊ���л�������Ļ��������Ὣ���˿��ɿɱ��Ҹ��ܷ��ѵġ�ֻҪʲô��Ū���ˣ��������ǵĹ���������ҲӦ����������ȱ�ģ����Dz�������������Ӧ�ñ��ı��������졣��Ϊ���ǵĵ��в��ѣ�����������Ϊ���Ǹ�����ʥ�����Ρ����������������������ռ�����ƣ�����˽�������������ʱ������������������ʹ����ñ��ӡ�����Ű������ǿ���������������Dz�ϲ���������Dz���Ҫ����������ȡ�������Լ��������ǵ�������
��ЩŤ��������֢���߶Ա���֮���������������У���Ӱ�������ԣ����������á�����λ����Ҫ�����������ڱ��ϵġ���Ϊ�������Լ��ĸ��ܣ����������������������õ��۹����۲쵽�ģ�������ֻ�Դ˷�ʽ�����DZ��Է�Ӧ�������������������Լ�����֮����Ҫ������Ӧ��
��������֮���Խ��ѱ��ϣ���Ҫ����Ϊ���dz�����Щ����Ҫ������������Ҫ���ܵ�����֮�������ֵķ�Ӧ�����ˡ�Ʃ�磬���˵�����˵ı�����Ϊ���������������ǡ���ŭ�Լ����������������£�������һ���ѻ�֧�ֵĸ��ۡ�ֻ�ж��ر�������ӷ��������Dz����ϳ�һ�����Ƿ�������Ҫ�����ܴ��ۣ�����ķ�ŭ�Լ�����ʵ�����������˵�������Ȼ����ᵽ�ף����ı�������������������������ء������Ƿ����Լ������ʱ�����DZ�����Զͬ����ע������ֿ����ԩ����༴���Dz��ɹ���ƫ��ijһ���ͣ�����������һ�ֵĿ����ԡ�ֻ�����������Dz��������ˡ��������á������Ǵ��˹�ϵ����Ӱ��ķ�ʽ��̶ȡ�
Ȼ������ʹ�����˽⣬�Լ���������ദ�Ĺ�ϵ���Ѳ�����һЩĪ���еĿ�������Ҳ����ֹ���������á��ķ�����ֻ�������ܽ���ЩĪ���еĻ�Ť���Ŀ��������ء��������ڼ������ܹ������������ڸ��ܵ����֡��������á������Ĺ���ʱ��Ψ����ˣ����Ƿ����������������á���
���˵������������á���Ť������һ�������ǿɽ�֮Լ�Եع��ɳ����ַ�ʽ��Ť�����ÿ������ڸ������������û�У������һЩ����֮�������¡�����֢���߿ɽ����ǿ�������ȫ������ˣ��Ҿ��������������Ȩ������Ҳ���ܽ�������Ϊ�ǿɱ������ģ����ȿɽ�����ת��ɾ��ˣ�ΰ�ˣ�Ҳ�ɽ�֮��Ϊ���ӡ�
��������Ҳ��ʹ�˺����˱��˼��е��ŵ��ȱ�㡣���Ὣ�Լ����ڰ���������֮���ɣ�ת�Ƶ��������ϣ����������������Щ���������ѵĶ��⡣���ߣ���Ϊ�������Լ��Ļ�����У��������ϱ��˵��������ȳϡ��������Ʊغ����ؾͽ�������Ϊ��α���ӣ���С���������Է������֡��ɼơ�����ƭ�ˡ�
���������������Ҳ����ʹ�����ڲ�����������������е�ijЩƷ�ԡ���ˣ�һ������Ϊ���л���֮���£���ȴ��֪���Լ����������Ӷ�������IJ��ˣ���ܿ���ϳ�����α�Ƶ�̬�ȩ����ر��������밮�����α����һλ���ˣ����о�����̹�б��ѻ��ҡ�������ϰ�ԣ�����ȴ���Ժ������ز�������˵���Щ������Щ���ӣ��ƺ����Ҷ��������õ�Ť����֮��һ���Ż���ì�ܡ�����˵���������ÿ���ʹ�˱���ر��ײ�������ر����ڲ�����˵�ijЩ����һ˵�����ý�Ϊ��ȷ�����Ҳ�����ΪȻ��������ijЩƷ�Ե������ԣ��ѱ���ЩƷ�������������˸�����������ˡ�ʹ����ЩƷ�Ա�ø�Ϊ��������ʹ������ЩƷ�е��˼��������Ǹ����壬�������һ���ر������˵��������������ˣ���Ϊ���������˸�Ŀ������������ƫ���������˸�ػᱻŤ�������ɵģ�������Щ�������ã��������ڱ��ϵģ���Ϊ���˱������Գ��õر����������ʵ��֮�Щ�����Ϊ����һ�й۲죬�Ͼ�����ȷ�ġ�
�����������Щ���ة�������֢����Ҫ�������˵ı����Լ������������é�����ʹ���˺������������������ٺ������������������ⷽ������֢���߱���������֪��������Դ���ȫ��֪�Ļ������������У�������Ϊ������Ҫ��������Ҫ������Ҫ���ǺϷ��ģ���Ϊ�����˵ı���ͬ���������ģ���Ϊ������������ֻ�ǶԱ��˼��е�̬�ȵķ�Ӧ����������֪���Լ�������Щ���Ѵ��ک�������ȷ�еؾ���������ú����ɡ���Ȼ���ǿ�����ģ�������ȴ��һ�ִ�����
���ļ���ֻҪ����������£����ᾡ������ȥ���������������ʵ��ˣ��ͺ��ദ��Ȼ�����ġ��������á�ȴ�Ǵ���Ŭ��������ϰ�����Ϊ�������õ���������˵�ʵ����Ϊ����ϵ�����Բ����Թ������ˡ�Ʃ�磬������ͼ��ö�����ֱ����Э������Υ����ָ����������������Ҫ����Ӧ�����·���͵�ȵȡ�Ȼ�������ǵ�Ŭ��ȴ������������������Ϊ���������Լ������У�����ʼ�������ˡ�
������ЩŤ���������£�����֢������Ӿ��ñ��ˡ����ɿ�������Ȼ��������Ŀ�У���ȷ���������ڹ۲���˵ģ������
![[HP]������������˷���](http://www.aaatxt.com/cover/2/2991.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