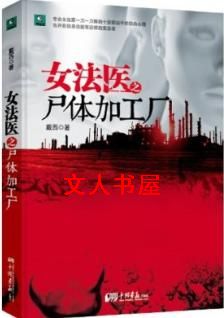首席女法医之人体农场-第3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依据我的推论,”谢德医生说,“因为硬币不纯含有杂质,尸体压在上面后硬币的氧化不均匀,所以有些地方是空白的,形成不规则的印痕。这很像鞋印,鞋印通常也不完整,除非体重分布很均匀,而且人踩在一个极为平坦的表面。”
“将斯坦纳的照片作影像强化处理了吗?”凯兹问。
“联邦调查局的实验室正在处理。”我说。
“嗯,他们的进度可能会很慢,”凯兹说,“他们有那么多资源,可是办案速度却越来越慢,因为案子越来越多。”
“你也知道预算情况。”
“我们的预算少得像一堆白骨。”
“托马斯,这句俏皮话太恐怖了。”
事实上,这次实验的三夹板就是我自费提供的。我原本打算再添购一台冷气机,但气候转凉,无此必要。
“很难让政治人物对我们从事的工作感兴趣。你的情况也一样,凯。”
“问题是死者不会投票。”我说。
“我听说过幽灵选票呢。”
我们沿着内兰大道开车返回,沿路欣赏河景。在一处弯道,我看见了人体农场后方从树梢间冒出来的围墙。我想着冥河,想象那对赞助我们的夫妻横渡河水,在那里了却余生。我由衷地感谢他们,因为死者是我借以拯救生灵的沉默大军。
“真可惜你不能早一点来。”凯兹说,他一向很亲切。
“你错过了昨天一场精彩的球赛。”谢德医生补充道。
“我感觉已经亲眼目睹了。”我说。
19
我没有听从韦斯利的建议,仍旧回到凯悦宾馆的那个房间。我不想为此浪费时间,我有许多电话要打,还要赶乘飞机。
在穿过大厅和上电梯时,我高度警惕。我看着每一个女人,突然想起也得留意男人,因为德内莎?斯坦纳很精明,她这一生都在进行欺骗、诱骗的勾当。我知道恶魔有多聪明。
我匆匆走回房间,没有看到特别值得注意的人。但我仍从手提箱中取出左轮手枪放在身边,然后开始打电话。我首先打电话到绿顶公司,接电话的是乔恩,他人很好,曾替我服务过几次。我开门见山,毫不迟疑地问了若干有关露西的问题。
“真是遗憾,”他说,“我看到报纸时真不相信会有这种事。”
“她的运气很好,”我说,“守护天使那天晚上陪着她。”
“她是个很特别的女子。你一定以她为荣。”
我这才想起我对此已经不确定了,这个念头令我更加难受。“乔恩,我想知道几个很重要的细节。她那天晚上去买枪时,是你值班吗?”
“当然,就是我卖给她的。”
“她还买了什么?”
“一本杂志,几箱练靶弹。嗯,我想应该是联邦海卓修克牌,对,这点我很有把握。对了,我还卖给她一个麦克叔叔牌枪套,一个去年春天我卖给你的那种足踝式枪套,是最高级的拜安奇牌。”
“她怎么付钱的?”
“现金,老实说这令我有点吃惊。那不是一笔小钱,你也可以想象。”
露西一向节约,在她二十一岁时我送了她一大笔钱。她有信用卡,我想她没有刷卡是因为不想留下购买记录,对此我倒不觉奇怪。她当时很惶恐,疑神疑鬼,经常与执法人士相处的人大都如此。对我们这类人而言,每个人都是嫌疑人。我们常会反应过度,稍有风吹草动便会掩饰行踪。
“露西是预约的,还是直接上门?”
“她打电话预约了时间。事实上,她又打了一次电话来确认。”
“两次电话都是你接的吗?”
“不,只有第一次。第二次是里克接的。”
“你能告诉我她打第一个电话到底说了些什么吗?”
“说得不多。她说已和马里诺队长谈过了,他建议她买西格索尔P230,他还建议她找我接洽。你知道,队长常和我一起去钓鱼。她问我周三晚上八点左右是否值班。”
“你记得她是哪一天打电话的吗?”
“呃,就在她来之前的一两天,我想是上周一吧。对了,我还问过她是否已满二十一岁。”
“她告诉你她是我外甥女了吗?”
“说了。看到她时我也想起了你,连声音都很像,你们都有那种深沉、平稳的声音。但她在电话中真的让人印象深刻,极有思想,也很有礼貌。她似乎对枪支很熟悉,显然也经常打靶。哦,她告诉我队长还教过她射击呢。”
听到露西声明是我外甥女,我不禁松了一口气,那说明她并没想瞒着我偷偷买枪。我想马里诺日后也会告诉我的,遗憾的是她没有先和我谈。
“乔恩,”我继续说,“你刚才说她又打了一个电话,能具体谈谈吗?什么时候打的?”
“也是上周一。两个电话大概相隔一两个小时。”
“她是和里克谈的?”
“只说了几句。当时我在招呼一个顾客,电话是里克接的。他说是斯卡佩塔,她想确认我们约好的时间。我说是周三晚上八点,他就这么转告她了。就这样。”
“对不起,”我说,“她说什么?”
乔恩迟疑了一下。“我不确定你在问什么?”
“露西打第二个电话时自称斯卡佩塔?”
“里克是这么告诉我的。他说是斯卡佩塔打来的。”
“她不姓斯卡佩塔。”
“天哪,”他一脸错愕,“你在开玩笑吧。我以为那是理所当然的事……那就奇怪了。”
我猜露西呼叫马里诺后,马里诺很可能是在斯坦纳家回电话给她的。德内莎?斯坦纳一定以为马里诺在和我说话,等他一离开房间,她就从查号台很轻易地得到了绿顶公司的电话号码,接下来她只需打过去问她想问的问题。我松了一口气,随即怒不可遏。德内莎?斯坦纳并不想杀害露西,嘉莉?格雷滕或其他人也没有这种意图,受害的目标原本是我。
我又问了乔恩最后一个疑问。“我不想找你作证,但你招呼露西时,她有醉酒的迹象吗?”
“如果她喝醉了,我不可能卖东西给她。”
“她的神情如何?”
“她很匆忙,但不时开开玩笑,也很亲切。”
如果露西真如我所怀疑般已酗酒几个月或者更久,她很可能在酒精浓度为零点一二时神志仍很清醒,但判断力与反应能力都会受到影响,对开车时发生的紧急情况可能无法做出快速反应。我挂上电话,又拨了《阿什维尔市民时报》的号码,地方版的采编主任告诉我撰写那则意外事故新闻的是琳达?梅菲尔。我运气不错,她在办公室,电话不久就接通了。
“我是凯?斯卡佩塔。”我说。
“哦?我能效劳吗?”她的声音听起来很年轻。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有关我的车子在弗吉尼亚出车祸的报道。你在报道中说当时是我开车,后因酒后驾车被捕,你知道这与事实不符吗?”我的语气平和而坚定。
“哦,是的,女士,我很抱歉,请让我向你说明当时的情况。车祸发生当晚,有人深夜打电话说那辆车,奔驰车,已证实是你的,并说驾驶员可能是你,而且是酒后开车。我当时正忙着赶另一篇稿子,编辑正催我交稿付印,他告诉我如果能证实那个驾驶员是你就发稿。那时已是截稿期限了,我想没有机会证实了。
这时有一个电话出人意料地转接到我手中。那位女士说她是你的朋友,从弗吉尼亚医院打来的电话。她想让我们知道你在那场意外中并没有受伤,她还认为我们应该知道这一点,因为斯卡佩塔医生,就是你,有一些同事仍在侦办斯坦纳家的案件。她说她不希望我们听到这场车祸的其他说法,要求撤销会令你的同事惊慌的报道。”
“你就这么听信了一个陌生人的话,照她所说的报道了?”
“她向我提供了姓名和电话号码,经查证也属实。何况如果她与你不熟,怎么会知道那场意外和你来此地侦办斯坦纳家的案子?”
那位女士可以知道这一切,如果她是德内莎?斯坦纳,如果她在试图杀害我之后在弗吉尼亚的电话亭打电话。
我问:“你怎么查证的?”
“我立刻回拨电话,是她接的。那是弗吉尼亚州的区号。”
“电话号码还在吗?”
“噢,我想还在吧。应该在我的笔记本上。”
“能否马上找一下?”
我听到翻动纸张等窸窸窣窣的声音。过了好一阵,她才将号码告诉我。
“非常感谢。我希望你已经更正报道了。”我说。我感觉得出来她吓坏了。我为她难过,也相信她不是有意害人。她只是年轻而经验不足,当然不是想与我斗智的变态杀人狂的对手。
“我们第二天就刊登更正启事了。我可以寄一份给你。”
“不用了。”我想起了开棺验尸时忽然涌出的那群记者。我知道是谁向他们透露了消息——斯坦纳太太,她忍不住想引来更多关注。
我拨了那个号码,许久才有一个男人接听。
“打扰了。”我说。
“喂?”
“你好,我想知道这个电话在什么地方。”
“哪个电话?你的还是我的?”那人笑道,“如果你不知道你的电话在哪里,那你就有麻烦了。”
“你的。”
“我在一家西夫韦门外的公用电话亭,正打算打电话给老婆,问她想吃什么口味的冰激凌,她忘了告诉我。刚好这部电话响起,我就接了。”
“哪一家西夫韦?”我问,“哪里的分店?”
“卡瑞街。”
“在里士满?”我惊慌地问。
“对。你在哪里?”
我谢过他后挂上电话,在房内踱步。她曾经到过里士满,为什么?看看我住在什么地方?她曾经开车经过我的住处?
我望着窗外。晴朗的蓝天与鲜亮的树叶在这个明亮的午后,似乎都在说不可能发生如此龌龊的事,世上没有邪恶的黑暗势力,我查出来的都不是真的。但我在风和日丽时,在瑞雪缤纷时,在城内洋溢着圣诞节的灯火与音乐时,总是对此存疑。每天早晨我进入停尸间时总会遇上新的案子,有人被强暴、枪杀,或在意外中丧命。
在办妥退房手续之前,我试着拨打联邦调查局实验室的电话,惊奇地发现原本打算留言给他的那位科学家居然还在。同我们这些除了工作便无所事事的人一样,他的周末也是别人的。
“我已经尽力了。”他是说已经处理了许多天的影像强化。
“没有结果?”我失望地问。
“我已设法使影像清晰了一些,但还是辨认不出来。”
“你还会在实验室待多久?”
“一两个小时。”
“你住哪里?”
“亚奎港。”
我不喜欢这样每天通勤,但华盛顿住在亚奎港、斯坦福德和蒙特克莱有家眷的探员出奇的多。亚奎港距离韦斯利家大约一个半小时车程。
“我实在不愿提出这种要求,”我继续说,“但我必须尽快取得这份影像强化的打印件,它很重要。你能不能送一份到本顿?韦斯利的住处?不过必须绕路,多出了一个小时的路程。”
他犹豫了一会儿才说:“如果现在出发应该可以。我会打电话给他问清路线。”
我拎起行李袋,直到进入诺斯维尔机场的女厕所才将左轮手枪放回手提箱。通过例行安检后,他们照例为我的行李袋系上了橘黄色荧光标签,这使我想起了那卷胶带。德内莎?斯坦纳怎么会有鲜橘色的胶带,她是从哪里得到的?我看不出她和阿蒂卡监狱有什么关联,在我穿过飞机跑道搭乘那架小型螺旋桨飞机时更加认定此案与监狱无关。
我坐在靠近走道的座位上,陷入沉思,没有注意到其他大约二十名旅客的紧张表情,直到我忽然发现机上有警察。其中一位正和地勤人员交谈,眼光偷偷扫视着每一位乘客。我在进行侦查时也会这样,我太熟悉这种神情了。职业惯性使我开始思考他们在寻找什么不法之徒、他可能做了什么事。我想着如果他突然从座位上跃身而起我要如何反应。我要绊倒他,要在他经过时从后面抱住他。
一共有三名喘着气冒着汗的警察,其中一个在我身旁停下来,紧盯着我的安全带。他的手灵巧地放在半自动手枪上,松开枪套扣。我不动声色。
“女士,”他用警察办公时的口吻说,“你得跟我来。”
我愣住了。
“座位底下的袋子是你的吗?”
“是的。”我紧张不已。其他乘客都不敢动弹。
警察迅速弯腰拿起我的皮包与行李袋,在整个过程中视线从未了离开我。我站起来,他们让我下飞机。我只有一个念头:有人将毒品塞入我的袋子里,是德内莎?斯坦纳栽赃的。我疯狂地环顾跑道和机场的玻璃窗,想找正在暗中窥视我的人,一个女人,她现在已隐身于阴影之中,看着我百口莫辩。
一个穿着红色跳伞衣的地勤人员指着我。“就是她!”他激动地说,“在她腰带上!”
我恍然大悟。
“只是一个电话。”我缓缓移开手肘,一边让他们看清我外套里面的东西。在穿宽松的衣服时,我通常将移动电话挂在腰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