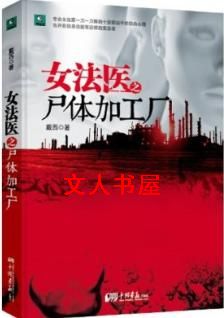首席女法医之人体农场-第1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见过面。”
“我们要到他办公室展开一场快速又令人讨厌的讨论,”他说,“之后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哪里?”
“一个很难前往的地方。”
“本顿,你再这么神秘,我可别无选择,只能说拉丁语来报复了。”
“你知道我最痛恨你说拉丁语。”
我们将来宾通行证插入一个旋转门内,沿着一道长廊走向电梯。每次来联邦调查局总部,都会令我更不喜欢这里。很少有人正视你或微笑,每件事或每个人似乎都隐藏在各种白色或灰色的百叶窗后。实验室间的走道错综复杂宛如迷宫,如果我独自行走,一定会迷路。更糟的是,在这里工作的人似乎也不认路。
杰克?卡特赖特办公室的景观不错,阳光照在窗户上,使我想起了当年埋首工作,兢兢业业的美好时光。
“本顿,凯,你们好。”卡特赖特与我们握手,“请坐。这位是乔治?基尔比,这位是希斯?理查兹,实验室的工作人员,你们见过吗?”
“没有,你们好!”我和那两人打招呼。他们都很年轻,神情严肃,衣着朴素。
“有人喝咖啡吗?”
没有人喝,卡特赖特似乎也急着谈正事。他看起来很迷人,而他那令人肃然起敬的办公室似乎也在向人证明他的办事方式。每份文件,每个公文袋和电话留言都井然有序地放在固定位置,一个笔记本上摆着一支老旧的银色派克钢笔——只有极度守旧的人仍在使用。窗边摆有盆景,窗台上还摆着他妻女的照片。外面阳光普照,车水马龙,小贩在叫卖T恤衫、冰激凌和牛奶。
“我们一直在侦办斯坦纳的案子。”卡特赖特开始了讨论,“目前为止有很多相当有意思的发现,我先从或许是最重要的开始,即在冰箱内找到的皮肤。虽然DNA分析尚未完成,但我们仍然可以确定那是人类的生理组织,血型呈O型阳性。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受害人埃米莉?斯坦纳也是O型阳性血。那块生理组织的大小,形状也与她的伤口相符。”
“能确定那块生理组织是用什么器具切割下来的吗?”我问道,同时记着笔记。
“一种单刃,锐利的切割工具。”
“这几乎囊括了所有刀具。”韦斯利说。
卡特赖特继续说,“根据凶手切割时划在肌肉上的第一个点判断,是一种有尖端的单刃刀。目前只能将范围缩小到这里。还有——”他望向韦斯利,“在你送来的刀具上找不出任何人类的血迹。呃,就是从弗格森家送来的那些。”
韦斯利点点头,面无表情。
“下面谈微物证据,”卡特赖特接着说,“这就开始变得有趣了。我们在显微镜下找到了被害人尸体和毛发上某些不寻常的物质,鞋底也有,经查为若干与她床铺上的毛绒相符的蓝色亚克力纤维,以及与她穿去教堂的那件绿色灯芯绒外套相符的绿色棉纤维。还有若干羊毛纤维,出处不明。我们也找到了若干尘土,来源广泛,无法确定,但也不是到处都能找到。”
卡特赖特从他的旋转椅上转身,打开身后柜子上的放映机。画面上出现了四个不同角度的切片,是一种略像细胞的物质,让人想起蜂巢,但有些地方沾上了琥珀色。
“各位所看到的,”卡特赖特告诉我们,“是一种称为接骨木属黄耆的植物组织切片,它是生长在佛罗里达州南部海岸平原和礁湖间的一种灌木。最有意思的是这里的黑点部分。”他指着污点处,“乔治,”他望向其中一个年轻的实验员,“这是你的专长了。”
“这些是丹宁囊。”乔治?基尔比靠近我们,加入讨论,“在这个辐射状切片上看得更清楚。”
“丹宁囊到底是什么?”韦斯利追问。
“是植物茎部用来传送物质的运输管道。”
“什么物质?”
“通常是细胞活动产生的废物。各位也知道,这是植物的髓,就是植物的丹宁囊所在处。”
“你是说这个案件的微物证据是髓?”我问。
乔治?基尔比点点头,“没错。商业上称之为髓木,虽然就专业术语而言它并不存在。”
“髓木有什么用途?”韦斯利问。
这时卡特赖特回答,“通常用固定精细的机器零件或珠宝首饰。珠宝匠和钟表商或许会将小耳环或手表的齿轮插在髓木上,以免这些东西在桌上滚动或被甩落,但现在大家都改用泡沫塑料了。”
“她身上留有很多髓木吗?”我问。
“相当多,大都在流血的部位,其他微物证据也主要是在这些部位采集到的。”
“如果有人要用髓木,”韦斯利说,“要去哪里找?”
“佛罗里达州南部的大沼泽,如果你想自己砍树,”基尔比回答,“否则就得订购。”
“到哪儿订购?”
“我知道在马里兰州的银泉市有一家开展此业务的公司。”
韦斯利望着我,“看来,我们得查查黑山地区有谁在修理珠宝首饰了。”
我告诉他,“如果黑山地区有珠宝匠,我会大感意外。”
卡特赖特再度开口:“除了刚才提到的证物,我们在显微镜下也发现了若干昆虫,甲虫、蟋蟀、蟑螂,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还有一些白色与黑色的漆斑,但都不是汽车上的,另外,头发中还有木屑。”
“来自什么木材?”我问。
“大都是胡桃木,但也检验出桃花心木。”卡特赖特望着韦斯利,而韦斯利正望着窗外,“你在冰箱内找到的皮肤组织上没有这些物质,但她的伤口上有。”
【文、】“这是否表明在皮肤被割下来之后,尸体才运到藏尸地点,沾到这些物质?”韦斯利说。
【人、】“可以这么认为,”我说,“但割下皮肤加以保存的人也有可能进行了清洗——割下时一定血淋淋的。”
【书、】“会不会是放在了某种交通工具里面?”韦斯利继续问,“例如车后面的行李箱?”
【屋、】“有可能。”基尔比说。
我知道韦斯利在朝哪个方向思考。高特曾经在一辆破烂不堪的老旧箱型车内谋害十三岁的艾迪?希斯,车上有各种令人费解的证物。简单地说,高特,一个佐治亚州经营胡桃园的富商之子,一个变态杀人狂,以留下一些令人摸不着头绪的证物为乐事。
“至于鲜橘色的绝缘胶带,”卡特赖特终于谈到了这一点,“是不是还有没有找到整卷胶带?”
“是的,还没有。”韦斯利回答。
希斯?理查兹实验员正翻阅笔记本,卡特赖特告诉他,“我们开始谈这一项吧,我个人认为这会是我们找到的最重要的证物。”
理查兹开始侃侃而谈,就像其他刑事鉴定人员一样,他热爱自己的专长。联邦调查局的数据库里有一百多种绝缘胶带,以备刑案设计胶带时鉴别。事实上,这种司空见惯的日用品被用来作案,这令我在五金行或杂货店看到它们时也会产生恐怖的回忆。
我曾用绝缘胶带将被炸得支离破碎的残骸拼凑在一起,也曾将性虐待狂凶手捆绑被害人的胶带拆除,还曾从绑着砖块沉尸河底或湖底的被害人身上撕下胶带。我已经数不清那些送进停尸间同时嘴巴仍蒙着胶带的受害人有多少了。只有进了停尸间,这些尸体才能开口,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才会有人关心他们所遭受的一切。
“我从没有见过这种胶带。”理查兹说,“它的捻线数目之高让我确信,无论如何,这卷胶带不是在商店里买的。”
“你怎么确定?”韦斯利问。
“这是专业的规格,拥有六十二条经线与五十六条纬线,而在大卖场购买的那种二十比十的经济型规格,一卷才一两美元。专业型的或许要十美元一卷。”
“你知道这种胶带是在哪里生产的吗?”我问。
“北卡罗来纳州希克利市的休福工厂,全国数一数二的大型胶带制造厂。他们最出名的品牌是‘粘得牢胶带’。”
“希克利位于黑山东边大约六十英里处。”我说。
“你找过休福工厂的人吗?”韦斯利问理查兹。
“找过,他们仍在替我追查胶带流向。母亲已经找到一些线索。这种鲜橘色胶带是该公司在八十年代专为一家客户制造的私人标签用品。”
“什么是专为客户制造私人专业标签用品?”我问。
“有人需要一种特殊的胶带,于是下订单给工厂。一张单子至少得订五百箱,所以还有数百卷胶带我们可能永远看不到,除非它像这一卷一样出现。”
“能否举个例子?什么人会自己设计并定制胶带?”我进一步追问。
“我知道有些赛车选手就会订购,”理查兹回答,“例如理查德?佩蒂订购的就是红色与蓝色的,而达雷尔?沃奇普用的则是黄色。休福公司几年前也曾遇到这样一个客户——因为工人老是在下班时顺手牵羊拿走昂贵的胶带,所以订购了独一无二的亮紫色胶带。如果有人用亮紫色胶带修补家里的管线或孩子的充气游泳池,一眼就可以看出是偷来的了。”
“这一回成为这种鲜橘色胶带的订购目的吗?防止工人偷走?”我问。
“有可能,”理查兹说,“另外,它还防火。”
“那很不同寻常吗?”韦斯利问。
“是的。”理查兹回答,“依我看,防火的胶带只用在飞机和潜水艇上,但并不特别要求得是鲜橘色,至少我这么认为。”
“为什么有人需要鲜橘色的胶带?”
“这是值百万奖金的智益问答题,”卡特赖特说,“橘色,总令我联想到打猎和锥形的交通路标。”
“我们再回过头来讨论一下凶手用来捆绑斯坦纳太太和她女儿的那些胶带吧。”韦斯利建议,“还有什么可以提供的信息吗?”
“胶带上黏附着若干像是家具上的亮光漆的东西,”理查兹说,“另外,胶带从整卷撕下来的次序与绑在那位母亲手腕和脚踝上的次序不符。这意味着那个歹徒撕下一段段的胶带后,可能将它们黏在家具的边缘。捆绑前,已经准备妥供他使用的胶带,一次用一段。”
“但是他将次序弄乱了。”韦斯利说。
“是的。”理查兹说,“我将这些用力绑母亲和女儿的胶带都加了编号,你们想看一下吗?”
大家都表示要看。
我和韦斯利当天下午一直待在材料分析组,置身于一大堆气相层分析仪、质谱仪、差示扫描热量器,以及用力判别是何种材料及其熔点的其他复杂万分的仪器之间。我站在一部便携式爆裂物探测器旁,理查兹则继续分析用力捆绑那对母女的特制胶带。
他向我们解释,在用热蒸汽将黑山警局送来的胶带分开后,发现共有十七段,长度从八英寸至十九英寸不等。他将这些胶带置于透明的厚树脂塑料片上,分两次进行编号——胶带撕下来的次序和歹徒用来绑受害人的次序。
“绑在母亲身上的胶带编号完全乱了,”他说,“应该首先使用的是这一段,却是最后才用的。撕下来的这第二段,使用时应该也排在第二,而不是第五。而那位小女孩身上的胶带,则完全依照撕扯次序使用,总共用了七段。绑在她手腕上的胶带编号就是从胶带卷上撕下来的编号。”
“她应该比较好控制。”韦斯利说。
“这很容易想到。”我说,接着问理查兹,“你从小女孩身上取下的那些胶带上找到家具漆的残留物了吗?”
“没有。”他回答。
“这真有意思。”我说,这些袭击令我困惑不已。
胶带上的乌黑条纹,是我们最后才讨论的。经过分析证实,那是碳氢化合物,用浅显一点的名词来称呼就是油脂。这对我们没有什么帮助,因为油脂就是油脂。胶带上的油脂可能来自汽车,来自亚利桑那州的一辆马克牌货车。
12
四点半,我和韦斯利来到红色鼠尾草餐厅。这个时间喝酒太早了些,只是我们都觉得不太舒服。
再度独处,我很难直视他的双眼。我盼着他谈起那天晚上我们之间发生的事。我不希望只有我在乎。
“这里有带活塞的小桶啤酒,”韦斯利在我看菜单时说,“味道很棒,如果你喜欢喝啤酒的话。”
“除非大热天我奔波了两小时,口渴难耐,又大嚼披萨,否则我不喝啤酒。”他竟是如此不了解我,我有点不悦。“事实上,我不喜欢啤酒,只有找不到其他替代饮料时才会喝,但从不认为它味道很好。”
“这可不值得你动肝火。”
“我没有。”
“你听起来火气很大,而且都不正眼看我。”
“我很好。”
“我考观察人为生。让我告诉你,你一点都不好。”
“你是靠观察精神病人为生,”我说,“你要观察的对象不是一个为儿童谋杀案忙了一整天,现在只想放松一下的奉公守法的首席女法医。”
“要上这家餐厅不是那么容易。”
“我知道。谢谢你大费周章。”
“我不得不动用关系。”
“想必如此。”
“吃晚饭时喝点酒号码?没有料到这里竟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