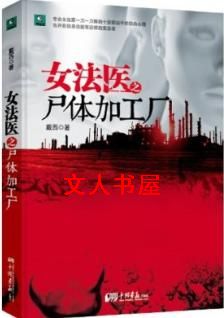首席女法医之人体农场-第1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环顾着阴冷的州政府自助餐厅,用餐的客人都很沉闷。许多人将皮夹克与毛衣都扣到下巴处,埋头猛吃。
“他们将所有的自动调温器设定为十六摄氏度,以节约能源,那真是天大的笑话。”格格里亚继续说道,“弗吉尼亚医学院还在使用蒸汽暖气,所以降低调温器的温度根本无法节省任何电力。”
“我觉得这里还不到十六度。”我说。
“现在是十二度,与室外温度相同。”
“欢迎你到街对面去使用我的办公室。”我打趣地笑着说。
“哦,那可是全城最温暖的地方了。我能帮你什么忙,凯?”
“我想追查一件疑似婴儿猝死症的案子,大约十二年前发生在加州。那名婴儿的名字叫梅莉?乔?斯坦纳,父母的名字分别是查尔斯与德内莎。”
她立即记了下来,但她很专业,没有问我缘由。“你知道德内莎?斯坦纳的娘家姓吗?”
“不知道。”
“加州什么地方?”
“我也不知道。”我说。
“你能查出来吗?你能提供的消息越多越好。”
“还是请你先用这些信息查查看吧。如果查不出来,我再想想还能找到什么资料。”
“你说疑似婴儿猝死症,是指有可能不是婴儿猝死症吗?我必须知道,以防登记成别的死因。”
“依据推测,那个孩子夭折时一岁大,这令我很困惑。你也知道,婴儿猝死症的发病高峰期是在婴儿三到四个月时,超过六个月的婴儿就不太可能患这种病了。过了一岁,应该就是其他原因导致猝死。所以,很有可能登记成别的死因了。”
她把玩着桌上的茶包,“如果事情发生在爱达荷州,我只要打电话给简,她立马就会依照婴儿猝死症的分类去查询,在九十秒内给我答复。但加州有三千两百万人口,是最难查询的州之一,或许要用特殊方式查询。来吧,我送送你,这算是我今天的运动了。”
“那位户籍登录人员还在加州首府吗?”我们沿着一条死气沉沉的走廊前行,走廊里挤满了行色匆匆,需要社会服务的市民。
“是的,我一上楼就打电话给他。”
“那么我想你认识他了。”
“哦,当然。”她笑了,“这一行总共也不过五十个人,我们找不到别人聊天。”
当天晚上我带露西去高级法国餐厅,享受名厨的手艺。我们点了水果腌小羊肉,要了一瓶一九八六年的名酒,以舒缓我们疲惫的神经。我答应回去后再请她吃一客加了阿月浑子与马尔萨拉白葡萄酒的甜美巧克力慕斯,那是我珍藏在冰箱里,以备不时只需的。
回家之前,我们驱车至市区的休克巴登,在街灯下的鹅卵石步行道上散步。不久前我还不敢靠近此地。河边,天色暗蓝,繁星点点,我想起了本顿,又因截然不同的原因想起了马里诺。
“姨妈。”我们在咖啡厅喝可布其诺时,露西说,“我能不能找个律师?”
“为什么?”我明知故问。
“即使联邦调查局无法证明他们加诸我的罪状,还是会从此将我拒之门外。”她口气平缓,但掩不住痛苦。
“告诉我你需要什么。”
“一个大人物。”
“我帮你找一个。”我说。
我没有依照原定计划于星期一返回北卡罗来纳州,反倒飞往华盛顿。我在联邦调查局还有些事待办,但它们都不及探视一位老朋友重要。
法兰克?罗德参议员当年与我在迈阿密就读同一所天主教高中,但不是同一级的,他比我年长许多。当我在戴德县法医办公室任职,而他担任佐治亚州检察官时,我们才结为朋友。他成为州长、参议员时,我已经离开南部的出生地;他受命担任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后,我们才再度联系。
罗德在推进美国有史以来最艰巨的犯罪法案时,曾要求我担任顾问,我也曾请他帮忙。他算是露西的贵人,这一点露西一直不知道。若没有他干预,她或许就无法获准入学。也无法实现今年秋季的留校实习。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向他启齿,谈起此事。
晌午时分,我在参议院大厅内一张光洁的棉椅上等他。艳红色墙壁,波斯地毯,水晶吊灯,使得大厅富丽堂皇。隔着大理石走道,能听见外面的各种声响,偶尔也有观光客探进头来,希望能在参议院餐厅内看到某个大人物。罗德准时赴会,给我一个快速而有力的拥抱。他精力充沛,亲切平和,但不善于表达感情。
“你脸上有我的口红印了。”我将他下巴处的唇印擦掉。
“哦,你应该留着,让我的同事有个茶余饭后的话题。”
“我看他们的话题已经够多了。”
“凯,见到你真好。”他说着陪我进入餐厅。
“你或许会发现没有那么好。”我说。
“真的很好。”
我们挑了一张靠窗的洁净桌子,窗外是骑着马的乔治?华盛顿雕像。我没有看菜单,因为这里从不改变菜色。罗德参议员仪表堂堂,一头浓密的灰发,深邃的蓝眼眸。他身材高瘦,偏好优雅的丝质领带和老式的华丽服饰,例如坎肩、袖扣、怀表、领带别针等。
“你怎么会到华盛顿来?”他问,同时将餐巾铺在腿上。
“我手上有些证物,必须就此与联邦调查局的实验室讨论。”我说。
他点点头,“你在侦办那件骇人听闻的北卡罗来纳州案件?”
“是的。”
“非得阻止那种杀人狂不可,你认为他在当地吗?”
“我不知道。”
“我只是在想他为什么会在那儿,”罗德继续说,“照理说他应该到其他地方避避风头才对,也罢,我看这些歹徒在做决定时很少依常理出牌。”
“法兰克,”我说,“露西惹上大麻烦了。”
“我感觉到有事,”他淡然地说,“从你的神情可以看得出来。”
我花了半个小时向他讲明原委,从心底感谢他的耐心。我知道他当天有几项法案要投票,也有很多人想瓜分他的时间。
“你是个好人,”我诚挚地说,“我却让你失望。我恳求你帮忙——我几乎不曾恳求过别人,今天却如此狼狈。”
“是她做的吗?”他几乎没有碰盘中的烤蔬菜。
“我不知道,”我回答,“证据对她不利。”我清清喉咙,“她说不是她做的。”
“她一向对你实话实说吗?”
“我想是吧。但我最近发现她有些重要事情没有告诉我。”
“你问过她了吗?”
“她表明立场说有些事情和我无关,还说我不该批判她。”
“凯,如果你担心自己带着批判的眼光,或许你已经在批判她了。而且无论你说什么或不说什么,露西都可以感受到这一点。”
“我一直不喜欢批判、纠正她,”我懊恼地说,“可是她的母亲——多萝茜,我唯一的妹妹,太过依赖男人,又太过自我中心,无法处理女儿的现实生活。”
“如今露西惹出麻烦来,你又在暗察自己的过失了。”
“我倒没有察觉到这一点。”
“我们很少能察觉到潜伏在理性之下的原始焦虑。要将它消除,唯一的办法就是将一切摊开来谈。你认为自己足够坚强,可以承受吗?”
“是的。”
“让我提醒你,一旦你开口问,就得承受那些答案。”
“我知道。”
“目前只能希望露西是无辜的。”罗德参议员说。
“然后呢?”我问。
“如果露西没有违反安全规定,显然就是另有其人。我的问题是: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的问题是‘怎么做的’。”我说。
他向服务员招手示意上咖啡,“我们首先必须确认的是动机。露西会有什么动机?别人会有什么动机?”
为了钱是很简单的答案,但我认为那不是真正的动机,我这么告诉他了。
“金钱就是权力,凯,一切都是为了权力。我们这些堕落的生灵永远不会满足。”
“是啊,禁果。”
“当然,那是万恶之源。”他说。
“这个悲惨的事实每天都在血淋淋地上演。”我附和道。
“那对你目前面临的问题有何启示?”他往咖啡里加糖。
“让我知道了动机。”
“当然了,权力,就是如此。请告诉我,你要我怎么做?”我的老朋友问。
“除非能证明露西从工程研究处窃取了档案,否则他们无法对她进行任何起诉。但我们在此交谈时,她的前途已经毁了——至少就执法部门,或是任何需要背景调查的职位而言。”
“他们已经证明她就是当天的闯入者吗?”
“他们拥有所需要的证据,法兰克,问题就在这里。我不确定他们会花很大心血去还她清白,如果她是无辜的。”
“如果?”
“我不想有先入为主的偏见。”我端起咖啡,又放下,因为不想再让身体受更多的刺激,我的心跳加速,双手也不由自主地颤抖。
“我可以和局长谈一谈。”罗德说。
“我只希望有人在幕后确保这件事能彻底调查清楚。开除露西,他们不会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反正还有那么多事情等着办呢,而她又只是一个大学生。老天,他们怎么会在乎?”
“我倒希望联邦调查局能多关心这件事。”他说完,紧抿着双唇。
“我很清楚官僚体制,我这辈子都在这种体制中工作。”
“我也是。”
“那你一定很清楚我在说什么。”
“没错。”
“他们要她到里士满和我同住,直到下学期开学。”我说。
“这么说,那就是他们的裁决了。”他再度端起咖啡。
“正是如此,那对他们而言只是举手之劳,但露西怎么办?她才二十一岁,可她的梦想就此破灭。她该何去何从?过完圣诞节之后回弗吉尼亚大学,假装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听着,”他亲切地抚着我的手臂,这种亲切感总会令我希望他是我父亲,“我会在避免干预行政作业的原则下尽力而为,你能信得过我吗?”
“当然。”
“同时,不知你是否介意我向你提供一点个人忠告?”他瞥了一眼手表,向服务员招手。“我迟到了。”他转头望着我,“你最大的问题是家事。”
“难以苟同。”我坦诚地说。
“是否同意,悉听尊便。”他笑着接过服务员递来的账单,“你和露西情同母女,可你想如何帮她渡过这个难关?”
“我认为我今天已经在做了。”
“而我认为你今天这么做是因为你想和我见面。对不起。”他向服务员示意,“我看这不是我们的账单,我们没有叫四道小菜。”
“我看看。糟糕,哦,真抱歉,罗德参议员。那是另一桌的。”
“既然如此,就叫肯尼迪参议员一并付了吧——他的和我的。”他将两张账单都递给服务员,“他不会反对的,他信奉纳税与花费。”
服务员是个肥胖的女人,身穿黑色套装与白围裙,头发齐肩向内翻卷。她笑着,对自己所犯的错误总算松了一口气,“遵命,先生!我会这么告诉参议员的。”
“告诉他,再多付一笔慷慨的小费,米苏里。”他在她正要离去时说,“告诉他是我说的。”
米苏里已年逾七十,几十年前搭乘北上列车离开南部老家来到这里。这些年来,她目睹了参议员的盛衰荣枯、起落浮沉、情场得意或政坛失意。她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打岔上菜,什么时候该添茶或告退。她知道这个美好的餐厅内那些掩饰得当的秘密的真面目,因为要对一个人做出最准确的评断,就是在没人观察时看他如何对待像她这样的人。她喜爱罗德参议员,这从她望着他柔和的眼神以及听到他名字时的神情看得出来。
“我只想督促你多花点时间陪露西。”他继续说道,“别急着替别人解决难题,尤其是她的。”
“我不相信她可以自行解决。”
“我想,你不用告诉露西我们今天的交谈,也不用告诉她我一回办公室就会替她打电话,如果你觉得需要有人告诉她,就由我来开口。”
“好的。”我说。
不久之后,我在罗素大楼外拦了一辆出租车,前往联邦调查局总部外的半圆形广场。我和韦斯利约好两点十五分在此地碰面。他正坐在一条长椅上,津津有味地读一本小说,但我知道在我开口打招呼之前,他早已注意到我了。当一个参观团与我们擦肩而过时,韦斯利将书合上,放进外衣口袋,站了起来。
“旅途顺利吗?”他问道。
“加上前往机场和离开机场到达市区的时候,乘飞机与开车相差无几。”
“你说乘飞机来的?”他替我拉开大厅的门。
“我让露西用我的车。”
他摘下墨镜,替我们俩各取了一张来宾通行证,“你认识刑案实验室的主任杰克?卡特赖特吗?”
“见过面。”
“我们要到他办公室展开一场快速又令人讨厌的讨论,”他说,“之后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哪里?”
“一个很难前往的地方。”
“本顿,你再这么神秘,我可别无选择,只能说拉丁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