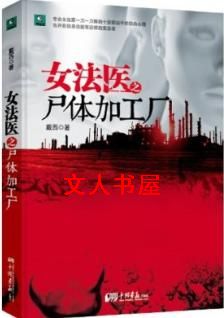首席女法医之人体农场-第1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你可以帮忙查看一下柜子,看看我是否将东西都拿出来了。”露西说,“右边那一个。抽屉也检查一下。”
“全都空了,只剩下你的外套衣架,那些有软垫的高级衣架。”
“那是我母亲的。”
“那我猜你应该像保留它们。”
“不要,留给下一个搬进这鬼地方的白痴。”
“露西,”我说,“这不是联邦调查局的错。”
“不公平。”她跪在行李箱上固定扣环,“在证明有罪前应该如何对待无辜者?”
“就法律而言,在证明有罪之前你是无辜的。但在查明真相之前,你不能怪他们不让你继续在机密区域工作。何况,你又没有遭到逮捕,只是奉命离开一阵。”
她转过身来面对着我,眼睛又干又红,“一阵意味着永远。”
上车后我细细追问时,她不是涕泗纵横就是怒气冲冲。直到她睡着了,我仍没问出个所以然来。又是一阵冷雨,我打开雾灯,跟着在前方柏油路面上摇曳的红色尾灯前进。大雨与密云使人几乎无法看清路况,但我没有停靠路边等候天气好转,只是换到低档,在这辆有胡桃木、软皮、钢铁的车内继续颠簸。
我仍不确定自己为什么会购买这辆深黑色奔驰E500,只知道马克去世后,开辆新车似乎非常重要。或许是为了挥别记忆,因为前一辆车里有爱也有争吵。也可能只是因为日子越来越难过,而我也越来越老,需要掌控更多权力。
我驾车驶入温莎农场时,听到露西变换姿势的声音。我就住在这个里士满的老旧小区,我的房子位于距离詹姆斯河不远的佐治亚式与都铎式庄严建筑之间。车前灯闪过前方一个陌生男孩自行车踏板上的小反光板,接着是一对我不认识的夫妇,他们牵着手悠闲地遛狗。我院子里的橡胶树又掉落了一大堆多刺的种子,阳台上放有几份报纸。我不需要离家太久就会觉得自己像个外地人,我的房子也像久无人住。
露西拿行李进门时,我打开瓦斯炉煮了一壶大吉岭茶。我在火炉前坐着,静听她从容地安置行李,沐浴。我们即将讨论一件让我们心怯的事。
“你饿吗?”听到她进来,我问。
“不饿,有啤酒吗?”她问。
我迟疑了一下,回答道:“在吧台旁的冰箱里。”
我又听了一会儿她的动静,没有转身。我想让自己看着露西时,看到她如同我心目中的那副模样。我喝着茶,鼓起勇气面对这个和我有着若干相同的遗传基因、美得摄人心魄的聪慧女孩。经过这么多年,我们也该面对面了。
露西来到炉火边,坐在地板上,靠着石制壁炉喝啤酒。她自行穿了一套颜色鲜艳的运动服,那是我以前打网球时偶尔穿的。她打着赤脚,湿漉漉的头发往后梳。我意识到即使我不认识露西,在走过她身边时也会多看她几眼,这不只是因为她姣好的身材与脸蛋,还因为举手投足间的灵巧。她做什么似乎都轻而易举,这也是她朋友不多的部分原因。
“露西,”我说,“解释一下。”
“我被耍了。”她说着喝了口啤酒。
“如果那是事实,能说说怎么被耍的吗?”
“你说‘如果’是什么意思?”她紧盯着我,眼中噙满泪水,“你怎么会认为……哦,该死。这有什么意义?”她将目光挪开。
“如果你不告诉我真相,我也爱莫能助。”我说着,觉得自己也不饿了,到吧台倒了一杯苏格兰威士忌加冰块。
“我们从事实开始。”我走回椅子边,“有人上周二大约凌晨三点进入工程研究处——使用了你的身边识别码与指纹。辨识系统进一步显示,这个人,也就是拥有你的识别码与指纹的人,调阅了许多档案。注销时间是凌晨四点三十八分。”
“我被陷害了。”露西说。
“发生这件事情时你在哪里?”
“我在睡觉。”她愤然喝光啤酒,起身又去拿了一罐。
我缓缓喝着苏格兰威士忌,这种烈酒无法喝得太快。“据称,有几个晚上你的床铺空着。”我平静地说。
“你知道什么?那与别人无关。”
“当然有关,而你也知道。事发当晚,你在宿舍的床上吗?”
“我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在哪张床上是我的事,与他人无关。”她说。
一片静默。我回想着露西坐在暗处的野餐桌上,一个女人手拿火柴照亮了她的脸。我听到了她和朋友的交谈,也明白她言辞中所表达的情感,因为我知道什么叫做甜言蜜语,分辨得出含有爱意的声音。
“工程研究处发生侵入事件时你到底在什么地方?”我又问了一次,“或许我应该问你跟谁在一起。”
“我从没有问过你跟谁在一起。”
“如果问了能使我免去许多麻烦,你会问。”
“我的私生活与此无关。”她继续说。
“不,我想你是怕不被人接受。”我说。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几天前的晚上我看到你在野餐区,和一位朋友在一起。”
她将目光别开。“哦,原来你也找监视我。”她颤声道,“别浪费时间跟我说教,也别提什么天主教的罪恶感了,我不信。”
“露西,我不是在批判你。”我说,虽然就某些方面而言我的确是在批判她,“帮我了解情况。”
“你在暗指我不正常或变态,否则我就不需要别人来了解了。我可以让人不假思索地接纳我。”
“你的朋友可以为你在星期二凌晨三点的行踪做担保吗?”我问。
“不能。”她回答。
我只说了句“明白了”,就接受了她的回答。这意味着我认识的那个女孩已经不见了。我不认识这个露西,我也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她问我,这时夜色更浓了。
“我在北卡罗来还有一个案子要处理。我想我得在那边待一段时间。”我说。
“你在这里的办公室呢?”
“费尔丁替我看着。明天一早我还得上法庭,事实上,我必须打电话给罗丝确定时间。”
“什么案子?”
“凶杀案。”
“我想也是,我能跟你一起去吗?”
“如果你想去。”
“呃,或者我回夏洛茨维尔吧。”
“回去做什么?”我问。
“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到那边。”凌秀看起来有点惶恐。
“我不用车时你随便使用,你也可以去迈阿密,学期结束后再返回学校。”
她将最后一口啤酒喝完,起身,眼中再度泛着泪光,“你就承认吧,姨妈。你认为是我做的,对不对?”
“露西。”我坦白道:“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想,你的说法和证据表明的情况截然不同。”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她望着我,好像我让她心碎了。
“欢迎你在这里过圣诞。”我说。
11
第二天早晨受审的北里士满帮帮派分子穿着一件深蓝色双排扣西装,系一条打着完美蝴蝶结的意大利丝质领带。他的白衬衫看起来很整洁,胡子也刮得很干净,还戴着耳环。委任律师托德?科威尔将他的客户打扮得很体面,因为他知道陪审团很难抗拒“眼见为实”这种观念。当然,我也相信这句至理名言,所以我尽可能多带受害者的验尸彩色照片出庭。开着红色法拉利的托德?科威尔想必不太喜欢我。
“斯卡佩塔女士。”科威尔在这个秋高气爽的日子盛气凌人地说,“人们在可卡因的影响之下会变得很暴力,甚至会拥有超人的力气,是否真有此事?”
“可卡因的确会使服用者兴奋和产生幻觉。”我面对陪审团回答,“像你所说的,超人的力气通常都来自可卡因或PCP——一种马匹镇定剂。”
“受害者的血液中同时检验出可卡因与苯基柯宁。”听科威尔的语气,仿佛我已同意他的说法。
“没错。”
“斯卡佩塔女士,你能否向陪审团解释那意味着什么?”
“我首先要向陪审团解释,我是一个拥有法学学位的医生。我的专长是病理学,其次是法医病理学,这你应该很清楚,科威尔先生。所以请你称呼我斯卡佩塔医生,而不是斯卡佩塔女士。”
“好的,女士。”
“能否请你重述刚才的问题?”
“能否请你向陪审团解释,如果有人被检验出血液中同时含有可卡因和苯基柯宁,那意味着什么?”
“苯基柯宁是可卡因代谢后的产物。如果血液中同时含有这两种成分,意味着他服用的可卡因已部分代谢,尚未完全代谢。”我回答时发现露西坐在后方角落里,她的脸被一根柱子半遮着,看起来很颓丧。
“那意味着他吸毒已有很长时间,他身上的针孔更能证明这一点。这也表明,当我的委托人在七月三日晚上与他碰面时,面对的是一个极度激动、兴奋、暴力的人,我的委托人别无选择,只能自卫。”科威尔边说边踱步,光鲜亮丽的委托人望着他,像一只焦躁不安的猫。
“科威尔先生,”我说,“受害人乔纳?琼斯被一把可以装三十六颗子弹的九毫米口径手枪连开十六枪,其中七枪打中背部,还有三枪是近距离,甚至是贴着琼斯先生的后脑射入的。依我之见,这与自卫而开枪不符,尤其是琼斯先生的酒精度高达零点二九,几乎是弗吉尼亚州法定值的三倍。换句话说,受害者在遭到攻击时,运动神经与判断力已基本无法运作。老实说,如果琼斯先生当时能站得起来,我都会感到惊讶。”
科威尔转过身面对着波法官。自从我来到里士满,就听闻这个法官有个绰号叫“乌鸦”。毒枭呼吸厮杀、儿童带枪上学、在校车上互射,已经令他疲惫的心灵感到厌倦。
“法官阁下,”科威尔戏剧化地说,“我要求将斯卡佩塔女士的最后那段证词删除,因为那既是揣测也是煽动。无疑,那并非她的专业。”
“哦,我不认为医生所说超越她的专业范畴,科威尔先生,而且她已经很有礼貌地请你称呼她‘斯卡佩塔医生’。我对你的古怪行径与手段都已经很不耐烦了……”
“可是,法官阁下……”
“事实上,斯卡佩塔医生已经数次在我的法庭出庭,我对她的专业能力相当了解。”法官继续用他的南方腔调说,这令我想起了拉成长条的温热的太妃糖。
“法官阁下……”
“依我看她每天都在处理这种事情……”
“法官阁下?”
“科威尔先生!”“乌鸦”大吼一声,微秃的头部涨得发红,“如果你再打断我,我就以蔑视法庭的罪名起诉你,让你到监狱里住几个晚上!听清楚了吗?”
“是,法官大人。”
露西伸长了脖子观望,陪审团成员也都紧张起来。
“我要让记录员忠实地记下斯卡佩塔医生所说的话。”法官记下说道。
“没有其他问题了。”科威尔简洁地说。
法锤重重一敲,波法官结束庭审,也吵醒了后排一个戴着黑色草帽、一直在打瞌睡的老妇人。她吓了一跳,坐正后脱口而出:“谁?”之后想起自己身在何处,又开始哭泣。
“没事,妈妈。”另一个女人说。众人散去,各自去吃午餐了。
我在离城之前,顺道前往户籍资料处,我有一个老朋友兼同事在此担任户籍登录人员。在弗吉尼亚州,无论是出生或死亡,都得经过格洛里亚?拉文的签署才算合法。她像鲱鱼卵一样在这里土生土长,却认识各州的同行。承蒙格格里亚的鼎力协助,几年来我多次查证某人是否存活,是否已婚、离婚或经人收养。
她的同事告诉我,她在麦迪逊大楼的自助餐厅吃午餐。一点十五分,我看见格格里亚独自坐在一张桌子旁,一边吃着香草酸奶和什锦水果罐头,一边聚精会神地读一本厚书。从封面看,那是名列《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的平装惊悚小说。
“如果面对这样的午餐,我宁愿不吃。”我说着拉了一把椅子过来。
她一脸茫然地抬头看着我,随后喜形于色,“哎呀,老天,你在这里做什么,凯?”
“我就在街对面工作,你不会忘了吧?”
她开怀大笑,“能否请你喝杯咖啡?亲爱的,你看起来很劳累。”
格格里亚?拉文人如其名,长大后真的充满爱心。她五十来岁,心宽体胖,对经手的每一份文件都给予高度的耐心。对她而言,记录不只是整理文件和分门别类。无论高官显贵还是市井小民,她都一视同仁。
“我不喝咖啡,谢谢。”我说。
“我听说你已经不在街对面工作了。”
“我只离开了一两个星期,人们就急着炒我鱿鱼了,真有意思。我现在联邦调查局的法医顾问,经常来来去去的。”
“依据我听到的消息,应该是进进出出贝拉罗莱纳州吧。连丹?拉瑟前几天晚上也在谈斯坦纳家女孩的案件,这件事CNN也报道了。天哪,这里真冷。”
我环顾着阴冷的州政府自助餐厅,用餐的客人都很沉闷。许多人将皮夹克与毛衣都扣到下巴处,埋头猛吃。
“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