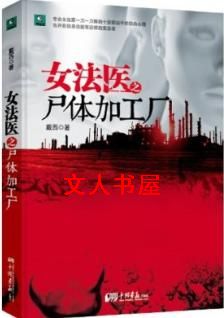首席女法医之人体农场-第1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你为什么要亵渎这小女孩的墓?”
在这一阵纷乱之中,马里诺突然像手上的野兽般大吼:“马上给我滚开!你们再妨碍调查,听见没有!去你的!”他重重地跺脚,“马上给我滚!”
记者们满脸惊慌,愣立当场。马里诺则继续朝他们咆哮,满脸通红,脖子上青筋毕现。
“唯一在亵渎的人是你们这些混蛋!你们再不走,我就砸你们的相机,砸任何我砸得到的东西,包括你们丑陋的脑袋!”
“马里诺。”我按住他的胳膊。他全身紧绷,有如钢铁。
“干这一行老是得应付你们这些混账东西,我受够了!听见了没有?我受够了,你们这群吸血鬼寄生虫!”
“马里诺!”我拉住他的手腕,吓得全身发麻。我从没见过他如此暴跳如雷。亲爱的上帝,我想,可别让他开枪杀人。
我走到他面前,想让他看着我,可是他眼神狂乱,跳向我的后方。“马里诺,听我说!他们走了,请冷静下来。听着,马里诺,放轻松,他们离开了,看到了吗?你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了,他们几乎都是逃跑的。”
那群记者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有如一群劫匪突然现形之后又消失得无影无踪。马里诺愣怔地瞪着眼,草地上空荡荡的,只有一枝枝塑料花和排列整齐的墓碑。钢铁碰击的声音此起彼伏。掘墓工人用钢锤与凿子敲开墓板的柏油封口,将棺盖抬到地面,我们装作没注意到马里诺跑到月桂树丛后呕吐时恐怖的咕哝声与呻吟声。
“还有这种防腐液吗?”我问鲁西亚·雷。对于蜂拥而至的媒体与马里诺的狂怒,他似乎觉得可笑,而不是深感其扰。
“我抹在她身上的那种或许还有半瓶。”他说。
“我需要知道化学成分,以便作毒物分析。”我解释。
“那只是福尔马林和掺了少量羊毛脂油的甲醇,像鸡汤一样常见。不过,我使用的浓度确实低一些,因为她身材娇小。你那位刑警朋友看起来脸色不太好,”马里诺从树林后出现时,他补上一句,“你知道,流行性感冒正在肆虐。”
“我看他不是患流行性感冒了。”我问,“那些记者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
“你可把我问倒了。但你知道,人就是这样。”他停下来吐口水,“总会有人四处传播闲言碎语。”
埃米莉的钢制灵柩涂得像他墓旁的野生萝卜一样白,掘墓工人无需吊车就可以将它抬起来,放到草地上。和里面的尸体一样,灵柩很小。鲁西亚·雷从口袋中取出一个无线电对讲机。
“你可以过来了。”他说。
“好的。”一个声音回答。
“不会再有记者了吧?”
“他们都走了。”
一辆黑亮的灵车从墓园入口驶进,在树林和草地之间穿梭,灵巧地闪过一座坟墓与一棵棵树木。一个身穿防水外套、头戴平顶卷边帽的胖子下了车,打开车尾的门,看着掘墓者将灵柩搬上车。马里诺则站在远处观望,用一条手帕抹着嘴。
“我们得谈一谈。”我走近他轻声说,这时灵柩已经上路。
“我现在什么也不想听。”他脸色苍白。
“我必须到停尸间与詹雷特医生碰面。你要一起去吗?”
“不,”他说,“我要回轻松旅游汽车旅馆。我想喝啤酒直到再吐一次,然后改喝波本威士忌。我还要打电话给韦斯利那个混蛋,问他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因为我已经没有一件像样的衬衫可以穿了,这一件刚才也毁了。我连条领带都没有。”
“马里诺,回去躺一躺。”
“我睡的小床就这么一点大。”他用双手比画着。
“服用点镇定剂,尽量多喝水,再吃些吐司。我在医院忙完之后会去看你。如果本顿打电话来,告诉他我带着移动电话,或者让他打我的寻呼机。”
“他有你的这些号码?”
“是的。”我说。
马里诺又用手帕擦擦脸,看了我一眼。在他试图掩饰之前,我看到了他受伤的眼神。
9
快十点时,我与灵车同时到达医院,詹雷特医生正在处理文件。我将外套脱下,换上一件塑料围裙时,他紧张地朝我笑了笑。
“你想不想猜猜媒体怎么知道我们要开棺验尸的?”我摊开一件手术袍。
他满脸惊讶。“怎么了?”
“有六七个记者出现在墓园。”
“真过分。”
“我们必须确保不会再走漏消息,”我将那件长袍在背后系住,设法使自己心平气和,“这里发生的事不能传出去,詹雷特医生。”
他没有搭腔。
“我知道我只是客人,如果你厌恶我的出现我也不会怪你,所以请不要认为我对你的立场或权威视若无睹。但我向你保证,无论杀害那个小女孩的是谁,他都会留意新闻的发展。一旦消息走漏,他就会有所发现。”
为人随和的詹雷特医生仔细聆听,丝毫不以为忤。“我只是想打听一下他们知道些什么,”他说,“问题是风声一传出去,就会有很多人知道。”
“我们要确定今天在这里查出来的情况不能再传出去了。”我说。这时我听到灵柩送来了。
鲁西亚·雷率先进门,跟在他身后的是那个戴着平顶卷边帽的人,他用教堂的手推车推着白色灵柩。他们将灵柩停放在验尸台旁。雷从他的外衣口袋中掏出一把金属扳手,插入灵柩顶部的一个小洞中。他慢慢扳开封口,仿佛在发动一辆古董车。
“应该好了。”他说着将扳手放回口袋,“希望你们不介意我在一旁看看我的成果。对我而言,这是很难得的机会,因为我们没有将人埋葬之后再挖出来的习惯。”
他伸手要将棺材板掀开。如果詹雷特医生未出手制止,我会出面。
“通常这不是个问题,鲁西亚,”詹雷特医生说,“但现在实在不宜有外人在场。”
“我想这未免太大惊小怪了吧。”雷收起笑容,“我又不是没见过这孩子。我对她全身上下一清二楚,比她母亲知道得还多。”
“鲁西亚,你必须走了。你走之后,我和斯卡佩塔医生才能验尸。”詹雷特医生仍用他那种感伤温和的口吻说,“完成之后我会通知你。”
“斯卡佩塔医生,”雷注视着我,“我必须说,联邦政府人员进城之后,人们都变得不友善了。”
“这是凶杀案的调查工作,雷先生,”我说,“请不要当成是冲着你来的,因为我们无意如此。”
“走吧,比利·周,”这位殡仪馆负责人对戴着平顶卷边帽的人说,“我们去吃点东西。”
他们离开了。詹雷特医生将门锁上。
“真抱歉,”他说着戴上手套,“鲁西亚有时候可能很傲慢,其实人很不错。”
我起先怀疑埃米莉的尸体未经适当的防腐措施保护,或是入殓方式未能与她母亲所付的金额匹配。但在我和詹雷特医生将灵柩打开时,并未看到任何敷衍了事的痕迹。白色的绸缎衬布覆在她身上,上面摆着一个用白色面纸和粉红色丝带包装的包裹。我开始拍照。
“雷提起过这东西吗?”我将包裹递给詹雷特医生。
“没有。”他满脸困惑,翻来覆去地查看包裹。
我将衬布掀开,强烈的防腐香油味扑鼻而来。埃米莉·斯坦纳躺在衬布下,穿着淡蓝色天鹅绒高领套装,辫子上绑着同样质料的蝴蝶结,脸部已出现开棺验尸时常见的白色霉菌,像戴着一张面具,摆在腹部《新约》上的双手也有。她脚穿及膝的白色袜子、黑色皮鞋。全身上下,没有一件像是新的。
我又拍了一些照片,随后和詹雷特医生将她抬出灵柩,放在不锈钢桌上,脱下她的衣服。甜美的小女孩服饰下,隐藏着她丧命的恐怖秘密:自然死亡的人不会有她身上的那些伤痕。
每个诚实的法医都会承认验尸很恐怖。这种开膛剖腹和外科手术截然不同。解剖刀由锁骨切到胸骨,再笔直划过躯干,绕过肚脐后在耻骨告一段落。从头部后方沿着一只耳朵划到另一只耳朵将头壳掀开,也不怎么令人好受。
当然,头部的伤口没有缝合,只能用发饰和发型加以掩饰。浓妆修饰的埃米莉,被人从上到下划开了,仿佛一个伤感的布娃娃被剥掉衣服,遭到狠心的主人抛弃。
水滴入钢制洗涤槽中咚咚做响。我和詹雷特医生擦拭着尸体上的霉菌、妆容和头部后方伤口的肤色黏合剂,以及大腿、上胸、肩部遭剥皮处等部位。我们摘下埃米莉眼睑下方的眼角膜,取出缝合线。在强烈的气味从胸腔散发出来时,我们涕泪直流。各个内脏都沾满了防腐粉末,我们迅速而匆忙地擦拭干净。我检查颈部,找不到任何詹雷特医生没有记录的情况。然后我将一把凿子插入臼齿,迫使嘴巴张开。
“太僵硬了,”我失望地说,“我们必须将咬肌切断。我要看看舌头的解剖位置,再检查后咽喉。但我不能肯定,或许我们做不到。”
詹雷特医生在他的手术刀上装了一片新刀刃。“我们要找什么?”
“我要确定她有没有咬舌。”
几分钟后,我发现埃米莉曾咬舌。
“她的舌头边缘部分有咬痕,”我指出,“你能不能量一下?”
“八分之一英寸长,四分之一英寸宽。”
“出血部分大约四分之一英寸深。看来她咬了不止一次。你有何看法?”
“我看也很有可能如此。”
“由此判断,她临终前曾经癫痫症发作。”
“或许是头部的伤势造成的。”他说着去取相机。
“有可能,但为什么脑部状况却显示她中弹后存活时间并不久,不足以出现癫痫症?”
“我猜我们拥有无法回答的同一问题。”
“没错,”我说,“真令人费解。”
我们将尸体翻过来,我聚精会神地研究引发这次开棺验尸的斑痕。验尸照相人员已到达,并架好了设备。整个下午,我们拍了无数卷照片,有红外线、紫外线、彩色、高反差、黑白,等等,还加装了许多特效滤光镜与镜头。
接着,我从医事包中取出六个黑色的环,那是用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塑料制成的,说得明白一点,就是制造水管和下水管道的那种材料。每隔一两年,我就会找一位认识的牙科法医帮我锯这种八分之三英寸厚的环,打磨光滑。幸好,我无须经常使用这种古怪的装备,因为从尸体上移除人类的咬痕或其他的印痕的机会很少。
我决定采用直径三英寸的一个环。我用技工的冲压机在环的两侧压出埃米莉·斯坦纳的案件编码和身体部位。人的皮肤如画家的画面般有弹性,所以在割下埃米莉左臀部那个斑痕后,为了使其结构维持原状,还得补上一些稳定基质。
“你有没有强力胶水?”我问詹雷特医生。
“当然。”他拿了一管给我。
“如果你不介意,请拍下每一个步骤。”我对摄影人员说。那是一个瘦小的日本人,一直动个不停。
我将环摆在斑痕上,先用强力胶水将它初步固定在皮肤上,再用缝合线彻底固定。随后我将环的周围组织割开,整个放入福尔马林溶液中。这期间,我一直在推敲这块斑痕有何意义。那是一个不规则的圆,还有一个不完整的奇怪褐色污点,我相信那是某种图案的印痕。然而无论用拍立得从多少个角度观察,我都想不出那到底是什么图案。
摄影人员离去后,我和詹雷特医生通知殡仪馆的人员将尸体运回。这时,我们才想起用白色面纸包着的包裹。
“怎么处置这东西?”詹雷特医生问。
“必须将它打开。”
他将干毛巾摊在一部手推车上,把那个礼物摆在上面。他小心翼翼地用手术刀将面纸割开,里面出现了一个女性六号鞋的旧鞋盒。他又割掉了几层面纸,将盒盖打开。
“哎呀。”他轻叫了一声,张皇失措地凝视着小女孩的陪葬物。
盒子内,两层保鲜膜下裹着的是一只死猫,顶多几个月大。这是一只母猫,没有戴项圈,一身黑色的皮毛,但脚部是白的。我将它取出来,它僵硬得像三夹板,纤细的肋骨外突。我看不出它的死因,于是拿着它去照X光,几分钟后将X光片置于光板上。
“它的颈椎骨折了。”我说着汗毛直竖。
詹雷特医生靠近光板,紧蹙着眉头。“看来颈椎已经移位了。”他用指关节触碰着X光片,“太不可思议。它的颈椎向一侧移位。我认为那不是被车撞的。”
“是的,”我告诉他,“它的头部被人朝顺时针方向扭了九十度。”
将近晚上七点,我回到轻松旅游汽车旅馆时,马里诺正坐在床上吃一客奶酪堡。他的枪、手提箱、汽车钥匙都扔在另一张床上,鞋子与袜子随意丢在地上。看得出来,他不久前才回到这里。我走向电视机将电视关掉时,他目不转睛地望着我。
“走吧,”我说,“我们得上路了。”
依照鲁西亚·雷所言,他可以对天发誓是德内莎·斯坦纳将那个包裹放进埃米莉的灵柩中的。他简单地认为这个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