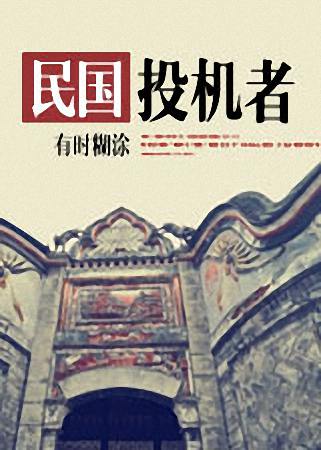去趟民国:1912~1949年间的私人生活-第2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出于对刘师培学问的敬重,黄侃一向对刘执弟子礼。1915年,刘参与筹安会活动,招集北京学术界名人到他家,商量“联名上书”、拥袁世凯称帝事宜。黄起初不明真相,到了刘家,听明意思后,他起身说了句:“刘先生以为这样好,你一个人去办好了。”言毕,拂袖而去。
钱穆曾谈及刘文典:“有一年,余适与同车,其人有版本癖,在车中常手夹一书阅览,其书必属好版本。而又一手持卷烟,烟屑随吸随长,车行摇动,手中烟屑能不坠。”
钱穆的不少学生回忆说,他讲先秦史别具一格,是“倒叙”式的,即从战国讲起,而春秋、西周,并且从不循规蹈矩地面面俱到。有学生描述说:“他讲课每讲到得意处,像和人争论问题一样,高声辩论,面红耳赤,在讲台上龙行虎步,走来走去。”“他以炽热的情感和令人心折的评议,把听讲者带入所讲述的历史环境中,如见其人,如闻其语。”
新凤霞晚年不离轮椅。但在病前,她走路一向风风火火,比一般人要快得多。据新回忆,这是小时候“赶包”练出来的。当年她和母亲在天津演戏,从南市到法租界、劝业场,没钱坐车,一路都是连走带跑。长此以往,便养成了“快走”的习惯。
10.性格
段祺瑞性憨直,经常口无遮拦。有一次他在执政府当着众多大员的面指着北京卫戍总司令鹿钟麟说:“这是我从前的兵。”后来段被通缉,鹿主动请缨捉拿他。
阮玲玉和胡蝶都曾供职明星影片公司,两人性格迥异。阮玲玉是苦孩子出身,性情刚烈、奔放,在摄影棚里想哭就哭,想笑就笑,对大导演张石川也并不言听计从,有时甚至令张颇伤脑筋,不久即脱离明星公司。胡蝶则是另一类人,银幕上下、从里到外,她都是美人,而且为人柔顺、和蔼、乖巧,拍戏很用心。成了“电影皇后”以后,也不拿架子。她在明星公司一干就是十多年,直至抗战爆发。两人截然不同的命运和结局,似乎应了那句“性格使然”的老话。
陈强初演《白毛女》,对黄世仁强奸喜儿那场戏,无论如何也演不到位,其实是成心不想演好。导演正告他:“你不是陈强,是黄世仁。”陈强狡辩道:“这戏演好了,还有人喜欢我吗?我还没结婚呢!”
李叔同和欧阳予倩早年同在日本留学。一日,李叔同约欧阳予倩早8点到他家,两人住处相距很远,欧阳予倩被电车耽误,晚到了几分钟,名片递进去后,李叔同从楼上打开窗户,说:“我和你约的是8点钟,可是你已经过了五分钟,我现在没有工夫了,我们改天再约罢。”说罢关窗离去,欧阳予倩只好掉头往回走。
李叔同在浙江第一师范任教时,宿舍门外有个信插。一天晚上,他已经睡下,学校的收发员跑来敲门,说有电报,李在屋里应道:“把它搁在信插里。”第二天早上他才取看电报。事后有人问:“打电报来必有急事,为什么不当时拆看?”他答:“已经睡了,无论怎么紧急的事情,总归要明天才能办了,何必着急呢!”
《大公报》两大当家人——胡政之和张季鸾——工作上的配合天衣无缝,但性格迥异。据说胡工作之外不大合群,奉行独乐主义,更有人指其“孤僻成性,同人对之尊而不亲”。而张季鸾则与下属打成一片,“喜交游,善谈笑,爱热闹,嗜饮啖”。他一到,往往就宾客盈门。无应酬时,他愿意拉一二同人去吃小饭馆,闲暇时也时常约同好唱唱昆曲,是个不缺亲和力的总编辑。
何应钦生性懦弱,行事优柔寡断,缺少勇气、毅力和决断力。与此相应的是,他待人谦恭和蔼,少有恶言急色,对朋友极有礼貌,对学生和部属也从不摆架子。无论上班和开会,何一贯遵守时间,准点到,不缺席。但何也有手面不大的弱点,对部下往往有一钱如命的苛求。
刘峙接人待物好打哈哈,口齿笨拙,不善辞令,貌似忠厚实诚,实则内藏机谋,个性倔强,认准的事情绝不动摇。他常对人说:“我刘经扶是大智若愚的人。”
宁汉合流后,被软禁于南京孔祥熙宅的胡汉民获释。他离开孔宅的当日,门前车水马龙,除蒋介石之外的几乎所有文武大员都来送行。胡由女儿木兰扶出大门时,众人排列两旁,纷纷向胡问好。胡不予理睬,旁若无人地直趋坐车,上车后抬眼看见囚禁期间负责他警卫事宜的一个工作人员,便又下车上前与之握手,连声道谢。
宋霭龄为人低调,平时深居简出,不爱抛头露面。但她有掌控局面的能耐,可以摆平蒋宋孔三大家族之间的摩擦和矛盾,连蒋介石遇事都让她三分。她称蒋介石为“介兄”,是蒋周围唯一一个不用“总裁”、“委员长”称呼他的人;在公众场合,蒋介石对她毕恭毕敬。
孔祥熙表面上嘻嘻哈哈、东拉西扯,对铭贤学校学生、山西同乡、旧日部属都视为亲信,给人以“厚道”和“怀旧”之感。
陈布雷为人质朴,待人宽厚,助人为乐。抛开职业和立场不论,他是个好人。
蒋介石平时不苟言笑,但也有例外。某次蒋的侍从室组长以上人员聚餐,蒋也加入,宋子安在座。席上宋子安说到一件关及卫生的话题时,蒋指着侍从医官吴麟孙开玩笑说:“不卫生找他好了。”
方志敏在狱中给鲁迅写过一封密信,想请鲁迅托宋庆龄向蒋介石保释其出狱。这封信是通过胡风转给鲁迅的,胡风回忆说:“鲁迅看了后,沉默了好一会,说,蒋介石是什么人?这绝对做不到。”
上世纪20年代,清华学生有“四子”之说,即子沅(朱湘)、子潜(孙大雨)、子离(饶孟侃)、子惠(杨世恩),四人同住西单梯子胡同的两间房内。“四子”中唯有子惠性情随和,与人无争;另外三个诗人的性格都属于急躁暴烈型。直到上世纪80年代,四人中硕果仅存的孙大雨提起朱湘以老大自居的态度对待他,仍不能释怀。
朱湘的朋友罗念生说:“朱湘性情倔强、暴烈、傲慢、孤僻,表面上冷若冰霜,内心里却热情似火。”“他并不懂得人情世故,太相信别人,太诗人化了,所以他处处上当。”
上世纪30年代,一次学者熊十力与冯文炳因争论一个问题互相抬杠乃至扭打起来,熊十力声色俱厉地说:“我代表的是佛,你不同意便是反对佛!”
抗战期间,五战区豫西别廷芳部的民团曾建奇功。别廷芳目不识丁,为人清廉正直。豫西产西瓜,历年偷瓜者不绝,别廷芳便发布“偷瓜者死”的告示。一日,别的女婿途中口渴,就便在附近瓜田里拿个西瓜吃了。此事被别知道后,立即吩咐卫兵,推出枪毙。别的独生女抱住父亲大哭,替丈夫求情,说如果丈夫被杀,女儿终身靠谁呢?别把女儿推开说:“枪毙了他,有我养你一辈子!”
1943年秋,刘峙接替李宗仁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对刘的评价是:“身为大将而胆小如鼠。”据说刘夜里起来小便,竟然要两三个卫兵陪着。
熊十力性狷狂,曾说胡适的科学知识不如他,冯友兰不识字,金岳霖讲的是戏论。
曹礼吾和曹聚仁曾同在暨南大学任教,两人是朋友,却常被别人弄混。曹礼吾对曹聚仁说:“我的名片上要附刊一行字——并非曹聚仁。”曹聚仁说:“他性慢,我性急;他把世事看得很穿,我一天到晚要出主意,不肯安分;他衣履非常整洁,我十分不修边幅;然而我们非常相投,可以说是管鲍之交;用佛家的说法:‘这是缘吧!’”
马寅初一次去拜访黄侃,和他说起《说文》。黄很不客气地说:“你还是去弄经济吧,小学谈何容易,说了你也不懂!”
抗战期间,一次黄琪翔请田汉吃饭,事先说好是一桌客人。届时田汉带着三十来人去赴宴,黄见状哈哈大笑:“我事先就防了你这一手,恰好准备了三桌。”
胡汉民谈到孙科时说:“因为他是中山先生之子,所以有革命脾气;因为他在外国长大,所以有洋人脾气;因为他是独子,所以有大少爷脾气。他有时只发一种脾气,有时两种一同发,有时三种一起发。”
邓散木腕力极强。他年轻时,一次去酒馆,跑堂的见他不像是有钱人,就把他晒在一边,专心去侍奉几个纨绔子弟。邓也没说什么,向店里要了几个核桃,放在桌子上,右手掌一运力,核桃应声而碎。店家及邻座都大吃一惊,以为遇上“绿林”高手了,赶紧过来招待。
邓散木家里挂着这样一张《款客约言》:“去不送,来不迎;烟自爇,茶自斟。寒暄款曲非其伦,去、去,幸勿污吾茵。”他当年的结婚请柬也别具一格:“我们现在定于中华民国十五年(1926)四月十八日——星期日——下午三点钟在南离公学举行结婚仪式,所有繁文俗礼,一概取消,只备茶点,不设酒筵。到那时请驾临参观指教,并请不要照那些可笑而无谓的俗例送什么贺礼;倘蒙先生发表些意见,和指导我们如何向社会的进取途径上前趋,那便是我们比较贺礼要感谢到千万倍的。”
孔祥熙曾请潘光旦调查其家谱,以证明他是孔子之后,潘一口回绝,说:“山西没有一家是孔子之后。”
丰子恺一向蔑视权贵。住在缘缘堂时,家乡的县长慕名求见,事先带话来,丰便在门上贴上“谢客”两字。抗战期间,丰住在贵州遵义,当地豪绅罗某几次上门求画,都被挡了回去,某日罗突然袭击,丰正吃午饭,不及回避,只得倒了杯清茶,敷衍了几句,即起身进卧室了。抗战胜利后,孔祥熙想出高价买丰子恺的西湖套画,杭州市长也曾亲自到家中求画,都被丰拒绝。
王云五说:高(梦旦)先生是一个老少年。
叶公超说:“他(徐志摩)对于任何人、任何事,从未有过绝对的怨恨,甚至于无意中都没有表示过一些憎嫉的神气。”
巴金告诉沈从文,他不喜欢在公众场合讲话。沈从文便说起,他第一次上中国公学的讲台,教室里坐满了学生,他骤然感到那么多年轻的眼睛盯着自己,立时涨红了脸,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好在黑板上写了五个字:“请等五分钟。”而当时是中国公学学生的罗尔纲的回忆则是另一个版本:“沈从文只读过小学,是胡适把他安排上大学讲座的。选他课的约有二十多人,但当他第一天上课时,教室却坐满人,他在讲坛上站了十多分钟,说不出话来。突然他惊叫了一声说:‘我见你们人多,要哭了!’”
抗战期间,当年上海滩的两个大佬虞洽卿和王晓籁常往返于重庆和昆明之间。两人行事风格迥异。虞洽卿到昆明都借宿友人家,友人嗜烟,不及招待,早饭由虞自理。虞洽卿每天只花一毛钱买四个小馒头,后物价上涨,馒头变成三分一个,有人戏问虞洽卿如何应付,他答:“我改吃三个,反而可省钱一分。”一女戏子曾随虞洽卿从重庆到昆明,有人问她,虞是阔人,路上用什么招待呀?她答:至多吃到蛋炒饭,这就算最丰盛的了。王晓籁则是另一路,每天牛奶面包,听任物价上涨,从不更改。
傅雷多才多艺但性格暴烈急躁,楼适夷说:“我亲眼看见他抓住孩子的头发,提着小脑袋往墙上去撞,好像立时三刻要把孩子处死的神情。”抗战结束后,昆明一家美术学校请傅雷去当教授,傅雷便从上海起兵发马、捆载而去,一路跋山涉水。到昆明的当天,即去参加一个讨论教学计划的会议,因一言不合,他马上扛起尚未打开的行李,回了上海。
林语堂用英文写成《吾国吾民》,并在美国成为畅销书后,决意赴美从事英文写作。这是30年代中期的事情。当时林在上海已经住进花园洋房,过着舒适惬意的生活。但主意一定,便可弃这些如敝屣,可见林为人的有决断。
周扶九本是江西盐商,发迹后在上海置有大量地皮房产,成为巨富。周为省钱,外出从不乘车。有一晚,周从外面提着灯笼回家,见前面一顶轿子前后都挂着玻璃灯,便尾随其后,吹灭手中灯笼里的蜡烛。一直走到家门口,周正为省下的半截蜡烛窃喜时,定睛一看,从轿子上下来的,却是他家的媳妇,周气急之下,差点背过去。
郑超麟早年曾与瞿秋白同事。他晚年回忆说:“我佩服瞿秋白的多才多艺,如鲁迅说的。他政治上很敏感,工作努力,但性格根本上是软弱的。杨之华一次告诉我,她某日与秋白同坐电车,车上一个人瞪目对着秋白看,秋白当时吓得面如土色。”
抗战时期,傅斯年常在国民参政会上“放炮”,蒋介石私下请傅斯年吃饭,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答:“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应该信任你所信任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