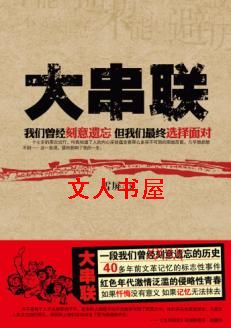青春之火-第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你可知道那时候你主人往那里去的?”
“知道的。太太早一天说过,昨晚上少爷要到汉口路钱家去吃喜酒。他出去时穿的也是新衣裳。”
“但你主人晚上回来时,你可知道他是不是确实吃过喜酒?”
“是,他确实喝过酒。因为他叮嘱我把前后门关好的时候,我还觉得他的嘴里酒气直冲。”
霍桑停了一停,说道:“好了。现在你好好地看守大门。如果有别的事回头再问你。”
霍桑走出门房的时候,汪巡官便挺挺腰走近去点头招呼。他分明认为他发觉的足印在全案上占着重要的地位,故而急不容缓地要把他所发见的成绩报告霍桑。可是事不凑巧。这时候姚国英正也从里面匆匆出来。他一见霍桑,便抢先开口,陈说他问话的结果。他已问过死者的母亲,据说有刚的朋友很多,但绝少冤家,若要仔细,可去问面粉公司里的朋友。关于纳妾的事,虽然谈过一回,可是因着他的妻舅做过县知事的颜小山的反对和他的妻子颜撷英的阻挡,没有成功。昨晚发案以后,张母和效琴到了楼上,都吓得什么似的,各自归房,直到金寿领了颜撷英回来,母女俩才同王妈下楼。至于铁箱内的银钱数目,他母亲完全不知道。因为有刚的嗣父张世勋在临死时的时候,除了张母的一部分养老费以外,已将遗产平均分给兄妹两个。所以有刚分内的财产,只有他一个人掌管,家中人都不知道底细。
霍桑听姚国英说完,说:“那么,银钱的数目在这里是问不出的了。”
我并不是有意和汪熙年争先,但谈话的题目已关涉我的任务,便再度剥夺了他的发言机会。
我插口说:“我知道。至少是一千五百元。”
汪熙年向我眨着白眼。姚国英也抬起他诧异的眼光,向我呆瞧。
霍桑立即问道:“包朗,你可是发现了什么证迹?”
“是。我寻得一个银行存折。他昨天在沪江银行里提出了一千五百元。”
我就将在书桌抽屉里得到的存折和照片信笺等物,都拿出来给霍桑和姚国英看。他们都承认照片和信笺非常重要。姚国英将这证物收藏好。这当儿急坏了汪熙年巡官。他在忍无可忍之后,终于不甘缄默。
他大声说。“那边还有一个凶手的足印呢!”
他的报告是用着郑重方式发表的,虽曾引起姚国英的惊异的一瞬,但霍桑却只淡淡地点一点头,似乎不以为意。我倒反替汪巡官有些难堪。
霍桑旋过头来,答道:“那足印不是在那发案室的第一个窗口外面吗?这个刚才我也已瞧见,是的,确很重要。不过汪先生就认做是凶手的足印,如果没有别的证明,似乎还嫌太早些儿。”
自然,这批评会使那胖子大大地扫兴。但解救他的两眼交替眨而口吃无言的窘态的,也还是霍桑。
他说:“好罢。我们回进去坐一坐,商量一个办法,才可以着手侦缉凶手。”
第六章 两重谋杀
我们在客室中把彼此的成绩交换过以后,又商议了一会,就假定这是一件复杂幻秘的谋杀案,而且是两重谋杀——一是中毒,一是刀刺。凶手有两个,动机也许是各别。据霍桑单独的见解,有刚不但中毒,却还是因毒而死的。为着法律上的佐证,故而他曾请许济人医官特别重视这一点。至于有刚被害的原因,就毒与刀两方面推测,有如下几种可能:
下毒的,屋内人屋外人都有可能。屋外人的注意点,自然在吃喜酒的钱家方面。屋内人,除了仆役们因着死者的脾气太坏受了怨屈阴损报复以外,他的妻子颜撷英最有嫌疑。据我们所知,夫妻间并不和睦,并且伊的装饰非常时髦,行动又的确是非常自由的。还有书桌抽屉中发现的那一封信,很像是有人写给有刚的匿名信,有刚特地录出一份,准备有什么作用。第二,论行刺一点,瞧了有刚的打扮和他书桌上的小报,他的和女伶来往,加着抽屉里书中夹着的那些女子照片,显见他是一个好色之徒。同时他又是个酗酒的赌徒。他近来又有畏惧什么人的表示。若使假定他因着争风吃醋,外面有什么冤家或情敌,那也是有可能性的。此外或是有什么人因财起意。例如那辞歇的魁林,会不会偶然回来?或是和金寿有某种勾通?还有那打杂差的阿莱在昨天晚饭之前,忽然有人来报告他母亲有病,因此告假回去,似乎也不能不认为凑巧可疑。
我们凭着这三种理由,就依照旧例,彼此分工办事。霍桑自己到靶子路颜家去探听。因为这一着最关紧要,并且颜撷英又是我们的委托人,所以霍桑不得不亲自去走一遭。姚国英担任往汉口路钱家去,调查有刚昨晚上吃喜酒时的情形,和有刚同席的是那几个人。我一个人往南市去找阿荣,查问他昨天晚上是否当真回家里去。内中要算汪巡官所担任的比较最省便,只在本区中调查,近几天来张家附近有没有可疑的人。
计议妥定,我们四个人便都从张家出来。我一个人先自回寓。因为那天早晨,我穿的衣服不少,这时候骄阳临空,气候转热,我不能不回去换一身较轻便的衣服。
我到了寓中,就上楼去更衣,一边推想这案子的情节。这种二重谋杀的案子,我们探案以来,还是破题儿第一遭。这案子从情节上看,显然有两个凶手:一个下毒,一个行刺。霍桑曾假定那醉汉的死因是由于中毒,刀刺倒不是主因。那么下毒的人是谁?是屋外人,还是屋内人?若是屋内人,可就是有刚的妻子颜撷英?照目下的情势揣测,伊的嫌疑负得最重。但伊既谋杀了伊的丈夫,怎么竟还敢登门请教我们?自己做了贼,帮同着呼叫捉贼,原是一种很普通而有效的卸罪方法。也许伊来请教我们,只是伊的一种烟幕,目的在利用霍桑做一个避嫌疑的幌子。如果如此,霍桑又怎么样应付?他可会庇护伊吗?不,不,霍桑是主持公道的人,公和私的界限分别得最严格。我相信他决不会毫无理由而徇一人的私谊,干违法的勾当。但假使伊的谋杀有刚,或者竟是有刚不义的反响,那么霍桑将怎样结束这件凶案?又怎样处置伊呢?
我换好了衣服,又在办事室中吸一支纸烟,休息片刻,等到纸烟烧尽了,正待拿了帽子往南市去,忽见霍桑气息咻咻地走进来。
他一见我,很诧异地问道:“你还没有往王家码头去过?”
我点点头。“我正要动身去。”
“既然如此,你姑且再坐一会。我同你一块儿去。”
“你从哪里来?可有什么端倪?”
我放下帽子坐下来。霍桑取出一支白金龙,燃着了坐在藤椅上,舒适地吸几口。
他答道:“我在颜家的邻居人家探访过一会。据说那颜撷英回母家之后,时常和年轻的女伴们出去逛游戏场。这确是事实。”
“那么匿名信中的话不像是虚构的了。”
“是,一部分总已实在。”
“别的呢?”
“我还见过颜撷英和伊的哥哥颜小山。”
“他怎么样说?”
“他自然是竭力袒护他的妹妹,请求我把这件事弄明白。他说有刚是个登徒子,确曾有过纳妾的提议,因着他的反对,才不敢实行。又据颜撷英说,有刚又曾借着没有子嗣为由,露过离婚的意思,可是也为着畏惧伊的哥哥,说不出充分的理由,到底不敢出口。”
“照你想,颜撷英有没有谋害丈夫的嫌疑?”
霍桑连续吸着烟,还没有答复,忽而电话铃响。他忙起身去接。一会。他回进来兴冲冲地向我报告:
“电话是汪熙年巡官打来的。他虽很想努力,可惜总是吃力不讨好。这一次却已有些效果。”
“什么效果?有什么新发现?”
“他说他已把全区的警士们一个个都仔细问过。在昨夜里十一点三刻的时候,有一班巡逻的警士们经过虬江路张家的洋房门前。他们都看见一个穿黑衣的男子从张家的铁条大门里出来。这是多数警士都瞧见的,当然不会错误。这一个发现在案子上不能不算是很重要的。”
“唔。你想这个人可就是我们理想中的那个刺客?”
“也许是的。据金寿说,昨夜他和颜撷英走出颜家门口的时候恰正打十二点钟。从虬江路到靶子路敏德里,坐黄包车至少得十多分钟。他到了颜家,又等他的主母从床上起来,梳洗好动身,也得再耽搁十多分钟。这样合证起来,可知金寿从张家出去,应得在十一点半左右。当十一点三刻时分,警士们所见的那个从张家出来的黑衣男子,分明不是金寿,却是另一个人。这一点我相信已没有疑义。”
“不错。昨晚上张家里除了金寿,没有第二个男子。那人一定是行刺的凶手无疑。但你想这个人在什么时候进张家去的?”
“金寿说过,当晚饭的时候,他曾经到里面厨房里去搬晚饭。那时候大门上当然空虚没有人。在这个当儿,若使有人混了进去,匿伏在树荫后面,或是躲在后面的小园中,等待机会动手,自然是人不知鬼不觉的。或者在金寿十一点半出去报信的时候,屋子里反而静了,那人以为机会成熟才悄悄地进屋子里去,也未可知。”
我反辩道:“你第一个理由还近情。第二个理由,我不敢赞成,我看你还有些矛盾哩。”
他很疑讶似地说:“矛盾?你指什么说的?我不明白。”他张大了两眼向我望着。
我说:“金寿出去报信是在有刚死之后。你怎么说凶手进屋子里去反在金寿出去以后?”
霍桑仍瞧着我。“唔,这就是你所谓矛盾点吗?其实你自己太粗心了。你得知道这是一件两重谋杀案啊!”
我呆了一呆,一时不能回答,就用纸烟掩护我的惶惑。
霍桑继续说:“虽然,你也许有你的理解。现在姑且把你想象中对于那人的举动说说看。”
我对于这个人果然有一种假定的理解。霍桑既然叫我说,不妨就乘机和他商酌一下。
我吐了一口烟,说:“我也假定那人在晚饭时潜进了大门,伏在树后。这一点和你的见解相同。直到十点钟后,有刚从外面回来,进了书房。那人先到窗口外面,踮足向书室内探望,因此窗下的草地上就留着半个很深的足印。接着他就走进书房,和有刚会面。那人是否为着寻仇而来,或是向有刚索什么东西,我不知道。但瞧他们俩争吵的声音和痕迹,显见彼此起初曾用过武的。后来有刚不胜,就被那人刺死。那人又取了钥匙,偷开铁箱,窃取了银钱,然后再悄悄地出去。你以为对吗?”
霍桑蹙着双眉,两眼直瞧看地毯,摇头说:“不对。你我的设想,唯一的不同点,就在致命的缘由。”
“你可是说有刚一定是因毒致命,不是因刀致命的?”
“是。我相信如此。我敢说他们并没有用武。但瞧有刚身上的一只金表丝毫没有损伤,便是一个明证。我料他一定是因毒致命。”
“不过许医官还没有证明啊。”
“他的证明只是一种法律上的手续。其实这一点我早已确定了。……晤,你是不是笑我夸口?我说给你听。有刚的伤痕,你也瞧见的。他的伤口平齐,四周又没有血渍,显见当刀刺的时候,他身上的血运已经停止,肌肉的皮肤也都已失却了弹性,所以伤口周缘一些没有卷缩的痕迹。这原是普通的生活反应。并且他的衬衫上也只有些血水,并不是鲜红的血液。这还不能算死后行刺的证明吗?凭这一层,就可见行刺的凶手进去一定是在金寿出外以后。你不能说我矛盾。况且金寿当时只知道有刚气绝,那时有刚身上是否已有刀痕,金寿却没有瞧。所以我料那人的行刺定是在金寿出外报信和有刚的母妹都在楼上的当儿;甚至假定那人混进大门就在这个时候,也未必一定不可能。”
“那么争吵声又怎样解释?难道那凶手先和有刚争执过一会,接着又退出来,等金寿出外后再行进去?”
“不,这不近情理。要是真有人和有刚争吵——你记得他是往往会独个儿发酒疯的——这定是另一个人。总之,我相信争吵和行刺决不是在同一时候,也不是同一个人。”
这一番解释在情势上确有可能,我不由不暗暗点头。不过论情势,除了下毒行刺的以外,又多了一个争吵的人的可能,更复杂了些。同时我也自认我的察看伤势不及他的精细。
霍桑吸了几口烟,又说:“如此,我们可以下一个结论,那行刺的人是这案中的次犯,并不是主犯;主犯却是那下毒的人。”
我应道:“唔,假使如此,你想这行刺的人是个什么样人?”
霍桑颦蹙地说:“这个还待侦查。譬如金寿所说的戴凸晶眼镜的那个近视眼家伙,那个穿西装的高个子,还有仆人阿荣魁林等,都得加以调查。至少我们得听听姚探长的调查结果,再打算进行。”
“那么那个下毒的主犯是谁,你可已有些眉目?”
霍桑摇摇头。“这个人究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