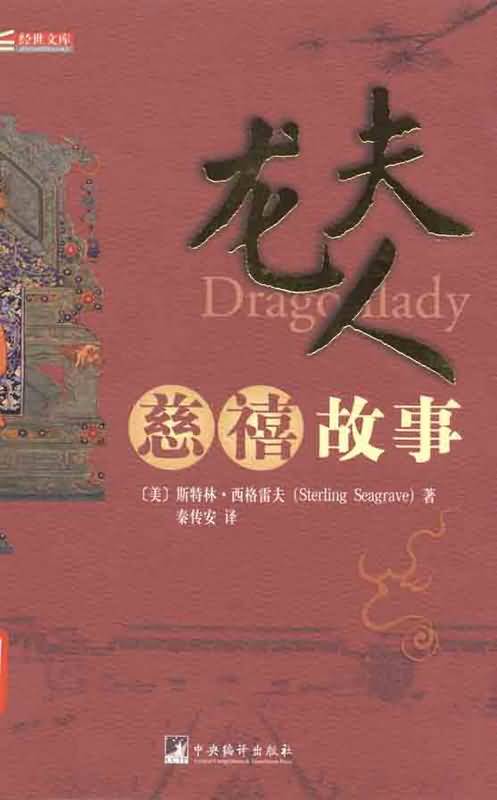慈禧全传之母子君臣-第2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有此了解,他觉得不必过于谦下,所以一进门便往客位上一坐。随即有人来献茶,端茶盘的一个人,捧茶的又是一个人,动作细微而敏捷,让凌兆熊不由得心想:观其仆而知其主,看来这姓杨的,倒不象没有来历的人。
一个念头不曾转完,有人自外高掀门帘,凌兆熊急忙定睛细看,出来的那个人,约莫三十出头,浓眉深目,脸色苍白,戴一顶青缎小帽,身穿宝蓝贡缎的皮袍,上罩一件玄色琵琶襟的坎肩。举止异常沉稳,稳得近乎迟滞了。
“爷!”跟在后面的梁总管,闪出来引导,“请这面坐。”等他旁若无人地坐定,梁总管又说:“那面是本州的地方官凌大老爷。”
姓杨的点点头,抬眼注视,凌兆熊忽然有些发慌,急切间要找句话说,才能掩饰窘态,便不暇思索地问:“贵姓是杨?”
“姓杨。”声音很低。
“台甫是?”
“我叫,”他很慢地回答:“杨国麟。”
经此两句短语的折冲,凌兆熊的心定了些,便即从容说道:“说起来很冒昧,只为人言藉藉,都说真慧寺有位客人,与众不同,所以特意来拜访,请多指教。”
“喔!”杨国麟点点头,“凌大老爷想问点儿什么?”
“足下从那里来?”
“从北边南来。”
“京里?”
“对了!从京里来。”
“足下在那个衙门恭喜?”
杨国麟似乎不懂凌兆熊的话。转脸问道:“什么?”
“是问,爷在那个衙门,”梁殿臣轻轻地又加一句:“内务府。”
“在内务府。”杨国麟照本宣科地说。
这作伪的痕迹就很明显了!岂有个连自己在那个衙门当差都不知道,而需要下人来提示的道理?不过,凌兆熊心想,此人年纪轻,又是汉姓,亮出来的幌子不过内务府,看起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意会到此,更觉得不必太客气,索性话锋紧一紧,且逼出他的真相来,再作道理。
于是他说:“在内务府,不会是堂官吧?”
“不是堂官。”
“是什么呢?”
杨国麟听得这话,似有窘迫不悦之色,答语也就变得带些负气的意味了,“就算司官吧!”
“那么,这趟出京,是不是有差使?”
“对了!有差使。”
“什么差使?”
‘那!“杨国麟扬起了验,”那可不能告诉你。“
由于他的态度突然变得强硬,凌兆熊倒有些顾忌了,换句话问:“足下在内务府管什么?”
“什么都不管,也什么都管。”
这口气好大!凌兆熊又困惑了,“那么,”他只好再换句话问:“足下出京,预备到那里?”
“反正往南走吧!”
“往南一直可以到广东。”
“广东不也是大清朝的疆土吗?”
凌兆熊语塞。宾主之间,有片刻的僵持,而是梁殿臣打破了沉默,“凌大老爷,”他说,“你请回衙门去吧!”
凌兆熊心想,这是下逐客令了!堂堂地方官,在自己管辖的地方,让一个不明来路的人撵了出来,这要传出去,面子不都丢完了?
这一念之间,逼得他不能不强硬了,“不劳你费心!”他冷笑着说,“你名为总管,到底是什么总管?看家的下人可称总管,总管内务府大臣也是总管!这种影射招摇的勾当,在我的地方,我不能不管。你们出京公干,当然带得有公事,拿出来瞧瞧。”
这番话咄咄逼人,着实锋利,但杨梁主仆二人却相视而笑,仿佛遇见一件很滑稽的事似的。这样的表情,大出凌兆熊意外,不由得就愣住了。
“凌大老爷,也不怪你!”梁殿臣说,“公事可是不能给你看。河水不犯井水,我们经过这里,没有要地方办差,也没有人敢在外面招摇。有天厨子在肉案子上闹事,我还抽了他一顿马鞭子。凌大老爷,你眼不见为净,等我们爷一走,事情不就过去了吗?何必苦苦相逼,非搞得大家动真的不可?”
“动真的”是什么?什么是“真的”?凌兆熊不能不考虑,同时也觉得梁殿臣那几句话相当厉害,除非板起脸来打官腔,否则,评理未必评得过他。
事到如今,贵乎见机。凌兆熊拿他的话想了一遍,找到一个题目可以接口,“好吧!”
他说,“那么,你们那一天走呢?”
“这可不一定。”杨国麟又开口了,“只要是大清朝的地方,我那里都可以去,那里都可以住。”
“爷!”梁殿臣低声下气地凑到他面前说,“也别让人家为难,看这样子,再住五六天也就差不多了!”
“好!”杨国麟看着凌兆熊说:“再住五六天。”
“以六天为度。”凌兆熊站起身来,扬着脸说:“我是一番好意。无奈世上好人难做,敬酒不吃,那可没有法子了!”
说罢,头也不回地出了屋子。郭缙生候在外面,两人对看了一眼,都不肯出声,一直离了真慧寺,回到衙门,方始交谈。
“你都听见了?”凌兆熊问。
“是的。”
“那,你看怎么样?”
“很难说。”郭缙生问道:“如说冒充王公贵人,可又为了什么呢?而且地方正印官出场了,要冒充不正该这个时候装腔作势假冒吗?”
“装腔作势”四字提醒了凌兆熊。他一直觉得杨、梁二人有点不大对劲,却说不出什么地方不对劲,现在可明白了!“对了!缙生兄,你这‘装腔作势’四个字,用得太好了!”
凌兆熊突然下了决心,“没有错!我看是冒充。非断然处置不可。”
这一回答,使得郭缙生大吃一惊,他发觉凌兆熊的看法跟他竟是两极端。若说断然处置,事情可能会搞得不可收拾。
想了想,不便直接拦阻,只好间接表示异议。
“堂翁!”他问,“若说冒充,是冒充什么?冒充内务府司官?这似乎犯不上吧?”
“谁知道他犯得上,犯不上?我们看一个内务府司官,没有什么了不起,在商人眼里,尤其是跟内务府有大买卖往来的商人,那还得了。”
“我看不象,不象是冒充内务府司官。”
“莫非真的如孙老夫子所说的,冒充皇上?那是决不会有的事。”凌兆熊又说,“退一万步而言,就算是真的皇上,我已经登门拜访,客客气气地请教过了,谁让他们真人不露相?不知者不罪,我也没有什么罪名好担的!这,当然是说笑话,决不会有的事。缙生兄,事不宜迟,明天就抓。有什么责任,我一个人挑。”
“堂翁此言差矣!祸福相共。既然堂翁主意拿定了,我遵办就是。”
于是第二天派出差役和亲兵,由郭缙生亲自率领,到得真慧寺,驱散了闲人,将杨国麟所住的那个院子,团团包围。然后,郭缙生派人去通知梁殿臣,说是请到州官衙门叙话。杨家上上下下,都很镇静,一言不发地都聚集在院子里。只梁殿臣问了一句:“是上绑呢?还是上手铐?”
护送到知州衙门,格外优待,不下监狱而软禁在后花园的空屋中。凌兆熊少不得还要问一问,为了缜密起见,特意将杨国麟带到签押房,自不必下跪,但也没有座位,是让他站着说话。
“杨国麟,你到底是什么人?”
“天下一人!”
此言一出,满屋皆惊。靠里面的门帘一掀,孙一振大踏步走了出来,自作主张地吩咐值签押房的听差:“叫人来!把他好好带回去。”
“老夫子……。”
“啊!啊!”孙一振急忙使个眼色,拦住了凌兆熊。等带走杨国麟,屋子里只剩下凌兆熊与郭缙生两个人时,他方始低声说道:“东翁,不能问了!‘天下一人’什么人?不是孤家寡人的皇上吗?不论是真是假,倘或市面上有这么一句流言:凌大老爷审皇帝!东翁倒想想看,这句话吃得消不?”
“是!是!”凌兆熊惊出一身冷汗,“倘有这样一句流言,可以惹来杀身之祸。老夫子,擒虎容易纵虎难,我这件事做得鲁莽了。”
“这也不去说它了。”郭缙生也有些不安,“如今只请教老夫子,计将安出?”
“没有别的法子,只有连夜往上报。”
呈报的公事,颇难措词,因为黄州知府魁麟原来的指示是,先查报真相,再作处理。如今真相未明,先行逮捕,不符指示,得有一个说法。彼此研究下来,只有一个说法最妥当,说杨国麟、梁殿臣主仆,行踪诡秘,颇为招摇,以致蕲州流言极盛,深恐不逞之徒,借故生事,治安堪虞,所以将杨国麟等人暂行收管。最后又说:此人语言狂悖,自谓“天下一人”。知州官卑职小,不敢深问,唯有谨慎监护,静候发落。
“公事是可以过得去了。”孙一振说,“不过这不是动笔头的事,最好请东翁再辛苦一趟。”
“好!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凌兆熊无可奈何地说:“我就再走一趟黄冈。”
※ ※ ※“老哥,”魁麟面无表情地,“你搅了个马蜂窝,怕连我都要焦头烂额。”
“府尊这话,让兆熊无地自容。”凌兆熊答说,“不过,州里绝没有贻祸上台的意思。”
“我知道,我不是怪你,只是就事论事。如今没有别的法子,只有咱们俩一起进省,看上头怎么说法?”
于是魁麟与凌兆熊连夜动身,赶到武昌,先见藩司善联。听完报告,大为惊诧,“有这样的事?”他说,“光天化日之下,冒充皇上,不发疯了吗?”
“是!”魁麟躬身问道:“大人说是冒充,我们是不是就禀承大人的意思,拿杨国麟当冒充的办?”
“不!不!不!”善联急忙摇手,“我可没有这么说。冒充不冒充,要认明了才能下断语。”
魁麟是故意“将”他一“军”。因为彼此旗人,所知较深,善联为人圆滑,不大肯替属下担责任,魁麟深恐他觉得事情棘手,拖延不决,未免受累。这样一逼,善联就不能不有句实实在在的话交代。
“说实话,这件案子出在别省还好办,出在湖北不好办。其中的道理,我也不必细说。
如今先请两位老哥回公馆,我立刻上院,先跟于中丞去商量,看是如何说法?回头再请两位老哥过来面谈。“
“是!”魁麟试探着问:“这件事恐怕还要请示香帅吧?”
“我看,不能不告诉他。”善联又说,“香帅的‘起居无节,号令不时’是天下闻名的,如果非请示他不可,那就要看两位的运气了!也许今天晚上就有结果,也许三天五天见不着面。”
“大人,”魁麟立即要求,“这件案子,反正不是州里能够了结的!人犯迟早要解省,晚解不如早解,我看请兆熊兄马上赶回去带人来。如何?”
善联沉吟了一下答说:“这样也好!香帅的性子,大家知道的,一声要提人,马上就要,不如早早伺候为妙。不过,案涉刑名,得问问老瞿的意思。明天一早听信吧!”
等魁麟跟凌兆熊一走,善联随即更衣传轿“上院”。督抚衙门简称为“院”,湖北督抚同城,但在统辖上,藩司为巡抚的直属部下,所以善联的“上院”,自然是上巡抚衙门。
湖北巡抚本来是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戊戌政变那年,改革官制,湖北巡抚一缺裁撤,谭继洵不必等他儿子身罹大辟,便已丢官。及至太后训政,一切复旧,湖北复设巡抚,谭继洵当然不会复任,朝命由安徽藩司于荫霖升任。
于荫霖是极少数生长在关外,而不隶旗籍,又做大官的汉人之一。他是吉林伯都厅人,翰林出身。那时的翰林院掌院是守旧派的领袖大学士倭仁,于荫霖相从问学,颇得赏识。不过,于荫霖倒不是启秀那样的腐儒,更不是徐桐那种神既全离,貌亦不合的假道学。从光绪八年外放湖北荆宜施道以后,久任外官,凡所施为,孜孜以为民兴利除弊,振兴文教为急务,略有康熙朝理学名臣汤斌、陆陇其的意味。
于荫霖的擢任方面,原出于张之洞的保荐。张之洞跟他在广东便共过事,相知有素,但在湖北却不大投机,因为张之洞赞成行新政。当戊戌政变之际,亏得见机得早,做了一篇文章,题名《劝学篇》,暗斥康有为的学说为“邪说暴行,横流天下”,新旧之间,虽持调停的态度,但特拈“知本”一义,以为“在海外不忘国,见异俗不忘亲,多智巧不忘圣”,这话很配慈禧太后的胃口,亦不得罪顽固守旧王公大臣,因而得在皇帝被幽、帝师被逐、朝士被斩的这场政海大波澜中,得免卷入漩涡。
祸虽得免,张之洞对新政仍未忘情。而于荫霖颇不以为然,因而又落入历来“督抚同城”势不可免的故辙,明争暗斗,格格不入。只是于荫霖对整顿税收,勤理民事,颇有绩效,再则顾念旧时的情谊,所以张之洞还能容忍得下,保持一个虽有裂痕,勉可弥补的局面。
当然,于荫霖亦能守住分际,遇到需要让总督知道或者请示的事情,绝不会擅专,所以一听善联告知其事,随即表示:“这非得先告诉香帅不可!咱们一起上南城。”
武昌城内以一道蛇山,分隔南北,所谓“南城”,是指在山南的总督衙门。时将入暮,坐轿翻山,天黑才到,却扑了个空,张之洞在蛇山的“抱冰堂”张灯夜宴,与幕府中的名士在分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