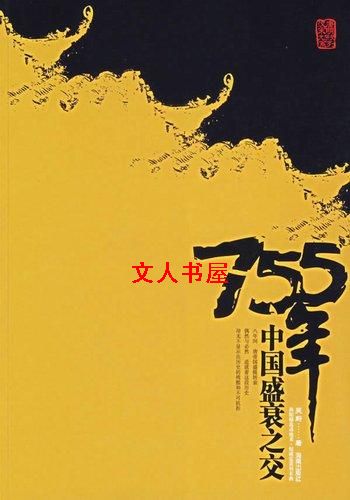清末那几年:一幕未散场的潜伏传奇-第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氏道:“这怨得我吗?”一看她满脸的幽怨,我也不敢再与她争竞,依主宾端坐下来,宽慰她道:“怨我怨我,你说却如何处?这样吧,我罚酒两杯,总行了吧?”祝氏道:“你想得倒惬意。”她径直走到当院,从水缸里舀一瓢井水递与我,我才喝了一口,就把牙扎得生疼。
祝氏笑了,笑了就好,我就怕她生气着恼。祝氏道:“你若能跳出七情六欲的关口,便是一个真君子了。”我说:“我假使做了坐怀不乱的柳下惠、秉烛达旦的关云长,也就不再是人,而是神,叫人供起了。”祝氏想了想说:“即便不是神,也该削去六根清净,披一领袈裟出家去了。”我合掌笑道:“还是你聪明。”祝氏叹息一声:“知你是个身负大任的人,不娶我,也是情有可原,我不恼。我恼的是至今连一句实话也从你嘴里得不到,难道说我就这般靠不住?”我说:“我能告诉你的就是,你眼里的我,绝非是真正的我,你只知我不是个眠花宿柳、惹草招风的风流子弟,就足够了。”祝氏见我仍是遮三掩四,眼圈不禁红了。我哄她道:“我家原也是定兴呼奴使婢、骡马成群的殷实户,出来任这个小小的驿丞,必有缘由。到时候,一准给你个切实。”祝氏道:“只怕我等不到那一天了。”我执起她的小手,到文案上写了几个字,拿给她看:对你不起,林白叩首。祝氏的泪刷地落下:“就会糊弄人。”我又使了些功夫,发誓将来必补偿她,才将她哄转来;一会儿嗔,一会儿骂,一会儿又笑,祝氏总算脸色舒坦下来。她说:“你烫烫脚睡吧,看累着。”我说:“明日我去澡堂泡一泡。”转天,我叫上李耳一起去新开的一家浴堂,脱了衣裤放进衣箱,李耳说:“驿丞,我来给你搓搓背。”我松开辫子趴下:“那就烦劳你了。”浴堂里雾气腾腾,谁都看不清谁的脸。我突然说:“不管发生什么,我都劝你别忍心撇下我们几个兄弟。”李耳动一动嘴唇,没说出什么来。泡了澡,在外间屋躺下,唤伙计摆出一桌茶果和青萝卜来,修脚的师傅也过来伺候。李耳说:“我决定了,留下来与你们就伴。”我说:“这样最好,遇为难事,倘可用力,定当相救。”李耳闻之,不禁动容:“往后驿丞有用我的地方,只管吩咐。”我心中大喜,他也是江湖上的一大能人,若能与我联手,也不负他平生大志。不过,现在与他多说,尚为时过早。巳时到了,我拉了李耳同去酒楼一坐。
刚刚落座,跑堂的就过来说张目跟王品在楼上,我二人又连忙起身寻他们去。李耳悄悄对我说道:“暂时还是不要跟他们说得太多为好。”我闻言,笑了一笑,晓得他是不愿我过早地暴露他的身份,便爽快地允诺了。李耳说:“驿丞不必多疑,我当年曾起誓法不传六耳,实不想违约。”我自是理解他,只是一切皆有定数,光绪的定数已到。阎王注定三更死,谁敢留人到五更?不过,我不想戳他的肺管子,没再言语。张目跟王品见我们来,又是一番谦让,银鱼、醉虾、腌蟹、鱼丸四样小菜都上来了,我们的座次还没排好呢。通州城傍着运河,最方便的就是不愁吃鱼吃虾。几个推杯换盏,谈及北京之变业已平定,文良老爷失踪案也撂在了一边,该驿站轻松两天了。李耳虽也强颜欢笑,不觉形诸颜色,好在都没留意。我推脱不过,不得不跟王品划了几拳,都输了。王品就说我“情场得意,赌场失意”,我也不驳他,随便他说。饮得正尽兴,忽听门外一阵吵闹,酒楼里的人都拥出去看。停了一会儿,问伙计何事喧哗,伙计说:“是一伙子叫义和拳的在门口打把势。”我说:“赏几个大钱,叫他们走。”伙计说:“他们不要钱,都是身怀绝技、刀枪不入的汉子,你给他两大包子砒霜吃下去,也毒不死他。”
张目说:
恩主说,早年清兵个个都是能征惯战的。入关时,手握双刀,转动如风,直把刀砍得卷了刃,换刀接着再拼杀;而今这帮爷,提笼架鸟,寻欢作乐,睡个女人都得靠药石撑着才能应付得来。难怪赞襄政务王大臣肃顺说:满人糊涂不通,不能为国家出力,唯知要钱耳。老妖婆和光绪帝更是风雨飘摇,只要再推他一把,兴许他们就跌倒爬不起来了。不光我一个人这么看,林驿丞他们几个心里也是明镜一般,只是三缄其口罢了。从酒楼回来,我没回自己屋,而是直接去找三娘,敲她的门。
绣户微启,湘帘半卷,三娘露出半张脸来,问我何事;我托着食盒,把特意打酒楼给她捎来的酒菜,径自向窗内送去。三娘说:“劳你还惦记。”我赶紧说:“是驿丞的意思。”帘内哼了一声,伸出纤细小手儿,把食盒接进去,呱嗒撂了窗。我求她让我进屋,她却只说一句“醉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便不再睬我。
半月余,三娘见我都是一脸冰霜,上前搭讪,也没个好颜色。这天,西头谯楼上已鼓打二更了,忽有人敲门,开开,闪身进来一个女子,细一瞅,却是三娘。本想戏言挑之,又怕她厉声相拒。三娘不慌不忙侧身坐下,问道:“这一程子听说义和拳的事了吗?”我说:“听倒是听了,不过都是些无稽之谈,神乎其神,不足采信。”三娘道:“你尽管说来我听听。”我知道她一个黄花女,不便上街招摇,便告诉她:“都说义和拳是钢筋铁骨。刀砍在脖上,刀卷了;斧剁在腰间,斧断了;人则好好的,不伤一根毫毛。”三娘又问:“还有呢?”我说:“还有更神的,说是义和拳念了咒语后,日光之下行走,地上居然不见影迹,从来都是阴鬼无影;有人不信,贴上去一张天师的法符,结果一点无用。”三娘道:“不管怎样,义和拳愈闹愈凶,还是要留意一些为好。”我说:“他们更像是乌合之众,横竖看不出有大出息来。”三娘道:“也很难说,总归马虎不得。”一头说话,一头往门口走,没来得及拦她,她已出去了。我闷闷昏昏地回到房里,神情呆滞,挑帘望望窗外,浮云似烟非烟,疏星更似萤火虫儿一样闪着亮,益发觉得三娘的神秘,真怀疑刚刚是做了一场梦,幸而一缕淡香还留在屋内。
过几日,林驿丞做寿,我才又遇见三娘。林驿丞特别邀她,给她单摆一张桌。林驿丞说起他所见过的义和拳,有骑鹤的,有乘兽的,有踏风火轮的,持刀执戟,装扮得天兵天将一般。众人都说那是些铜铸的金刚、铁打的罗汉,我倒以为他们更仿佛是赶庙会的卖艺人。林驿丞怕冷落了三娘,问她义和拳这伙子能否成就大事,三娘低头答道:“这是你们男人家的事,如何问我?”三娘的女儿情态,迷死个人,我就似三魂尽数被她摄去了一般。只是席间三娘看都不看我一眼,倍觉冷落。她只敬过寿星佬一杯,再没什么言语;谁来论说天下事,全不在她心上,光以饮酒吃菜为是。几次想撩拨她两句,又唯恐同僚取笑,心中甚是不乐,也勉强着说些个笑话凑趣,不禁好生寂寥。
我这人有个毛病,心中不悦,要么一连几夜不睡,要么就是几天都不醒,谁都奈何不了我。偏就在我昏睡的这几天里,出了大事。义和拳在北京、天津和山东闹将起来,烧了教堂,打了洋和尚。我一醒,便赶去四下打听这事的头尾。人说,老妖婆不仅不管,还惦记借义和拳的手教训教训老毛子。这么一来,义和拳简直如虎添翼,折腾得更加欢实。一日,一群人甚至闯进驿馆来,林驿丞急忙出去安抚:“各位拳爷,小官叩见。”拳民喝道:“大胆狗官,知道我们要来,敢不来远迎。”林驿丞说:“拳爷息怒,小官闻听几位爷要来,赶紧备上几坛子上佳的醇酒,犒劳各位。”好歹算是将他们打发了。
事后,林驿丞心疼得什么似的,说那酒都是在地窖藏了十数年之久的佳酿,可惜了。李耳说:“有什么可惜,县衙门还给拳民放了饷银呢。”林驿丞嘱咐我们:“惹不起,咱们躲,这几日一概不准擅动。”又吩咐门官,大门紧闭,用心把守。
这中间,兵部用火牌行文各处,除关隘码头外,不得过多干涉义和拳。潞河驿也接到了指令。
通州城里的洋教士和教民跑了大半,余下的也躲了,剩不下几个。我们天天端坐驿馆,大眼瞪小眼,好似泥塑木雕。
林驿丞说:“我们正好可以坐山观虎斗。”
只有王品张罗着弄些参汤,端出去叫拳民们饮用;我们好奇心发,都冷眼旁观,没一个人帮衬。三娘说:“义和拳一起事,那王品倒是吹皱一池春水。”我没吱声,但心下已明白了许多,知道了他王品的真实背景,估计林驿丞他们也早看出了端倪,都不是瞎子。只要王品有意举旗起事,必遭围攻,想他王品到那时肯定是孤掌难鸣,无所作为,所以我也不怎么惧他。
我虽日日安分地待在驿馆,从不做钻洞越墙的勾当,但是偶尔攀到树上偷偷前去相看一下的事情还是有的。拨开树枝子,向街上瞧,只见替天行道的幌子满处都是,还见捉住的洋人绑着游街,往他脸上啐唾沫。后背忽然挨了一石子,俯身一瞅,原来是三娘,招呼我下去。我出溜到树下,问她有何指教,三娘翻翻眼皮道:“这群义和拳已经做了老妖婆的狗,有什么看头。”我说:“看也是看个热闹。”
其实,想那些个洋人曾在大清的地面上横着膀子走道,而今却叫义和拳折腾得七荤八素,也怪解恨的。三娘却说:“要看热闹也该大大方方地到街上去看,如这样做贼的架势,像个什么样子!”我已经叫这个小妮子申饬惯了,也不过意,只狡辩一句:“林驿丞不让随便出去。”三娘道:“林驿丞叫你吃屎你也吃?拿着鸡毛当令箭!”正说着,有人搭话道:“谁在背后嚼我的舌头根子呢?”回头一瞧,竟是林驿丞。三娘登时脸上红一阵儿白一阵儿,适才对我的凛然正气早抛到爪哇国去了,干张嘴说不出话来。林驿丞说:“义和拳这么闹,洋人能善罢甘休吗?一准要报复,到那时候非惊天动地乱一场不可。
我等都是一介草民,经不住大阵仗,还是做缩头乌龟的好。”我跟三娘都不服气他,又都懒得申辩。不过,林驿丞并没都说错,没多久,几千的洋鬼子联军就端着洋枪找义和拳算账来了。本来是打算从天津坐火车奔北京的,结果,铁道叫拳民拿撬棍给撬了,洋鬼子只得在杨村下车,走到廊坊跟义和拳干上了,末了,硬是没斗过义和拳,只好撤了。王品奔走相告:“拳民胜了,把老毛子打败了。”又拉上我跟李耳便装上街瞧稀罕,到处都是扎红头巾、着红兜肚的拳民,男儿汉子无不拜在张天师的供像跟前;入了坛,连寺院的和尚、江湖的术士和少年寡妇也来凑趣儿。但是,很快发生的两件事,叫王品不那么有兴致了——头一件事是当铺的严掌柜总在耳朵上夹一只洋铅笔,义和拳不光把他的铺子点了,还把一家老小都宰了,连怀抱的刚满月的孩子都没放过;另一件事是一个在药房代客煎药的闺女,煎药时用洋火生火,叫义和拳遇见了,非说她是洋人的奸细,几个人把她给奸了,活活折磨致死。王品实在看不下去了,变得忧忧郁郁,从此对义和拳不再抱期待。叫他听戏,他也不去,任什么都提不起神来。叫他起上一个号,他说烦;叫他刻上一部稿,他说累;叫他坐上一乘轿,他说闷;叫他讨上一房小,他又说俗。总之,怎么哄都哄不好了。李耳跟他摆棋,让他开心,他也三心二意,输赢全不在意,只是痴痴地感慨道:“义和拳这般不良不莠,必然是一事无成。”李耳说:“莫想没用的,下棋下棋。”王品说:“这么大的事怎么能不想?”我们也帮不了他,只觉得他可怜,自寻些烦恼。
这些日子,三娘也没闲着,一双金莲紧行慢赶,镇日里在街上游逛,晚晌回来又总掉着脸。她所到之处,拳民都颂扬老佛爷的德政,嚷嚷着要扶清灭洋。这让她很是气不忿儿,恨义和拳瞎了眼。我劝她慎言,她还骂我胆小鬼,我笑她似这般坏的脾气,甭说出阁,就是许字怕也难得很。三娘蛾眉倒竖:“谁说我要出阁来?”见她动容变色,未免可笑,便故意逗她:“你不出阁,就不会有儿子;没儿子,就有不了孙子;没孙子,哪里再有重孙、灰孙、滴里耷拉孙?”没想到三娘突然说了一句:“真想把王品杀了。”我不禁吓了一跳:“为什么?”三娘说:“你没看出他是老妖婆的人来吗?”我劝她:“管他呢,碍我们什么了?”我真想给她开一帖补中益气的方子,思虑伤脾,不补,会成疾的。
我说:“今儿个你看出王品是老妖婆的人要杀,明天又看出谁是光绪帝的人,该怎么办?后日你再看出谁是哪个旗主王爷的眼线,你杀是不杀?杀来杀去,潞河驿还办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