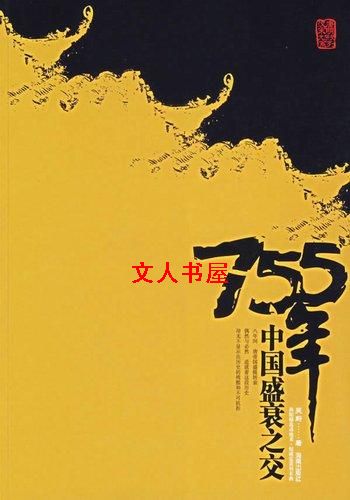清末那几年:一幕未散场的潜伏传奇-第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作者:雪屏
【】
写在前面
说来有趣——前两年,克凡和龙一来京开会,晚上来我家聊天,说起龙一创作的《潜伏》来。当时,以这部作品改编的电视剧正在播放,颇为轰动,人尽皆知。我跟龙一开玩笑地说,回头,我也写一部卧底的故事,你写一个,我干脆写一堆。只是说过,也就忘脖子后面去了。前不久,偶尔看到清朝画家江萱画的一幅长卷《潞河督运图》,气势恢弘不亚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立时有了创作的冲动。于是,就有了这部作品。
我尝试着用“三言”“二拍”式的语言,来叙述一个虚构的故事,当中刻画了形形色色有趣的人和事,还有许多我对逝去的那个时代的解读。有些人物,直接就是来自当今现实生活中,不过是加以敷衍、改头换面了而已。这部书,跟我以往的创作风格迥然不同,过去我没这么写过,估计将来也不会再这么写了。完成之后,我还是发现有许多稚嫩的地方,因为身体欠佳,已无力再精益求精了,但愿不会让读者讨嫌就好。
不知不觉,我已虚度了半生,我给自己总结了一下,半生大致经历无非是:上学,上班,上医院。这几年,更是足不出户。一日,读郑逸梅先生的《艺林散叶》,其中提到一件趣事,郑逸梅与徐碧波为邻,两家仅仅相距一百余步,但都腿懒,有事辄付邮简以传达。我很欣慰,暗暗引为知己。
因为卧床的时间久了,四肢就闲着,但大脑则显得忙碌。相对静止的生活,反而令我更愿意从事创造性劳动,尽可能地使自己创作风格多样化,不墨守陈规。这部作品就不是传统的线性结构,而是大量采用内心独白,便于从心理层次上来反映人物的内在性格,这样多少有点挑战读者的阅读习惯。类似的探索效果如何,还有待读者的检验。
在此,借编辑给我的这个机会,我还要多说一句:在这个世界上,真正在意我创作的其实只有我母亲,她不识字,但是她珍惜我写的每一个字,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母亲是我创作的原动力之一。我创作其实并非是艺术创作那么简单,更大程度上,是我的精神寄托。感谢曾帮助过我的朋友们,比如克凡、仲宪、龙一、老谭、九涛、成国和徐献。另外,在这本书出版过程中,责任编辑认真负责,并提出了一些不错的建议,令我感动。
雪屏
2011年11月26日于北京
人物表
文良老爷:男。三十上下。慈禧太后的差使。
林驿丞:男。三十来岁。名白。精明、风流、体格好。潞河驿站小官。张目:男。二十多岁。绰号“千里眼”。
李耳:男。二十多岁。绰号“顺风耳”。在驿站中掌管厨下活计。王品:男。二十多岁。绰号“铁嘴”。在驿站中负责槽上活计。三娘:女。二十多岁。实名宋石榴。一身轻功,日行千里。祝氏:女。二十多岁。一个年轻寡妇,与林驿丞生情。房三爷:男。中年。花铺老板。
蒲先生:男。中年。香铺老板。
黄老板:男。中年。书铺老板。
静怡师父:女。二十多岁。
九儿:女。十五六岁。李耳媳妇。
金铃:女。二十来岁。王品媳妇。
景儿:女。八九岁。林驿丞收养的女儿。
伴儿:男。十五六岁。孤儿。茶楼一伙计。
厨子:男。烧得一手好菜,其实另有身份。
一
“文良老爷一行在潞河驿门口下马的时候,已经是钟鸣漏尽时了。张目那小子赶紧将他们迎进后院驿馆,偷眼瞅瞅,这位文良老爷气派不凡,就猜他即便不是西佛爷身边的王公贵族,也得是东暖阁常来常往的亲枝近派。”“文良老爷想不到这么一个小小的馆驿,内院倒是另一番天地,不禁夸了一句,里外端详起来。”
“张目赶紧说,您老见笑了,您老见笑了。”
“我听说张目这小子让文良老爷歇夜,被文良老爷拒绝了。说公事当紧,今晚就不歇了;不拘什么取上些酒菜来,随便垫补垫补打个尖就走,紧着要赶路。张目便招呼厨下备饭,上上下下一通忙,工夫不大,荤的素的就摆满了一桌,然后拱手道:您老几位请,夜深露冷,非喝两杯不可,防着感冒风寒。”
“张目这小子眼好,文良老爷一行饮酒吃菜时,张目盯着文良老爷的左右长随,俱是紫面长须大汉,威风得紧。不待说,此次盛京之行非同小可,他几人自然规矩守礼,万一出个一差二错,文良老爷必替朝廷行家法,不徇私情。所以文良老爷说什么,几个紫面长须大汉都点头称是,不敢顶撞一句,只顾憨吃。顷刻,酒便告干了一壶,厨下的李耳又添上酒来,站在一边伺候。趁这当儿张目去马房看看马喂得如何,文良老爷推开碗筷一旁剔牙时,张目早已料理好鞍屉,将马拴在外院桩上,听候着文良老爷的驱使……”
“我还听说,李耳在桌旁小心伺候着,听这几位说:文良老爷这一番确实是急务在身,起身前长随们就要将官衔旗扯起,叫文良老爷拦了,言明对外一概声称去省亲。眼下兵荒马乱,西佛爷的密函要是被途中劫了去,非掉脑袋不可。临行,西佛爷也曾说过,此一去盛京,断不可惊动地方,更不兴怠慢,几日内速来回复。其实,文良老爷知道首先不能告知的是皇上那头,这也正是他为何掌灯时分方才出京的原因之所在。他离京之际,西佛爷刚传了一个小班,问他是不是听了戏再走,他哪敢拖延,行了礼就匆匆退了出来。文良老爷不比其他同僚个个四世公卿、一门科第,而是从七品知县起家,吃粗茶淡饭长大。因一次押粮进京,遇了响马,他舍命维护,得了西佛爷垂青,加赏优恤,才有了金玉锦绣,怎可不拼了一死,报效西佛爷知遇之恩呢?那些长随显见俱都是文良老爷的心腹人儿,文良老爷与他们道出利害,命他们一路之上非但不可显形,亦且不可露影,小心行事才是,句句是肺腑之言。长随们知道不是闹着玩的,一惊非小,立马都郑重起来,一颗心提到了嗓子眼儿,连酒都不敢喝了。”
“不像话的是,文良老爷一下马,张目就差人去知会驿丞,结果驿丞迟迟未到,不知他又到哪里风流快活去了。这位姓林的驿丞,打头年断弦后,就迷上了脂粉,尤其是那些残花败柳的小寡妇,姿色端庄、花容月貌的黄花闺女倒懒得招惹。李耳自己又拙嘴笨舌,生怕怠慢了文良老爷,让文良老爷挑了眼就不好了。幸好这时候王品拍马及时赶到,解了李耳的燃眉之急。王品天生有一张好嘴,这是咱们都知道的,饶是你钢炼铁肠,经他上下嘴皮子一碰,也能让你化为绕指柔了,赛似苏秦、张仪。他一进垂花门就说:怪道是今夜星明月朗,敢情有贵客登门啊。叩见过了,文良老爷赏了他几两纹银,连同张目、李耳也一便赏了,借他吉言了。王品望望天又说:俗称,南斗掌生,北斗掌死,您老是南北斗,我们小民的生死大权都在您手心里握着了。文良老爷笑了说:贫嘴。时候不早,我们也该挪挪窝了。起身就走了。”
“驿站本来就是个赔笑脸的差事,跟你我不同,张目、李耳和王品三人鞍前马后地忙碌,而林驿丞却猫在暗地里跟浪蹄子脸偎脸地调笑去,想想,他仨就气不忿。文良老爷走出去横有二十里地了,林驿丞才来。进门先泡茶打坐,倒跟县太爷坐早衙放告一般气派,又吩咐三娘拿来一壶酒、两样菜,小酌一番之后才问:这么晚了,你们怎还不歇着?王品便将文良老爷来驿馆打尖的事讲了一遍。驿丞跳起来:为何早不说与我听,现在老爷人呢?王品道:已走多时了。三娘过来问驿丞还续酒不续,驿丞一拂袖道:哪里还有心思饮酒,算了。把个三娘唬得浑身一激灵。这个三娘也算地方上头一名伶俐人,烧出菜来,比京城馆子的色香味还地道,还会一手好针线。张目一直中意于她,欲求之,三娘却推三阻四不从,这一笔风花雪月账只好悬在那里。眼下,他见林驿丞无端迁怒于三娘,心里不平,就说:我遣人四处寻你,大人常去打牌掷骰、猜枚押宝的地方通通寻遍了,也寻你不到。林驿丞也是心虚,就不再啰唣。张目怕三娘柔弱,经不起夜寒,便催她回房歇息;三娘低头走了。张目瞅着她的背影觉得有万种妖娆,竟看痴了;林驿丞咳嗽一声,他才收回魂魄。天色这时候确实已晚,便流水似的回房安歇。”
“转天,本以为文良老爷那一页已经掀过去了,新一天重打锣鼓另开张,孰想,不到日上三竿,一群官兵就把潞河驿围了,为首的瞪眼质问林驿丞:文良老爷可曾夜里宿在此处?林驿丞赶紧说:连夜上路走了。那为首的顿足道:你怎么不将他留住!这话说得好没道理,但是,对方是五品京官,而他只是一介掌管草料银的未入流的小小驿丞,惹也惹他不起,只好忍气吞声。”“官兵不信林驿丞,馆驿上下分头去搜查。”
“结果查出什么来没有?”
“自然是狗咬尿脬一场空,屁也没查出一个。”
“为首的那位官兵仍旧不死心,一再追问:你知道文良老爷从哪条道走下去的吗?林驿丞用手指了指:沿东边这条官道,快马追下去,一天便可赶上。为首的官兵一声唿哨:上马,速速跟我去追。一干人马纵马追下去,须臾便没了影子。”
“林驿丞长舒一口气——潞河驿地处京畿左近,也算得上是个咽喉要地了,上传下达,不可谓不当紧;但是驿馆终究是个迎来送往的行当,随便哪个爷,都可以在这呼风唤雨。眼里夹不住沙子的人断然应不了这个差,好在他一颗心早就灰透了,叼个旱烟袋,剜上一锅子关东叶子,混上一天是一天。“不过,驿馆屋子小,院子大,长廊曲槛勾连,绿萼红香围绕,却有一份情致,最宜养老;街上店铺林立,繁华一片。林驿丞把衣裳换了,踱出驿馆,信步逛去,顺便喝一碗韭菜粥,也不嫌有什么寂寞。”
“他想如往日一样喝了粥,就去找百长丢下的一个小寡妇祝氏。那祝氏眉弯两月,花容蛮腰,还有那双不及三寸的金莲,简直迷死人不偿命。听说,祝氏赶庙时叫人将一双绣花鞋偷了去,唯恐丧了廉耻,丢了名节,当街哭起来;林驿丞见她有几分姿色,便动了怜香惜玉的心,叫祝氏坐他的轿回府,而他自己徒步。一来二去,两人便相熟起来。谁知,那祝氏是个许看不许吃的主儿,亲得,抱得,睡不得,急得林驿丞只得朝夕在她左右转悠。他以为做得神秘,一切都不为人知;殊不知,早有人把一切看在眼里。自他潞河上任以来,跟梢的就不曾断过,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被统统记录在册。至于何人所派,却无人知晓。幸好林驿丞只在寡妇床头做文章,并无异心,更不与朝廷为难,所以位子倒还坐得稳当。要说一个驿丞,也不过管着二百来人、百十匹马、几头骆驼,何必如此兴干动戈?只因为潞河驿是距离京城最近的一个驿馆,是进京出京的大小官员必经之处,就是宗室皇亲也常常在此处落脚,马虎不得。他走到哪里总有眼线跟到哪里。在粥铺,林驿丞脱掉官衣,跑堂的端来洗脸水;他拧了一把手巾,擦了擦,又把口漱了,才坐下喝粥。尾随于他的人,也不即不离地装作喝粥。喝了粥,林驿丞会账起身,那人也跟出粥铺……”
“林驿丞道上又拎上一瓶酒,惦记着与祝氏喝个合卺杯,推杯换盏后,谅她一个小女子不胜酒力,乖乖地让他林某人慢橹轻摇,捉她个醉鱼。后面那人见他进了寡妇门,便离开了。林驿丞怕是怎么想都想不透,老佛爷刚打发文良老爷出京,怎会又派官兵追他?祝氏见林驿丞来,沉着脸告诉他,晚间做了一梦,蹊跷得很,让他解上一解;林驿丞让她把梦说来听听。她说她梦见她死鬼丈夫从坟里出来跟她打招呼,林驿丞掐指算算,说周公解梦中云:梦见冢墓上开花是大吉,梦见开棺与死者言谈则主凶。祝氏一听吓坏了,赶紧轰他出去,扣上门闩烧香磕头,一天不敢出门。林驿丞正反扇了自己俩嘴巴,怪自己多嘴,可怜一个驿丞孤零零街头流落。路过勾栏曲院,花朵般的女子冲他招手,个个是破瓜年纪,娇得很;他正有火无处发泄,破口便骂:都他娘滚一边子去!勾栏女子也不是好惹的,撒起泼来厉害着呢,于是,两边当街对骂起来……”
“他们馆驿中人各有各的去处,比如李耳跟王品吧,俩人志趣相投,拜了把子,最常去的就是戏园子。叫一壶好茶,凳子上铺上狼皮褥子,听天津卫来的班子唱小戏;又都喜欢叫‘满场飞’的那个粉头,专捧她的场。‘满场飞’不光唱得好,扮相也标致,散了戏,还要递上拜帖,到后台跟‘满场飞’寒暄上几句。”
“他们两人一个掌着厨下,一个管着槽上,手下都引领着十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