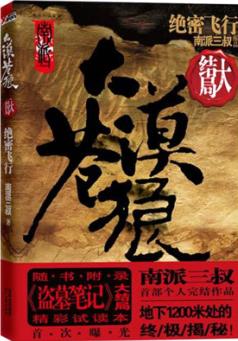黄金的秘密-第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说:“我已经告诉你我是什么人,也告诉你我要干什么,现在看你要怎么样办了。”
“10秒钟之后,”他说:“我马上要把你从这里抛出去,抛到你会从地上弹起来。”他自椅中站起来,把门闩打开,把门打开到底,用大拇指一指,他说:“滚吧!”
我站起来,我在选一个合宜位置,准备他来攻击时我可以转身,给他一个过肩摔。
他走向我;很随便,无所谓的样子。
我等候他出右手来攻击我。
想像中和桥田一起演练的那一招并没有出现。他的一招来自侧面。但是抓住的是我的外套领子。他的另一只手抓住我裤子后口袋。我想要支撑自己,但是好像在推一辆火车头,我被摔出去通过门框的时候,门框倏忽地经过我身旁。我双手向前,才不致让我的头撞到走道对面的墙上,我一把抓住了电梯边上把寄出信件直送楼下的钢管。他把我抓住钢管的手分开,把我一脚踢倒在电梯前空地上。
我现在懂得足球员罚12码时,皮球有什么感觉。球员撞过来,一半质量和速度的平方乘积变为动能,动能自一脚传到了球了。球的感觉就成了我的感觉。
我听到他走回去,把门关上又闩上。我摇摇曳曳走向走道,转一个弯,想找个楼梯下去,发现走错了方向。我就走回来。
离开转弯处尚有20尺,我听到砰!砰!砰!三下枪声。2 秒钟后我听到走道上跑步的脚步声,向相反方向走去。
我跑步又向右转。四一九号房是开着的。长方形灯光亮影自房里照出。我习惯的看了一下手表—— 11点16分。电梯仆役一定已下班了。电梯现在是全自动的。
我按下电梯的纽,听到电梯起动,我路起足尖来到419房。
金见田的尸体,在进浴室的门口缩成一团。他的头曲在两个肩膀中,他的上肢扭成一个怪异的角度。一只膝盖在浴室里,左上肢压在通421房间的门上。
我把手指升向他右侧上装下口袋,摸到一张折叠了的长方形纸。我都没时间来看这是什么。我把它抽出来,放进自己口袋。我转身跑向走道,电灯开关就在门旁,我把灯顺手关上,人在走道,我稍停一下,上下地看走道。全走道唯一看得到的有一个女人,大概55岁或60岁,头发烫过向上梳,把自己包在一件红晨抱里,站在一个走道末端开着的一个房门口。
“你有没有听到像是枪声?”我问她。
“就是呀。”她说。
我指向421说:“我看是……421出来的。我去看看。”
她仍站在门口。我走过电梯口。我叫道:“他有请勿打扰牌子在门外。我最好下去通知柜台。”
电梯开了门尚未离开4楼。我过去来到2楼,在2楼等着。
差不多等了l分钟电梯指针才指示它到了1楼。但是它立即又起动向上了。指针指示它到了4 楼。我自楼梯走下去来到大厅。职员不在柜台后面。雪茄香烟摊的金发女郎在看一本电影杂志。她下巴有节律地动着在嚼口香糖。她向上一看,又看回她的杂志。
走到街上、我把那张长方形的纸拿出来看。这是一张凭票即付10000 元的支票。发票人薄雅泰。我把支票放进口袋,走向白莎停车的地方。车子已经不在了。我在那里站了一下,还是见不到白莎的踪迹。我步行走过3 条街,才找了辆计程车,告诉驾驶我去车站。在车站里我把旅社钥匙抛入邮筒,另叫了一辆计程车,来到离薄家3条街外的1个大旅社,我把车费付了。我等车子走了,自己步行去薄家。
管家还没睡,当然薄好利给过我一支钥匙,但是他还是开门让我进去了。我问:“薄小姐回来了吗?”
“是的先生,她10分钟之前回来了。”
“告诉她,我在日光浴走廊等她。”我说:“是重要事。”
他看了我一下,眨了两下眼.他说:“是的,先生。”
我走出去,来到日光浴走廊坐下。雅泰大概在5 分钟之后下来。她走进来的时候下巴高高向上翘着。“你还有什么话可以说。”她说;“也不必解释了。”
“请坐下。”我说。
她犹豫了一下,坐了下来。
我说:“我要告诉你一些事,我要你记下来。今晚睡觉时想一想,明天更不可以忘记。你因为十分累又精神紧张。你推掉了一个约会。你决定去看场电影,但是看不下去,于是你就回家。你什么地方也没有去过。你懂了吗?”
她说:“我下来这里,是要一劳永逸地告诉你,我讨厌别人对我偷偷摸摸探讨我的隐私。我想一定是我继母聘你来看我我在想些什么……现在她知道了。其实我真的可以亲自当了她的面告诉她的,无所谓的。至于你,你叫我看你不起,你根本……”
我说:“不要空想了。我是一个侦探,但是我是被雇来保护你的。”
“保护我?”
“是的。”
“我不需要任何保护。”
“那是你在想。你要记住我告诉过你的话,你今天太累,你精神太紧张了,你推掉了一个约会,你去看电影但是看不下。你回到家里来。其他,你什么地方也没有去。”
她瞪视着我。
我把那张拿回来的支票自口袋中拿出来。“我想你不会在乎毁去这样一张小数目的票子吧。”
她坐着看向支票,两眼盯着支票,脸变得苍白不湛。
我自口袋中拿出火柴。擦亮了点着支票的一角。我拿着直到火焰烧了支票烧上来快烧到手,才把着火的一角抛到烟灰缸去。等支票烧完了,我用手指把纸灰磨成粉。
“晚安了。”我说,我走向楼梯。
她什么都不说,等我到了门口。“唐诺!”她大叫。
我什么也不说,只是把门自身后带上,上楼,上床。我不要她知道那家伙被谋杀了,我宁可她自新闻上得知,或警察来告诉她,万一旅社里有人认识她,警方会找上门来和她对质,到时她的惊奇表情会真实一些。除非她早就知道了?
我辗转反侧,久久不能入眠。
第五节
清晨3 点,警笛声传来。很远的时候,我就听到了。我起床,把衣服穿上,因为,真要有事发生时,我不喜欢措手不及,毫无准备。但是,我也立即想起在这件事件中我自己的立场,我又脱了衣服,回到床上去。
但是来的警察要找的不是薄雅泰,他们大声敲门把薄先生叫了起来。他们要和丁洛白谈话。
我在睡裤外面穿上了一条长裤,我又套上一件上装,在丁洛白下去到图书室里之后,立即踮足来到楼梯头。警察根本没准备客套,也不想降低声音。他们想知道到底他认不认识一位叫金见田的男人。
“怎么啦,是的。”丁洛白说:“我们有一位推销员,叫作金见田。”
“他住在哪里,你知道吗?”
“不知道。我们办公室记录里有。怎么啦?他干了什么了?”
“他什么也没有干。”警察说:“你最后在什么时间见过他?”
“我已经有3、4天没见到他了。”
“他负责些什么事?”
“他是个推销股票的人。事实上他是个测候人,他看准哪一个人有希望买股票,用电话报告进来。其他的人去销给他。”
“销什么股票?”
“矿。”
“什么公司?”
“没收农场投资公司。仔细的情况,恐怕要劳你驾去问我们的法律顾问。”他说。在我听起来这是他背熟的一句搪塞话。“我们的法律顾问是韦来东律师。他事务所在翔实大楼。”
“你又为什么不肯自己回答这问题呢?”
“因为这里面牵连着不少法律问题,而我是其中职员之一,随便发言可能会引起相当窘的情况。 ” 这显然是受过训练的一套说词,而且言来非常友善。他说:“假如你能告诉我们想要什么,我可以给你们更多的帮助。但是律师叫我不要谈公司的业务,因为我说任何话,都可能是律师认为我不该说的。你知道,这一切都是专业细节……”
“省了吧,”警察告诉他:“金见田被谋杀了。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谋杀!”
“是的。”
“老天,是什么人谋杀他?”
“我们不知道。”
“什么时候被杀的?”
“今天晚上7点左右。”
小洛说:“把我吓糊涂了。这个人我不是特别熟,他和我只有业务上的联络。苏派克和我才谈到过他,算来可能正是他被杀的时候。”
“谁是苏派克?”
“一位我的同事。”
“你们俩在谈他的时候,是在什么地方?”
“在我们办公室里。苏派克和我两个在闲聊,也谈一些业务上的问题。”
“好吧,这个死了的人有什么冤家没有。”
“我实在对他知道得不多。”丁洛白说:“我的工作多半和设计和政策有关。人事是由卡伯纳处理的。”
他们东问西问地混了一阵,都离开了。我看到薄雅秦也自卧房踮足外出。我把她推回去。“没你的事,”我说:“你回去睡觉。他们来看洛白。”
“干什么?”
“好像金见田是替小洛工作的。”
“但是他们为什么要为这件事见小洛呢?”
我认为这时候把消息告诉她很合宜,我说:“有人杀掉了金见田。”
她站在那里瞪眼看我,什么也不说,也没有表情,几乎不呼吸。她已经卸妆,我看到她嘴唇变白。“你!”她说:“老天,唐诺,不会是你,你不会—一”
我摇摇头。
“一定是你,否则你怎么会拿到……”
“闭嘴!”我说。
她向我走过来,像是在梦游一样。她的手指碰到我的手背,我感到她手是冰冷的。“你在想他对我是怎样的?”她问。
“我什么也没有想。”
“但是,你为什么—一为什么—一”
我说:“听着,你这个小呆瓜!我会尽量不使你的名字混进去,懂了吗?这支票假如被发现在他身上,你会怎么样?”
我可以见到她在想这个问题。
“回去睡觉。”我说:“—一不行,等一下。你下去,问一下发生什么事了。问他们为什么那么多声音。他们会告诉你,他们现在相当兴奋着。他们不会注意你表情、言行的。明天就不同,他们会警觉一些的……有没有人晓得你知道我是谁了?”
“没有。”
“有人知道你出去是去看他?”
“没有。”
“万一有人问你这个问题,”我说:“你避而作答,顾左右而言他,但是千万别说谎,知道吗?”
“但是他们问我,我怎么能不回答他们呢?”
“不断问他们问题,这是你避免回答问题最好的一个办法。问你的兄弟,为什么这样晚他们会来找他。你尽量问每一个人,每一件事,但要聪明点,不要自授罗网了。”
她点点头。
我把她推向楼梯、“下去吧,别告诉任何人你见到过我,我要回床去睡。”
我回到床上,但是睡不着。我听到楼下人在热烘烘地谈话,听到楼梯上的脚步声,和走道的低声讨论。有人自走道上走到我的房门口,停在门口,留神地听里面情况。我不知道外面是什么人。我没有锁门。房里的光亮仅够我看得到门,我等着门会不会被打开。
没有。过不多久,天亮了。我才感到困意。我想要睡一下。自从走道上回来,我的脚始终是冷着的。现在脚底也温暖了,一阵倦意,我就睡着了。
管家敲门把我叫醒,起床替薄先生训练体能的时间到了。
在地下室的健身房里,薄先生甚至连身上穿的羊毛浴施也懒得脱下。“昨晚上热闹得很,听到吗?”
“什么事热闹?”
“有一个替小洛公司做事的人被杀死了。”
“被人杀死?”
“是的。”
“撞车还是什么?”
“是‘什么’。”他说:“零点三八口径转轮枪,3枪毙命。”
我一心一意看向他。“小洛一直在哪里?”我问。
他的眼睛转向我,他没回答这问题,相反地他问我:“你一直在哪里?”
“工作。”
“什么工作?”
“我的责任工作。”
他自他袍子里拿出一支雪茄。把尾部咬掉,点着烟,开始抽吸。“有成绩吗?”他问。
“连我自己也不知道。”
“想像中呢?”
“我想是有点收获的。”
“找到什么人在勒索她了吗?”
“我都还不能确定她有没有被勒索。”
“她总不会把支票像彩纸一样随便乱抛抛掉吧。”
“不会。”
“我要你阻止它发生。”
“这一点我可以办成。”
“你认为她不会再付出钱去了?”
“我不知道。”
“要你有点进步可真难呢。”他说;“记住,我出钱是要求有结果的。”
我等候他自己打断他的话题,然后我说:“我们的生意都是由柯白莎亲自管制的。”
他笑了。“我这样说好了,唐诺,你是个小个子,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像你这样有胆量的……我们上楼穿衣服吧。”
他没有再提起为什么他要问我昨晚我在哪里,也不再问我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