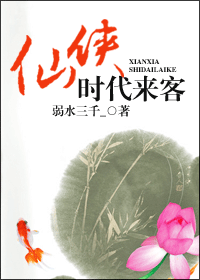巴巴罗萨来客-第2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一名戴着直筒帽子的仆人带他去电梯的途中,他看到有个人略微使他不安,这个人,也装扮成普通人的样子。这是一个矮小、结实有力的年轻人,黑皮肤,很自信,眼睛转个不停,一副街头拳击手的样子。他站在靠近电梯门口的地方,仔细看着每一个走近的人。这个人肯定既不是秘密情报局特勤科的人,也不是瑞典的特工人员。他浑身都透露着克格勃的样子,就像在英国海岸边石头上刻的字那样明白无误。情报局雇用的精神病医生根本说不出梅多斯是怎样看出这一点的,但他就是能看得出来,这部分原因是直觉,部分原因是他有长期在莫斯科的经验。他的鼻子嗅一嗅,脑袋里的天线转一下,就得出了答案,这是克格勃的党徒。对尼格西来说,这很令人不安,因为他知道,如果邦德在那里,也会得出同样的答案。在航班上,他开始觉得他对007 的失踪有负罪感。
他们来到他的房间时,电话上的信号灯还在闪烁,但仆人坚持要向他介绍室内的豪华设施,虽然豪华这个词在瑞典的生活方式中完全是侮辱性的。
尼格西想要将这个仆人赶走,他走向他,想将他挤出房间,将钱塞到他手里,给的小费比最多的还多三倍。但这仆人仍然不管不顾,继续他的长篇讲话,赞扬房间的设备、小酒吧柜和美妙的电视系统,这电视除了一般节目外,还可以放映绝妙的成人片,还有三个台可供选择,加上天气预告和CNN 。
费用也都还公道。
他还在讲个不休,一面炫耀他的英语,一面也是遵从饭店的规矩。梅多斯当他的面关上了门,转过身去,扑在床上,抓起那头的电话想得到消息。
“请呼伯纳多特套房好吗?现在接通好吗?请!”
“富兰克林·明特的套房,”比尔·坦纳的声音在他听来是个安慰。
“我是伯特。猎人回来啦。”没有“灰色的鹅今晚飞翔”这种废话。只说伯特就够了,当然,后面是重要的暗语。
“老家伙,尽快上来。”不到4 分钟,尼格西·梅多斯就站在这套著名的房间里了。这房间曾是像吉利、享利·福特第二、理查德·伯顿和伊丽莎白·泰勒这样一些名人的住处。
M 坐在一把舒适的椅子里,手里捧着一杯茶。“尼格西,来点吗?”他的微笑是狡猾的老鳄鱼的微笑。梅多斯谢绝了,并问这地方是否保险。
比尔·坦纳说,“像坟墓一样保险。”于是尼格西告诉他们,在走廊里有克格勃的人。
M 看起来一点儿也不慌张,“是的,我们将主持一个小而非常秘密的会议。”
梅多斯说,“噢。我坐下来打牌时,他们就都笑我。”
M 疲倦地叹了口气,“梅多斯,你总是说笑话。我了解,你丢失了我们最钟爱的人。”
他点着头,内心却很愤怒,“雪、冰、莫斯科之夜。这整个情景。我们以为我们完全掌握着他们的行踪。他们却用他妈的一架大直升机直接飞越我们的头顶将他接走了。”
M 又喝了一口茶。“这茶真的很好,你真的不要喝吗?”
“不喝。”梅多斯说。他这一辈子花了很多时间告诉他妻子,当他说不要食物或茶时,他就是真的不要。她总是在他说不要时强迫他要。
M 似乎在与茶壶讲话,“我们派人到了现场,你真的从他那里听到了可靠的信号吗?”
“你可以在十英里以外就听到这信号。只像通常那样偶尔失去信号。这不是设备的问题。”
“于是你就空手而归了,梅多斯。”
这又促使他回忆起另外一件事。他父亲看了格雷厄姆·格林一本书中的一行话后在发笑(他记不得是哪一本书了)。书中一个私人侦探所的头头对他无所收获的侦探说的几乎就是同样的一句话,“这次你又空手而归了。”
“你如果指的是他们逃得太快,我追不上,那倒是真的。我不可能乘着伏尔加汽车飞到天上去。当时又在下雪。我负的责任又有限。”
“他们是太快了。”M 微笑着,表示他是和他的下级说笑话。“这不是你的错,尼格西。”
“是啊,这不是我的错,但也不使我轻松。”
“当然不轻松。请坐下,详细对我们讲讲经过,我想了解细节。”
他从头到尾讲了一遍,从威尔逊·夏普收到邦德的快速电报起,一直到事情结束。他们在桌上放了一本用螺旋丝装订的莫斯科与郊区地图,让他指出跟踪的每一个地点,M 不断地插问。他说他要了解细节,他问得很细——附近有什么其他的汽车,梅多斯驾车跟踪的方式等。
M 嘟哝着说,“俄国内务部的监视车,你知道他们的车号吗?”
梅多斯想也没有想就朗朗说出了车牌号,这使他自己也吃惊。这类事是一个好的外勤人员的第二天性。在秘密情报局预备学校受训时,他们花了许多小时做一种类似游戏的训练——放了多样物品的盘子打开一分钟,然后要学员列出盘子上各物品的清单。在他们实习时,他们学习记忆法帮助记忆力,像鹦鹦一样将车牌照与电话号码记住。
M 用手指在尼格西与保镖戴夫·弗莱彻驾车经过的街道上划圈。“你们已很靠近莫斯科国立大学了。我指的是城里的附属建筑,不是在列宁山上的主建筑群。”“是,距离不到一个街区。”
“没有什么麻烦事?没有特别的事?有没有车走的样子比较古怪?”
“所有人都开得很慢。有时雪下得很大。”“你没有看到一辆旧的吉尔车?”M 反复说出一个牌照号码,梅多斯摇了摇头。
“你当时距一起凶杀案现场已非常近了。你离开莫斯科以前没有听一起到谋杀案吗?”“我没有听说。在莫斯科经常有谋杀案。每晚都有。莫斯科愈来愈像华盛顿了。”
M 哼了一声。
“有什么特殊的事吗?”尼格西问。
“那所大学的一名英语教授的半个脸被炸飞了。他是坐在停着的汽车上的。是一个姓雷科的人。如果我记得对的话,他的名字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可能他是开车将他们送进城来接头的司机。‘正义天平’还干了另一件事。”
“他们似乎在履行他们的诺言。”
“这是同一伙人干的两个案子。有一名外交政策顾问和他的妻子在别墅中被人勒死了。那天他休假。”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度假方式啊。”梅多斯总是不由自主地顺口说一些不恰当的评论。M 对他皱了皱眉头,他的脸一副怪相,就像吃了一口腐败的鱼似的。“他们用那女的唇膏在镜子上写了‘正义天平’四字。我谴责那些为引起轰动效应而拍摄的系列杀人片。”他面向比尔·坦纳说,“我认为应该叫鲍里上来了。要他明白,我们要他等在那里,并没有不可告人的动机。
我不想使他认为我们是对他进行心理战。”
当坦纳出去时,M 告诉梅多斯他们要见的是什么人。他详细介绍说,“他叫鲍里斯·伊万诺维奇·斯捷帕科夫,是俄国反恐怖部门的负责人。像往常一样,他这种人是不受法律管辖的。他只向最高层领导人报告。他与克格勃其他部门没有往来。他的档案不在总部的大型计算机里。就是这个人来向我们请求帮助的,我对他有百分之八十的信任。”
梅多斯问,“还有百分之二十呢?”
“我们必须留有怀疑的余地。如果没有未知因素,就不需要我们了,会计师都能干我们的工作了。”
“我有时认为会计师已接管了这个世界了。”
M 回答说,“可能是的。”这时,比尔·坦纳回来了,带来一个高高个子,脸长长的,像个小丑,不停地把额头一绺金色头发向后拂。
鲍里斯从委琐的、皱巴巴的衣服口袋里拿出一包万宝路香烟,问道,“介意我抽烟吗?”说着,用齐波牌打火机点着了烟。打火机的一面有金红两色的克格勃剑和盾的装饰。斯捷帕科夫将它抛向空中,又接住,笑着说,“一位朋友从洛杉矶带来的。我们买不到这样的东西,在新俄罗斯也不行。但这装饰不对。我们已将剑取消了。”
“是啊,但是会取消多久呢?”M 问道。
斯捷帕科夫耸耸肩说,“谁知道呢?历史教导我们说,人基本上是精神病患者。人不会汲取教训,这就是为什么历史总是周而复始。有一天,剑会回来的。”
他不愿在旅馆房间里谈话,他们也理解这一点,因为这不符合他所受的训练,于是他们到外面,沿着饭店前面的码头走。M 的人在一定距离外围着他们,而斯捷帕科夫的两个人——一个像街头拳击手,另一个和他不相上下——则靠他们很近,不过也听不到他们说话。
斯捷帕科夫说,“我们也试图跟踪他们。我们有汽车和两个监视小组跟踪你们”,说时向尼格西·梅多斯点了点头。“直升机很大,马力很强,是军用米12 型新型直升机。北约称之为“导航台”。它的航程近700 公里。他们很有效率,甚至把开车送你们的特工人员进莫斯科的人也除掉了。”
“我们的人,还有你的人,鲍里,”M 低下他的头,这时正有一股冷风沿码头吹来。“你们也渗入到这次行动中来了。”
斯捷帕科夫点了点头继续说,“雷科在把人放下后半小时内就被谋杀了,这说明‘正义天平’有可靠的内部消息。而且显然,他们的联系人已打入到军队,而且几乎可以肯定像我一直担心的那样,打入到克格勃内部去了。可能也打入了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但我还掌握一些大牌。有一个人,我的一个人,潜入军事空中交通管制中心工作。我想我们有‘导航台’的飞行计划。
因此,我想我们知道他们现在哪里。”
“离开俄罗斯了吗?是离此不远的一个地方吗?在一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
斯捷帕科夫摇了摇头。“不,他们在俄罗斯。只是在边境。在靠近芬兰边境的森林里。在北极圈里。”
他将确切的地址告诉了他们。他继续说,两年前,红军在北极圈有森林掩护处开始修建一座豪华旅馆。这是为了在严酷寒冷条件下受训的特种部队军官们。“但是,从来没有完工,这种花了很大一笔费用又取消了的工程有许多。许多人被派到这里来工作。军队称之为‘失去的地平线’。苏联国际旅行社并不想要它,但还是给了他们。他们什么也没有做。工作人员住在那里,但并没有开业。莫斯科电影厂要求用它拍一部电影,用飞机送去了许多技术人员。有少数人留下了。我估计这些人仍在那里。其中有些人,我认为,是受‘正义天平’控制的。那是个很好的安全屋。我猜想他们把可怜的彭德雷克先生就关在那里。”
“我们能从这里发起救援活动吗?”M 问道,似乎他已经知道答案了。
“我不认为能从任何地方发起救援活动。在开春以前,唯一的办法是用直升机。这地方是孤零零的,看上去像是中世纪的庙宇,但是用木头,而不是用石头建造的。”
“你没有办法吗?”
斯捷帕科夫耸耸肩,把头迎着风,好像要让风将掉在前额上那绺不听话的头发梳好。“除非我能说服我们特种部队的高级军官去——你们是怎么说的,冒一次险?”苏联特种部队是真正的精锐部队。斯捷帕科夫又将头在风中抬了一下,“但他们是由格鲁乌(军事情报局)控制的。”
“你在里面就没有朋友吗?”M 的声音突然变得急切了。斯捷帕科夫摇了摇头。
“我可能从中帮上忙。”这次M 几乎用得意的口气说。
几年以前,詹姆斯·邦德奉命到洛杉矶去杀一个人。在超级大国玩的游戏中,这既非同寻常,又完全不合法。与一般人以为的相反,情报部门是不参予暗杀事宜的,因为这会起反效果。如果你知道某个人是特工,或者是特工网的头,你可以用更高明的办法来消除这个威胁。第一条法则就是与你知道的敌人共处比用暴力除去他再冒一个更狡猾的暗藏的人来接替他的风险要好。
确实,有过一些报复性的暗杀,但这是卑劣下流的做法。是的,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曾有一些愚蠢的想法,提出许多可笑的暗杀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办法。但是,总的说来,暗杀不是一个可供选择的办法。
邦德被派去暗杀的人是在伦敦干了几乎10 年的双重间谍。年复一年,他的要价越来越高,他给得少,却要得多。他开始表现出自大狂的各种征候。
最后,当风雨欲来,威胁到他时,他已被一名女子推至绝境。那个在伦敦与他同居的美女离开他,跑到美国洛杉矶去了。他跟了去,做了许多蠢事。
例如偷偷潜入到她住的房子里,在黑夜里将花放在门阶上,深夜打电话给她。
他还打电话给华盛顿的英国大使馆,要求与主管特工人员谈话,并提出有可能对英国的情报界造成很大麻烦的威胁。因此邦德在没有征得美国同意下被派往

![[综]多么神奇的悦来客栈!封面](http://www.aaatxt.com/cover/4/4957.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