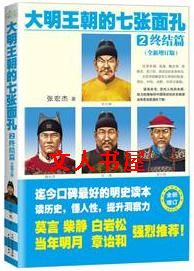别人的假面-第3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合成同盟,研究候选人资格,详细考虑选举委员会主席和议长,议会斗争的战略,同时谢尔盖·尼古拉维奇·别列津作为代表不能再做生意了,所以他必须暂时停止参加商务活动。得到一份新的工作,体面地摆脱了货币游戏。总而言之,目前的工作量很大,所以谢尔盖·尼古拉维奇·别列律埋头工作。此外他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声望。因此,在他们家几乎每天都高朋满座——时而是党内同志,时而是报界的代表,时而是谢尔盖·尼古拉维奇·别列律普通的老朋友和老熟人。当然,谢尔盖·尼古拉维奇·别列津总是给伊琳娜打电话并事先通知,他出去和回来都不是他一个人。反正她一直处于紧张的状态,因为她明白:即使他在到来前一个小时通知她,她也来得及为他提供他要求的那种接待。因此一切都应该提前做准备,以便在剩下的一个小时里只是摆桌准备开饭,“锦上添花”和把菜热一热。
“伊拉,”谢尔盖·尼古拉维奇·别列津激动地对她说,“你的烹饪天赋使我产生了俄罗斯风格的念头。这是十分美好的思想。我不打算扮演亲俄罗斯者和大国沙文主义者,但是主要的不是指靠西方,而是汲取某些传统的俄罗斯方面的力量的政治家应该引起同情和好感。假如我是肥胖而满面红光的人,那我就像只是因为面颊肥胖遮住了视野和不让睁大眼睛的陷入亲俄主义的商人了。而我的外表完全是欧洲式的,我开着价格昂贵的豪华轿车,穿着贵重的好衣服、我有一个年轻苗条的妻子,而且稍微有点被俄罗斯化的生活方式赋予我的形象以特别风味和无与伦比,您是怎么认为的?”
她没有认为他有什么特别之处,因为她不懂得政治,而且对它也不感兴趣。但她记住了:她与谢尔盖·尼古拉维奇·别列津签订有合同,对双方有利的合同。根据这个合同他得到一个彬彬有礼的妻子,而她从里纳特这个靠像在棉花种植园里的奴隶一样利用自己的女孩做妓女赚钱供养的魔掌中挣脱出来。谢尔盖·尼古拉维奇·别列津履行了合同中自己的那部分义务,在维克托·费奥多罗维奇·洛希宁的帮助下他做到了现在使伊琳娜对里纳特不感到害怕的地步。你瞧,她应该履行自己那一部分义务——扮演谢尔盖·尼古拉维奇·别列津所希望的那种妻子。因此,每天在家里都有红菜汤和小甜圆面包、大馅饼、大蛋糕、乳猪肉、鱼冻。尽管有这么多好吃的东西,但欧式饮料和下酒菜也没有取消。伊琳娜愉快地操持着家务,阅读了大量烹饪书籍,掌握了许许多多新的烹饪方法,大胆地进行试验。每次试验都达到了异常好的效果。尽管在操作法的描述中她有不明白的地方,但她的悟性很高,一切都做得精细、直观、正确。她喜欢为谢尔盖·尼古拉维奇·别列津的衬衫或者床上用品熨烫时织物所散发出来的那种气味。她喜欢每天早晨在谢尔盖·尼古拉维奇·别列津走了之后在住宅里收拾房间,擦掉灰尘,用吸尘器吸去毛织双面地毯上和软座家具上的尘土。有一次,进入卧室并开始进行每天一次的清扫工作时,她若有所思地在未收拾的床铺上坐了一会儿,然后躺了一会儿,把脸埋到谢尔盖·尼古拉维奇·别列津睡觉的枕头里。从枕头散发出几乎可以辨别的皮肤和头发的气味,幽雅而好闻。这种气味就同他是晚上回来不是一个人时当着所有人的面亲吻伊琳娜的面颊和嘴角时他身上所散发出来的那种味一样,别无二致。她越来越喜欢这个有魅力的男人。他心情安宁,精明强干,办事稳重。她也没有想对他的某些责备和有时带有侮辱性的攻击抱怨,因为她明白:在他们身上的罪过是均等的。而她除此之外还是个妓女,虽然谢尔盖·尼古拉维奇·别列津在各方面过着上流社会应有的生活。
她躺在他的枕头上,闭上眼睛在想,也许不定什么时候她真的会成为他的妻子,而且他们还有孩子,进而他们将成为一个真正的家,自从她陷入里纳特的魔爪时起,她只有一个夙愿:房子、丈夫、孩子。房子有了,有了需要操持的家务,也有了一个侍奉的男人。正好事情的一半完成了。剩下要完成的是使和这个男人有关联的不仅仅是家务和注册中的盖印,而那种事要多一些,就会生孩子,哪怕是一个。
伊琳娜想起了,当她告诉他有关季阿娜·利沃夫娜拜访的情况时,他的脸上呈现出怎样的惊惶神色。
“她什么都没有发现?”谢尔盖·尼古拉维奇·别列津追问道。
“我从哪里知道?”伊琳娜表示不解地耸了耸肩,“据交谈的情况判断,没有。她的确说了,我变得不怎么好看了,但我认为她这是故意在刺激我,让我难堪,而不是因为这是实情。谢廖扎,你说说,当初新婚后你真的找她埋怨过生活吗?”
“她也讲这个来着?”谢廖扎板起了面孔,“季阿娜·利沃夫娜永远是一个恶魔。她总是喜欢公开泄露别人的秘密并由此而感到满足,看别人的尴尬和难为情。”
“这就是说,你找过她?”
“找过。结果怎么样?”
“没有什么,倘若你能回忆起当时你对她说过什么,那简直就更好了。这便保护了我免受许多令人不愉快的意外事情。我怀疑,我和季阿娜·利沃夫娜还会不止一次地见面。”
谢尔盖·尼古拉维奇·别列津不敢正眼看人,仔细认真地回忆起了他在七年前对自己第一个妻子发第二个妻子牢骚时所说的话。其中上述某些话是真的,稍微有点夸张,有些是明显地在故意歪曲。因此谢尔盖·尼古拉维奇·别列津感到不好意思,但他勇敢他讲了出来,因为他明白:伊琳娜在这种情况下有百分之百的权利知道这一点,她必须知道这一点,如果她想恪守他们合同所有条件的话。
最后,精神上的极大痛苦以直言不讳而告结束,于是谢尔盖·尼古拉维奇·别列津松了一口气。
“当她来到的时候,你很害怕吧?”
“很害怕,因为我完全不明白,自己应该如何是好。我觉得,我无论做什么——一切都显得不合时宜。我打算谦恭有礼貌地说——忽然碰上没鼻子没脸地一通挖苦和嘲弄,她说,你一下子抖起来了,从妓女变成了公爵夫人了。我试图表现得冷酷无情——她要求姑息宽容,提醒我,我比她年轻得多。我表现得很持重,尽力不用自己的年轻激怒她,而她马上便重复说,看上去我很不好,总之变丑了。你要知道,她好像和我在玩猫捉老鼠的儿童游戏。她要说下流话就看我,好像在偷偷地观察、监视,很想知道,她得到的反应是什么。”
“她对我也是这样表现的。”谢尔盖·尼古拉维奇·别列津点了点头,“我和季阿娜·利沃夫娜过的整个这二十年我感到自己是个用来做实验的老鼠。”
“我觉得似乎她比你大。”伊琳娜说道。
“是的,大六岁。顺便说一句,她的气色怎样?两年前,当我最后一次看到她时,她气色极佳,现在她已是快五十岁的人了。”
“就是现在看上去她的气色也不错,神态端庄,几乎没有一丝白发,眼睛炯炯有神,一身上好的西服。你要知道,我觉得似乎在她身上没有对你的仇恨,而且她对我也不嫉妒。这好还是不好?”
“我的天啊,伊拉,当然这好。如果把季阿娜·利沃夫娜作为仇人的话,不如马上上吊自尽以免遭罪。你是个聪明人,没有与她发生冲突而能够达成协议。去她的吧,让她自己去做女人的蠢事去吧,只要别张开她那张臭嘴就行。你要明白,会有人向她讲许多谢尔盖·尼古拉维奇·别列津和他第二个妻子的事的,作为政治对手我不怕她。”
“为什么?”
“因为我们国家的人民幽默感发展适度,没有过度。”
“我不明白,”伊琳娜现出阴郁的神色,“这其中有幽默感?”
“喂,你看电视时大概看过扎多尔诺夫的演说吧,当他说:‘为什么选择日里诺夫斯基?——这是人民在开玩笑?’为了女人领导的政党在下一次选举中获得百分之五以上的选票,人民重新要经受无法遏制的玩笑,而且比今年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我认为再过四年当选民们看到他们的特别幽默变为什么的时候,选民们止不住的笑将会减弱。因此你满可以按着季阿娜·利沃夫娜的请求为她做广告式宣传。只要她不做卑鄙的事,就让她玩一玩吧。”
在谢尔盖·尼古拉维奇·别列津回到家之前,整个这一周伊琳娜没躺下睡觉,关于这一点谢尔盖·尼古拉维奇·别列津特别地请求她,所以她不能拒绝,尽管他回来都很晚——十二点钟,否则就是夜里一点。经常是在大约六点钟带着两三个不认识的人回来,伊琳娜扮演着一个好客女主人的角色并为他们做饭,此后谢尔盖·尼古拉维奇·别列律到很晚的时候又走了。偶然能遇到夜里零点钟也不是一个人回来,这时伊琳娜摆桌吃夜宵并默默地等待客人们离去。
“如果女主人离开去休息,”谢尔盖·尼古拉维奇·别列津说,“客人就会开始感到尴尬,以为女主人厌烦了,影响她睡觉了。因此,我请你别比我早睡。最后,你根本没必要每天早晨六点半起来给我做早饭,我完全可以做好这些的,而你尽情地睡,想睡到什么时候起就什么时候起。但对我来说重要的是,晚上我能安心地邀请无论是谁到家里来并明确地知道,笑容满面的妻子给我开门,而在住宅里能闻到烤大馅饼的香味。这一点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你明白吗?”
这时伊琳娜去自己房间睡觉了,轻松地想着明天她将在被窝里闲躺到中午。然而尽管他们差不多是夜里两点钟躺下的,但六点半她已起来了并到浴室洗了脸,梳好了头发,而快七点的时候从厨房里开始向外传出令人陶醉的咖啡磨嗡嗡作响声、茶壶咝咝声和煎锅发出的唏嘘声。对正常的男人来说,这是象征着家庭的舒适、女人的关心和正常家庭的声音。
“你到底还是起来了。”谢尔盖·尼古拉维奇·别列津出来吃早饭时责备地说,“昨天我已经告诉你了,早晨你可以晚点起,多睡会儿。”
但是,他自己没有觉察到当他看到身着淡蓝色长裙、外面扎上一条漂亮绣花围裙的伊琳娜时,他的脸上绽开了怡然自得的微笑。活见鬼,他感到高兴的是,她到底还是起来了,为他做了早餐并送他去上班,因此他看到她非常高兴。
“你不明白,谢廖扎。”她微微一笑,“为丈夫做早餐起早——对我来说是件愉快的事。我发觉自己有这样的习惯动作:我醒来、开灯、看表,看到已经早晨六点钟了,便高兴地在想,多好啊,只剩下等半个小时了,要知道没有闹钟我也能醒。”
“你说什么?”谢尔盖·尼古拉维奇·别列津感到很惊讶,“冬天,在那种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而且没有闹钟?我永远也不相信。”
“请你到我房间来看一看。”伊琳娜提议说,“我有一个闹钟,但它被我放在箱子里了。自从你把我从疗养院接回来时起我一次也没有把它拿出来过。”
在那天早晨,谢尔盖·尼古拉维奇·别列津准备去上班时,突然亲身体验到了一种出乎意外的和无法解释的、强烈的喜悦感,因为晚上当他回来的时候,这个面容娇嫩讨人喜欢的女人将会在家里等着他。他已经穿好大衣并拿起了手套,但他突然走到伊琳娜跟前并紧紧地拥抱了她。
“我很高兴你做我的妻子。”他轻声地说,“总之,我终于第一次开始明白了,有妻子意味着什么。头几年我有的不是妻子,而是一个教我生活和良好举止的、要求严格、求全责备的老师,而后来在七年的时间里与我生活的是一个令人十分恼火、变化无常、极端任性的孩子气的人,这个孩子气的人随时都有可能耍各种花招并需要经常照顾,我经常因为她的行为蒙受巨大耻辱。只有现在我才开始明白什么是妻子。”
伊琳娜感觉到了在自己后背上他那双温暖的手,一动不动地愣住了,莫非他要吻一吻她?她羞怯地扬起头准备把一切凭经验得到的性欲和多年来蓄积起来的柔情都献给这一吻。谢尔盖·尼古拉维奇·别列津用温存亲切的眼睛看着她,但伊琳娜在他的眼睛里没有捕捉到那种熟悉的、发生在亲吻之前的、轻浮的“失去理性”,当然,如果这个吻不是专门的,也就是性欲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的话。
她原来是对的。拥抱不是给人以希望的猛烈、有劲儿,而亲吻没有随之而来。在紧靠门的地方谢尔盖·尼古拉维奇·别列津做了一个再见的手势并又出去了一整天。
这是星期五,而在星期六一大清早维克托·费奥多罗维奇·洛希宁就打来了电话。
“近况如何?亲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