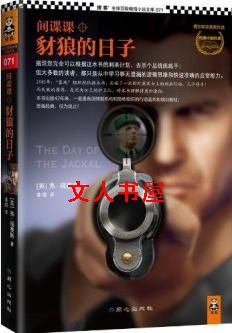豺狼恶人-第5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您好!”陌生人说道,点个头,友好地看着,打量着,“我是本地刑警局局长中校波波夫,”伸手给古罗夫,“高兴与您相识,列夫·伊凡诺维奇。”
“你好!同行。”古罗夫握着伸过来的手。
“欢迎,欢迎!”斯坦尼斯拉夫脸上显出憨厚的微笑说并且把工作证递给陌生人,“列夫·伊凡诺维奇是大明星,一看他那一张脸就认出来了,我们则是一般的密探,需正式介绍才行。”
作这样的暗示没有别的意思,来人立刻明白,拿起了克里亚奇科的证件,把自己的证件递给他。来人是特勤人员毫无疑问。但具体情况又如何呢?他很可能是联邦安全局的人,自己装成是密探。在国家安全局人员和民警之间早就存在着不愉快的事。有那么一个时期密探不按警衔拿钱,职务固定工薪很少。结果是,民警里一样职务和警衔的侦查员比克格勃少拿一倍工资。更不用说特殊装备和交通工具了。刑事侦查局的侦探每天要和犯罪分子斗争,从骗子和小偷开始到惯犯和杀人犯。密探们冒着生命危险,也说不上哪一天一块砖砸到头上,肋旁挨一刀,吃一粒枪弹。而委员会的侦查员穿得干干净净,找出那些经常出入旅游宾馆和酒楼的持异议分子。政府当局把特勤分成黑的和白的,这不能不影响人际的互相关系。如今这种区别逐渐消失,但互相关系中的憎恨和戒心还是存在的。
斯坦尼斯拉夫拿着中校的证件并没怎么看里面是怎么写的,核对照片,只是像烤饼似的翻了翻,估价了一下它的破旧程度,确认这不是掩盖身份的“通行证”也不是昨天才制出来的。
“很好,尤里·瓦西里耶维奇,”斯坦尼斯拉夫还了证件又取回自己的证件,“生活怎样,不枯燥吧!”
“有时相当枯燥,但大部时间是开心的,上校先生,”波波夫笑道,“俄罗斯人特别能出花招,偶然谁杀了谁,抢劫了谁,引人入胜的事。从南方来的客人不会忘记拿些捐助。总的说来我们生活得并不枯燥。列夫·伊凡诺维奇,”他看了一眼古罗夫说,“将军告诉我你们要来。我们是同行,有什么要帮忙的吗?”
古罗夫略加思考,看了斯坦尼斯拉夫一眼,他点了一下头。
“尤里·瓦西里耶维奇,你吃过晚饭了吗?”古罗夫问道。
“一般都是在路上吃的。”波波夫说,这个在刑事侦查局工作过十五年的人清楚地知道,总局来的人不会很快吐露出真实情况,什么也没告知,但处于主人的地位需要给予协助。
在宾馆餐厅吃饭,什么都没说,扯一般性的闲谈,五个人喝了一瓶伏特加酒。当喝完咖啡时,斯坦尼斯拉夫站起身来说道:
“呶,感谢领导请我们吃晚饭,现在侦查员们需要睡觉了。”
“祝您一切顺利,大家好。”波波夫站起身来要告辞。
“我很快就来,”古罗夫点点头,用眼睛看着侦查员们走出餐厅,环视一下这个不太干净、烟熏火燎的大厅,问道,“常有开枪射击的事吗?”
“不敢说常有,偶而也发生,”波波夫回答说,“久闻大名,列夫·伊凡诺维奇,如果我能帮助您,将尽力效劳。我不敢说我的伙伴都是能手,但他们都是沉默寡言的。”
古罗夫理解地点点头。
“我需要找一个小子,”古罗夫仔细地挑选词汇来描述伊戈尔·斯美尔诺夫。“他明天可能出现在总统演说的听众之中。暂时不要抓他,如果看到相当的人,请指给我们看。”
“带枪的人?”波波夫用日常的口气问,好像是对系领带的人或是敞着衣领的感兴趣。
“准确地说我还没想到,”古罗夫回答说,“如果他出现,可能我来抓他。他也许就像和普通老百姓发生冲突一样和警卫士兵发生冲突。”
“我们可以帮忙。”波波夫长长出了一口气,“哪时我们才停止战斗,难道就干这一件事吗?!”
“不要了,尤里,”古罗夫叫过招待来,要了二百克白兰地,然后结账,“美国人要什么民主,而联邦调查局的刑警们也不是白吃饭的。”
“不错,各自都有自己的精锐骨干。”
“还有,”古罗夫暂停了一下,等招待放下一瓶白兰地走开后又说,“可能市里来一个中校,此人可憎之极,是危险人物,叫福金·谢苗·彼得罗维奇,相信他会带有保护自己的文件。”
“国家安全局工作人员吗?”
“此人过去是上校,现居次要地位,但此人颇有影响,什么地方都去。他不住在宾馆,他的别墅你们都知道,”古罗夫详细地描绘了福金的外貌。“他是典型的莫斯科人,可能穿得简单些,但是还是能显示出他的本色来。如果遇到就立刻跟踪监视,立即向我报告。”
波波夫看了一下表,笑起来说:
“想起了吩咐下属的话了,没有我不要解散,可我自己坐在这里喝起来了。”
“不是每日都在喝吧!”
“我们努力做吧,列夫·伊凡诺维奇,”波波夫一饮而尽,拿出钱夹子来,不让客人付钱。
“不要这样,同行,上级总是要付账的。”古罗夫反驳说。
福金住在郊区一间别墅里,这是联邦安全局用作招待那些不慕虚名的客人的住所。
谢苗·彼得罗维奇喝完一杯伏特加酒,一小瓶瓦洛科金。不管医生怎么说伏特加与瓦洛科金不能同时用。这两种饮料在胃里融合的很好,中校感到轻松些,紧张情绪消失了。福金给自己沏了淡淡的热茶,铺好床,手不抖了,脚也站稳了,头脑也清醒了。但他觉得自己还是睡不着。明天重要时刻将来到,为此福金准备了半年,明天就决定一切了。他不知为什么要把自己比做冠军,这个冠军就要在奥林匹克运动场上起跑了。没有银质奖章,只铸造了金质奖牌,要到荣誉座位上只剩一级梯阶了,就要登峰造极了,剩下的就是虚无漂渺了。
谢苗·彼得罗维奇总是以自己的耐力而感到骄傲。有一次在克格勃学校里宣称,他是一个没有神经的人。有四分之一世纪以上时间境外秘密工作之经验并且上了年纪的老师,拿下他那宽大的眼镜并且一边擦试一边忧伤地说:
“这很不好,谢苗,你不知道你的神经怎样了。每一个会思想的人都有神经系统。有的人能自制,有的人则不能够。你连自己的这种情况都不知道,不好啊,神经在任何时候会使你上当。一切取决于赌注。”
这是很早以前的谈话了。在过去的时间里他有几次确信,他是一个普通的人,他的神经正常,他能克制自己。
此时他坐在落地灯旁边的圈椅里,喝着带把杯里的热茶,一边想着过去,一边理解到长者是对的,确信一切取决于赌注,你的希望。老师还说过不要与聪明的个人为敌。反间谍人员这是您职业上的敌人,这样认为,但没有把他变成个人的敌人。他强壮和危险许多倍。如果有人在你生活道路上拦了路,个人的敌人出现,就赶快杀掉他,不要等待烟消云散,地球转还。杀!决不要相信任何人,你的敌人会被另外一个人杀掉。让邻人开枪射击。但你私敌的尸体你必须亲自检查。老人说,“唉,孩子,我见过许多死者复活,他们就可以建立起很大一座陵墓。”
福金突然站起来,差一点打翻了落地灯,走进厨房,把茶壶放在煤气炉上,他白费力气地回想过去的事,现在看来没有安眠药是睡不着的。古罗夫的死亡像乘法表一样分明。现在没有时间回忆死去的人。
中校又喝了一点伏特加酒,吃了一片安眠药,喝了口水,闭上眼睛。睡眠还不来临,甚至相反,头脑更清醒了些,过去的事历历在目。
过去一年的事开始出现在杜马选举结果公布后一个同志式的晚餐上。老的肃反工作人员聚会在一起。自然,和胜利的“克普鲁弗”不同,在桌边的谈话是中立的,没有什么人拿出政治标语口号来。因循守旧的,有经验的人明白:刚刚过去的选举只不过是一个开场白,真正的故事六月份才开始。
坐在桌子后面环视一下,福金发现只有他过去的克格勃里的同事,那些人在当今政府里只据第二位或第三位。那时只有一个白头发的陆军上将是旁人。但就是他在年轻时曾在情报总局工作。谈论孩子们,生活,女人,骂骂现政府,但不是那么凶狠,心平气和的,就像一般市民一样地骂政府。他一边看着百货商店橱窗里的东西。看来现今情况不佳,但忍耐着,大家都知道情况可能会更坏。
参加这次聚会的人们的成分、他们的宴饮和谈吐的适度,引起了福金的警惕。请他来晚餐的这位上校在过去的克格勃里占据重要职位。他坐在桌子的主人地位,旁边就是陆军将军,显然是引导谈话。福金紧张地等待着开始谈实质性问题,决不可能是偶然地招集这些免职的安全局工作人员只为了喝杯伏特加闲扯一通。但谈话没有转折,散开时清醒了,真的还是摸不清头脑。福金注意到组织晚餐的上校和每个人交谈一两句。在街上,上校走到福金那里说:
“谢苗·彼德罗维奇,我的司机病了,你能把我捎带到地铁吗?”
“可以,”一边打开自己“伏尔加”牌轿车车门一边回答。他明白现在就要开始谈真正的事了。
当看清楚上校住在离酒店有两个街坊远的地方,福金什么也没说,停泊好汽车,跟着主人走进这座结实的房子,走过注视的年轻的警卫。
正如福今所料,房间内空无一人,主人引导他进入小房间,默默地摆几瓶酒在小桌子上,指给他圈椅。
“你看今天同学聚会怎么样?”主人一边斟满酒杯,“可靠的专业人员都失业了。”
“伊万·鲍里索维奇,过去你比我高很多级,既然你请我来不是闹着玩吧。请你长话短说开门见山好了,第一个问题,那么多人你为何只挑选我一个,请回答。”
“我要解释的,首先你说,现在胜利者的首领在六月份是不是毫无成功希望?”主人和福金碰杯,一饮而尽。
“我不明白,”福金承认,“我不太懂政治。”
“把政权抓到手的时间到了。特勤人员总是有权在选举投票上发出决定的声音。我们应该作的事情是叫总统依赖我们。就是今日沙皇在六月应让出宝座。”
“让出宝座,上哪里去呀,”福今坚定地说,“今天他的成就率是个零。”
主人同情地看了一下客人,有点宽宏大量地低声音地说,“总书记对此人估计不足,当上了苏联主席还是个笨蛋,最高苏维埃吹胡子瞪眼,国家特别非常委员会自己打自己的脸……有多少次可以向其进攻一下子将他扫除掉?”
“这一次他可无法起死回升了。”福金坚定地回应着。
“这家伙白手起家,现在还活着,必须抬他而到六月份一举胜过他。”
“那要我干什么?”福金耸耸肩说。
“一九八三年秋季,欧洲国家首都飞来了一个大人物,”主人暂停了一下,但福金一动不动,总的说找不出什么词来反应,主人抽了一口烟终于开口了:
“我听说那一天你离开了首都,首都里发生了爆炸事件。”
“可能是这样,这是很早的事了。”福金成功地表现出心平气和。
实际上,是他组织了那次恐怖行动,当时他只不过是情报总局的一个大尉。但他坚定地相信他在此次恐怖行动中的角色只有一个间谍头子知道,但那个人大约在五年以前已死了。
“略而不谈,我们这样决定好吗。谢苗·彼得罗维奇,如果你对此问题采取决定,我们保证给您一个委员会主席职位。”
“又是‘我们’和‘保证’,词听起来很好,”福金同意,“但你和我都是职业特工,伊万·鲍里索维奇,不管发生什么事情,组成什么样政府,上校福金不是那种人,谁都不给他那种职位。”
“我们需要专业人材,中立的人士。当然没有人会把所有政权交给你。我们来控制,但现在初期阶段你是最佳人选。”
“我很快就要出车祸了吗?”
“各种可能性都有,你自己决定自己的前途,我们说的是真话。你自己想一想,估量一下,让谁来执政好一些。最好不要和布尔什维克联系在一起,他们的恶习是毁坏了帮助他们执政的人们。”
“我可以想一想。”福金当时同意说。
在去年年末和今年一月份他不止一次地和上校相遇,弄清楚:以前的委员会后面有一股重要的力量,现实的专业人员。但是谁也不愿意当采煤工,去干费力不讨好的事。根据福金自己这种谨小慎微和斤斤计较的性格,他不会去贪图亚力山大·马特洛索夫的荣誉,但他越了解突击队的组成他就越觉得上校的建议可行。伊万·鲍里索维奇不想站到最高位,他想得到一个灰色主教的位置。
福金清楚记得,当时他想起拿破仑的话,主要的是参加战斗,在那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