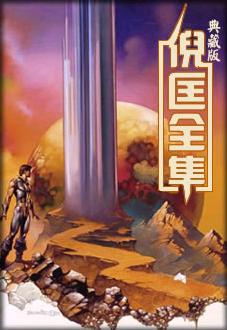电王-第1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说得十分坦白,而且他的这种心境。也可以了解,我道:“那你的意思是不再前进,回雪梨去?”
文依来道:“他死了,连目的地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怎么去?”
我道:“我倒知道一个大概,笛立医生要你去的地方,一定是你母亲出生的土著村落。要不是遇到了你们,我也准备去寻找那个村落的。不过这不知要花多久时间,尸体会腐坏的。”
文依来深深吸著气,神情为难,我又道:“而且这个人的身分十分神秘。我们和他在一起,他又死了。这种事,向有关方面解释起来,简直麻烦之至。他的死,另有原因。不会是你杀的。”
文依来双手握得更紧,神情十分苦涩,我陡地又追问了一句:“你为什么有这样的感觉?”
文依来道:“因为他曾十分恐惧地要我放手,而我没有放。”
我苦笑了一下:“除非你的手,有著可以致人于死的魔力,不然,抓住他的手腕,他也不会死的。”
文依来摊开手来,翻覆著看,在阳光下看来,他的手毫无异状,掌心绝没有什么鲜红色或漆黑色 像武侠小说中的“毒掌”一样。
他苦笑:“当然不会有什么杀人的魔力。怎么会?”
他说得十分勉强,好像隐瞒了一些什么,我又问:“你自小受非人协会的抚养,学了不少技能和知识,有没有学过中国武术?”
文依来道:“中国功夫?我只在电影中见过。”
他把中国武术称为“中国功夫”,那是最粗俗的一种叫法,自然是未曾学过的了,那么,看来也不必问他有没有学过内家气功了。望著“瘦子”的尸体,我俯下身,在他的身上搜了搜,一掀起他的外衣,就觉出外衣之中有一个十分隐蔽的夹袋,撕了开来之后,是一个密封著的、防水的纸袋。
在那纸袋上面,用四种文字写著同样的句子:“我是一个杀手。随时可以致人于死,也随时会被人杀死。如果我死了,这个纸袋被人发现,请发现人照纸袋中所写的行事,即使是杀我的人。也请照做。”
我和文依来看了之后,文依来道:“里面,可能是他的遗嘱。”
我道:“或许,先看看他身边还有什么。”
他身边的东西还真不少,除了普通人日常带在身边的东西之外,还有一只如同烟盒一样的扁平的金属盒,一打开,里面密密的放著许多只颜色不同的小盒子,那自然是他用来储放各种毒药的了。
我也不敢贸然打开小盒子来看,因为在野外风大,若然毒药是粉状的,被风吹得扬了起来,吸进若干,那可不是玩的,我知道有些剧毒的粉末,像这种指甲大小的小盒子,一盒就可以毒死好几千人。
盖上了盒子,又在他的裤袋内,发现了三柄极小的匕首,一拔出来,阳光下。刀身闪著一种暗蓝的光彩,自然也是淬过毒的。
我把在他身上找到的东西,全都放进一只布袋之中,和文依来两人,合力掘了一个坑,把他的尸体抛了进去埋好,又砍下一株灌木,插在沙上做为记号。文依来曾建议做一个十字架,我道:“算了,天堂中不会需要职业杀手的。”
这一下忙下来,早已浑身是汗,我们一起上了车,文依来道:“是不是要看著他的遗嘱?他总是死在我们面前的,他有什么事要做,也该代他做做。”
文依来的话,自然有理,我用力把纸袋扯破,里面是用牛皮纸包著的一个小包,包得很严密,一层层打开来,是一柄样子十分奇特的钥匙 钥匙上有许多不规则排列的小孔。
我知道这一类钥匙,是配合相当精密的锁使用的。和钥匙包在一起的是一张卡纸,卡纸上写著一个地址,是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从地址看来。是一幢大厦的一个单位。在地址下有几行字,也是分别用德文、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写成的。
“请到上址,用这柄钥匙打开一只镶有象牙的箱子。”
我和文依来互望了一眼,文依来道:“好像很神秘的样子。”
我闷哼了一声:“职业杀手,真是鬼头鬼脑。”
文依来吸了一口气,取了钥匙在手:“我回去的时候,可以替他去办事。”
我当然没有兴趣为了执行一个杀手的遗嘱而特地到维也纳去,所以点了点头。
第九章 探测师的奇怪遭遇
在“瘦子”身上找到的东西之中,一点也没有他要去的目的地的线索。甚至连地图也没有,真不明白他凭什么可以在广渺的澳洲腹地找到他要去的地方。
文依来望著我,等著我的决定,我道:“他曾一再说。前面会有一个牧场,可能他对这一带十分熟悉,我们先到了牧场再说。”
文依来没有说什么,发动了车子,向前驶去,果然,不多久,已可以看到前面是好大一片沙漠中的绿洲,驶上草地之后不久,就看到了一大群一大群的绵羊和牛马,那看来是一个规模极大的牧场。
车子继续向前驶,不多久,就在一排建造得相当考究的建筑物前,停了下来,主要的建筑物,居然是维多利亚式的大房子。
车子一停下,就有一群少年围了上来,我和他们谈了一会,知道牧场主人的名字是维克先生,为人热情好客,是这里附近几百哩,几乎百分之八十居民的雇主。
五分钟后,我们就见到了这位满面红光、身形高大粗壮得像牛一样的老人,在他宽大的书房之中,他应我所请,取出了一大叠大型地图来。
然后,他用十分洪亮的声音,指著其中的几幅:“刚刚族人很少离开山区,他们所履足的平地,也是在山中的盆地。”
老人又道:“至少超过十二个村落,是他们聚居的所在,你们要去找一个人?而不知道确切的地点?”
我道:“是啊,只怕相当困难,而且,虽然我会讲很多地方的话,但是却不会刚刚族话。”
当我这样说的时候,突然听到了“吱”地一声响,一张本来是背向著我们,放在书房一角的一张高背转椅,转了过来。
椅中坐著一个人,他一转过来,我只感到他的目光,十分锐利,异于常人,而且直盯著我。
这张椅子上坐得有人,这一点,我在一进书房来的时候就发现了,但既然主人未有介绍的表示,我自然也不便多口。
这时,他转了过来,在盯了我一眼之后,就目不转睛,望著文依来,既不站起来,也不出声。
他的行动,可以说是十分无礼的,但是当然也不便与之计较。我打量了他一下,他是一个有著一头十分悦目的浅灰色头发的中年人,身形瘦削,咬著一支烟斗,约莫六十上下年纪。
他在看了文依来好一会之后,又向我望来。场主维克对他像是十分尊敬,自他一转过身来之后,就未曾再开过口,他再望向我之后,突然说了一句话:“你以前到过士狄维亭山脉没有?”
我们要去的,刚刚族人聚居的山脉,正是士狄维亭山脉,但是他用来问我的这句话,却是用西非冈比亚河中游那一带的一种土语来发问的。
我听了之后,心中倒也觉得有趣,他自然是冲著我刚才说了句“我会说很多地方的话”,所以来考较我了。我如果用同样的话回答他,那倒叫他小觑了,为了表示我懂冈比亚河语,我先用同样的语言答:“没去过。”然后,我立即改用西藏康巴族人的语言:“阁下如果熟悉的话,很想请你指点一下。”
他听了之后,在他严峻的脸上,居然现出了一丝笑容来,再一开口,吓了我一大跳,竟然是字正腔圆的道地四川话:“名不虚传,硬是要得。”
我心中升起了强烈的好奇心,这个人是什么人呢?我答了一句四川话:“不算啥子。”接著我说的是爱斯基摩语:“你一定在四川住过,不然,不可能讲得这样道地,请教贵姓大名?”然后。突然又改用中国的宁波话:“又不知道你是如何知道我是什么人的?”
那人“哈哈”大笑了起来:“我知道你最后一句也是中国话,可是我不懂。”
我用四川话把那句话再说了一遍,那人摇著头:“我不以为两个不同省籍的中国人可以互相沟通。”
我笑道:“就算是同一省的,杭州人和温州人就无法交谈半句。”
那人道:“我当然可以知道你是什么人,我曾听过你不少事迹,也看到过你的照片。”
我笑对场主道:“主人如果不介绍一下这位先生,好像不是很公平。”
自从我和那人对话之后,场主用一种极其古怪的神情望著我,像是他再也料不到,一个随随便便来问路的人,居然还会有点来历。
而他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感觉,自然是由于那个人身分不平常的缘故,那个人身分非凡,连那人也知道我是谁,自然足以使得场主另眼相看。
场主望了那人一下,像是不敢胡乱介绍,那人站了起来,自我介绍:“我叫端纳,是一个探测师。”
端纳是一个相当普通的名字,探测师也不是什么特别的职业。可是我在一听到了他的名字和职业之后,心中陡然一动:我是听说过这个人的。接著,我想起了他那口道地的四川话,我立即“啊”地一声:“端纳先生,原来你就是被当年四川盐商奉为神明的那位洋先生。”
中国的四川省,号称“天府之国”,物阜民丰,可是缺盐,也不知道何年何代,由什么人发现的,凿井汲取含盐分的水,再凿井引天然沼气生火煮盐,盐井和火井的开凿技术极其复杂,可以写成一本厚厚的书,含盐的水和沼气,又都蕴藏在极深的地下,所以。先要勘察测量,决定这个地方是不是有蕴藏,然后再开凿,极其重要,不然,三、五个月苦干,若是一无所获,那就劳民伤财之至了。
所以,探测师的地位十分高,被富商大贾及民间官方,尊称为“先生”。而在众多的“先生”之中,据说,本领最大的是一位“洋先生”,这位“洋先生”,像是可以看穿地下几百丈深一样,他只要伸手一指,说哪里有盐就哪里有盐,哪里有火就哪里有火。
盐井和火井,全是日进斗金的财库,“洋先生”自然也受尽了尊敬。至于“洋先生”的名字是什么,也没有人追究,只要他能带来财富就行了。端纳笑了一下:“是,当时人人都这样叫我。”
而我又想起,当日白老大听我提起这位“洋先生”来时所说的另一番话:“这个人,有著超特的异能,日后若是见到了,倒要好好结识一番,不过听说他已经加入了一个什么非人协会,行动有点故作神秘,不好主动去找他。”
这句话,当时听过就算了,一点也没有放在心上,可是此际。却大不相同了。
他如果是非人协会的会员,文依来和非人协会之间有著极其深切的关系,文依来的来历,一定是他所深知的了,这正是求之不得的事。
所以,我立时又钉了一句:“听说,阁下是非人协会的会员?”
我这句话一出口,在我面前的三个人,反应各有不同,场主一副莫名其妙的神情,显然不知什么是“非人协会”。端纳只是微微一笑,来了一个默认。
而文依来一听之后,“啊”地一声,神情十分激动,向端纳走近了几步,又停了下来,用十分焦切的神情望著他:“那么,端纳先生,你一定知道我是什么人了?我……卫先生说,我可能是由……非人协会养育长大的。”
端纳望著文依来,半晌不语,才道:“卫先生,你陪著这青年,是想到士狄维亭山区。去寻找他的母亲?”
端纳这句话一出口,连我也不禁“啊”地一声。他能说出这样的话来,自然是对一切底细全知道的了,不过他这句话,也是用四川话说的,文依来自然听不懂。
我用四川话回答(以下的和他的对答,全是四川话):“事情十分复杂。不是三言两语讲得明白的。”
端纳道:“不论如何,卫先生,我劝你打消这个行程,就算找到了他的母亲,对他来说,只有坏处,一点不会有好处,就让他做一个普通人,好不好?”
端纳竟然会发出这样的请求来。我道:“他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端纳摇头:“你何必为了自己的好奇而揭人之秘?”
我吸了一口气:“不是我想知道,他自己本身,也渴望知道。”
端纳道:“他不知道比知道好。”
我们在急速地对话,文依来的神情,越来越是焦急,他终于忍不住,叫了起来:“求求你们别用我听不懂的语言来讨论我的问题。”
我向文依来用力挥了一下手,示意他不要插嘴,又道:“或许你在听了我刚才所提到的复杂的经过之后,会改变主意?”
端纳像是毫无兴趣地摇著头。
我提高了声音:“你们 贵会,一直不知道笛立医生愚弄了你们。”端纳一听,陡然一震,失声道:“天,他掉了包。”然后,指著文依来:“他不是伦伦的孩子!”
“伦伦”是什么人,我不知道,猜想是文依来母亲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