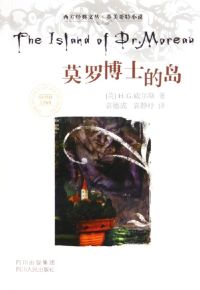熊熊燃烧的岛-第6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部长把一直拿在手中的笔记本放在口袋里,对工地发了预备信号。然后凝神看了一下莫尔尼亚。
“开炮!”
“是,开炮!”上校应声说着,并按下了电钮。
屏幕上地球仅仅看见一会儿。接着一切都消失了。
人们默默地望着空白的屏幕。
过了几秒钟,一阵可怕的火的旋风在工地上空疾驰而过。
中心控制室摇晃起来,它的一座墙倒塌了。克列诺夫、部长和莫尔尼亚都跌倒在地……
炮弹刚飞出炮口,就爆炸了!
过了一会儿,谢尔盖耶夫和上校站起身来,但是老教授弯折着瘦骨嶙峋的膝盖,伸长了青筋嶙峋的颈子,就那么仍旧躺在那儿。他抽搐地用嘴吸着气,脸色象死人一样苍白得发青。微微张开的眼皮底下只见眼白。
瓦西里·克里缅李耶维奇跪下,努力把克列诺夫的领子解开。
第八章 如愿以偿
在以代用品制造的炮弹试射失败之后,克列诺夫教授和瓦西里·克里缅季耶维奇一起回到了莫斯科。
克列诺夫过高估计了自己的体力,他打算帮助玛丽娜获取所需的镭-德耳塔的同位素。可是老教授一回来,就卧床不起,连自己的房门都出不来了。但他坚决拒绝进医院。
他不愿意袖手旁观,脱离共同的斗争。他把高度灵敏的无线电接收机对好“马特罗索夫的回波”,头上戴着耳机,躺在床上,日日夜夜地收听。
当然,本来他也可以使用扬声器,但是耳机使克列诺夫同周围的一切隔断,进入声音哨杂的太空世界。
克列诺夫知道在回波仪上没有他,也有人在值班,可是他怀着一个强烈的愿望,想第一个收听到他发明的反射被无线电发射机发出的信号。
克列诺夫没有拉开窗帷,因此日光几乎照不进他的房间。半明半暗中可以看到一张堆满了书、没有一点空隙的桌子。应该收拾一下,可是没有精力,主要是没有时间。圈椅、椅子、象棋台子……到处都堆着一叠叠买来后来不及看完的书。他有这么个规矩,没有浏览过的书是不放到橱里去的。现在反正连翻阅一下都来不及了。医生以后会安排好的……他会转交给图书馆的。因此,当他听完自己的“短吻鳄”讲完之后,就直摇头。
当克列诺夫侧身躺着时,他可以看到挂着油画的那面墙。还在美国时,他就开始收集这些画了。那时,他把一根根看不见的线伸向祖国,于是祖国对他就变得更近了。沃涅利克教授专门购买俄罗斯大自然的风景画,绝大多数是列维坦的作品。他获了多少心机才将它们预先寄到苏联啊!
特别是那些在蔚蓝天空的背景上树梢拂动、云缺飘浮的画面使他感到尤为亲切。
飞走了的云朵!……它很多年前就从生活中飞走了……而同它一起消失的还有爱的能力。
想想都奇怪,在大学生时代他曾有过很多挚友,他还作过爱情诗。究竟是什么使他变得令人难以辨认,变得如此孤僻,成了个禁欲者呢?
性格乐观、处于热恋之中、天真地梦想制止战争的克列诺夫在阿巴拉契亚山中发生爆炸时,已经跟莫德一起毁灭了。当摩托艇被日本潜水艇击沉,他连同他的幻想一起沉没在大西洋中时,他又一次遭到了段灭。
在海里被救起来的沃涅利克已成了另外一个人了。他改名换姓,一心一意对魏尔特保守自己的秘密。他假装成失掉了记忆力的人,重新开始生活。谁也料想不到,正由于这样,这个不同凡响的大学生才以一年半时间念完了康奈尔大学。他原来就已是位教授。于是不久约翰·艾伦·沃涅利克确实并不怎样费力就成了康奈尔大学的教授。谁也不知道,他在失去朋友和祖国、背着他腔想出来的为人类服务的十字架的情况下,在自愿的流亡生活中是多么的痛苦。
有一次,他出席一个科学家的代表大会。他怀着激动的心情跨上了欧洲大陆——俄罗斯离得多近啊!他在巴黎漫步,看着嬉戏的孩子们,心中在想,他们活着还得归功于他的善于沉默……他望着巴黎圣母院,走了进去,付给忙碌的修女一枚硬币,去欣赏阴沉沉的柱廊。离开时,他回首顾盼那直角的塔和装饰在建筑物正面的神秘的怪物雕像,想道:雨果使这一切出了名,而他以自己的沉默把它们保存了下来,因而失去理智的人类都能把巴黎连同它的艺术古迹一起炸毁,随风飘散……他向卢佛尔宫走去,象主人翁似地巡视着每间大厅。这一切的存在全仰赖于他。瞧,挂着天鹅绒帷帘的大厅,沿墙放着长凳。正中央黑色天鹅绒背景上,雍容华贵、优美绝伦的维纳斯女神的雕像引人注目……无论哪一件复制品都从未象这座雕像那样使克列诺夫产生如此强烈的印象,它的表面已稍稍留下岁月侵蚀的痕迹,然而雕像仍然充满了美和文物的魅力……它也是他克列诺夫为后辈保全下来的……尽管谁也不知道他,尽管谁也料想不到是他保全了这座雕像和其他的一切……他不需要赞扬和感谢!
不引人注目的、无人知晓的克列诺夫沿着巴黎的林荫道在喧闹的人群中徘徊,仿佛比所有的人都高出一头,他为他自己所负的使命和默默无闻而感到自豪……
现在看来,这是多么古怪而又荒诞啊!仿佛他与这个时代已相隔百年。一年前的此时此刻,他难道不是以同样的感情在莫斯科街上走来走去,为他用自己的沉默保全下来的那些富丽堂皇、高耸入云的建筑物而感到骄傲吗?一年前,当他读到宏传的建设规划的报道时,他难道不是曾经想象,他正在不露形迹地参加一切工作,保护整个国家和全世界免遭毁灭吗!?
究竟是什么东西使昨天的克列诺夫和目前头上藏着耳机躺在床上的克列诺夫两人之间似乎整整相隔一个世纪呢?
要知道,当他已经回到祖国,拒绝了许多对他的关切,被公认是个有点怪癖的老科学家时,心中总是似乎有条小虫在咬噬,感到痛苦不安。无论是成套的有好几个房间的住宅,无论是汽车或是照顾……他都不愿意要。然而在美国时,他曾享用这一切!而且沃涅利克教授当时也不古怪。就是说,在他身上良心还是发出了声音。只是他不愿去听这吱吱声,把它压了下去,他腼腆地拒绝接受起码的舒适条件,得过且过。他就这么做了违背良心的事!唉,如果能早些明白这一切多好!
教授辗转反侧,呻吟着。
为人类服务的虚伪的神殿崩溃了。原来,光靠沉默是不够的。他向下滑去……滑向犯罪的泥坑。要不是他的祖国新人们的热诚关怀和宽宏大量,他就会丝毫无助于人类……况且目前他也还没能有助于人类啊!如果马特罗索夫带来了镭-德尔塔,进行了炮击,扑灭了空中大火,那么克列诺夫就会明白,他并没有白话了。
日益衰弱的老人的最后的强烈而不可遏止的愿望集中在马特罗索夫的获救上。因此克列诺夫不摘下耳机,不愿听从什瓦尔茨曼医生的劝告,发狂似地收听着。老人固执地抛开一切疑虑,使自己相信,仪器很轻便,不需要电,马特罗索夫一定有办法传递自身的消息的。
只有热恋着的姑娘,只有克列诺夫那样具有全神贯注怪癖性格的人才能对马持罗索夫获救这种不可能的事怀有强烈的信念。
正因为如此,这位姑娘来到了克列诺夫这儿。
克列诺夫听到铃声,几乎有点感到高兴,医生是有钥匙的,这会是谁呢?
教授披上毯子,把喇叭打开以代替耳机,在半明不暗中拖着脚步,沙啦沙啦地走过去。
他把门打开,觑起眼睛。原来,甚至在楼梯口,就有白天、太阳,人们在生活、交谈、欢笑,高兴……
“我的天哪!是您!请原谅……请进来!嗯,是啊!……不过亲爱的,我冒昧问您,您怎么了?您仿佛是从十字架上被人抱下来的?”
玛丽娜苍白、清瘦,一个肩膀靠在墙上,站在克列诺夫的面前。
“嗯,是啊!……我的装束……我冒昧请您原谅。万分惊讶……同时很高兴。我们最可爱的医生说过,您病得很重。”
克列诺夫把玛丽娜带进他的房间。
“这是辐射造成的,伊凡·阿列克谢耶维奇,”玛丽娜微笑着说,“很难防护好。我们又获得了一种镭-德耳塔的同位素。可惜,”玛丽娜难受地微笑了一下,“它的半衰期为时更短。还没能作为防护层的形式把它加到超级电池上,它就已经消失了。”
“嗯,是啊!……是很严重,而且令人悲伤。看得出,您因为这些试验而憔悴了。没有保护好自己的青春。看在上帝的份上,请勿介意。嗯,是啊!……我想收拾一下床铺……”
“伊凡·阿列克谢耶维奇,可千万别这样。请您马上就躺下。瞧,我恳求您,恳求……”玛丽娜看了看克列诺夫,使得他只好蠕动着上下颌,听从地躺了下来。
“现在我拉开窗帘,开一会儿窗户。好吗?您有擦灰尘的抹布吗?”
“毫无疑问,抹布是有的。不过请别操心……这哪能,真的……您来了我就很高兴。”
玛丽娜很虚弱,勉强能站住,开始收拾起房间来。她不时坐下休息一会儿。
“可以把书叠到橱里去吗?”她问。
“嗯,是啊!……您要知道……这些书我还没翻阅完。好吧,算了,现在反正都一样。”
“为什么反正都一样,伊凡·阿列克谢耶维奇?”
“不,不……没什么……我指的是,您,我温柔的姑娘,怎么都行……您愿意叠到哪儿就请叠到哪儿。”
“伊凡·阿列克谢耶维奇,您这儿的画多么出色啊!您对绘画理解得真透彻。”
阳光洒满了房间,房中顿时改观了。
“当我把您的手稿搬过去的时候,我的手都在颤抖。要知道我学的就是您写的书,”玛丽娜含笑望着深受感动的教授说,“您愿意吗,我给您把茶温一温?”
“我将非常感谢,亲爱的玛丽娜·谢尔盖耶夫娜……同您一起喝茶,我认为是一种幸福。”
即使玛丽娜现在建议他吃他从未尝过的冰淇淋,他也会欣然应允的。
玛丽娜摇了摇头:“我给您煮茶,可我自己不喝,伊凡·阿列克谢耶维奇。您甚至都不会明白我的健康状况怎么样。辐射原来还会引起恶心……”
玛丽娜把电气水壶放上,又坐下来休息。
“嗯,就是……还记得吗,您是怎么答辩论文的?”克列诺夫说,“我要说,您那时是那样清醒、倔强……您确实把我给迷住了……嗯,是啊!……您原谅我,我极诚恳地请求,我戴着耳机。要知道我一直在听着、听着、听着……”
“伊凡·阿列克谢耶维奇……要是您知道,我是多么……”
“不值得感谢……真的……”
“不!我多么爱您啊”
“爱吗?嗯,是啊!……这多么奇怪……我爱……我从未听到过用俄语说这句话……我爱……难道可以爱我吗?作了那么多反对您的事?”
“伊凡·阿列克谢耶维奇,据说,心是不能解释的……”
“玛—申一卡①”克列诺夫轻轻地、一个一个字分开地说,就仿佛自己在谛听似的。
【① 玛申卡:玛丽娜的爱称。——译者】
“什么?”玛丽娜低声应道。
“不,我随便这么说说……我是个易怒的、爱嫉妒的老头。我羡慕您的父亲。我多么想有这么个女儿啊!或者孙女儿……因为您是可以作我的孙女儿的……我会这样地为您感到骄傲!……嗯,是啊!生活的安排是这样悲惨和不合理。大概,有孩子这是巨大的幸福?”
“巨大的幸福,伊凡·阿列克谢耶维奇!”玛丽娜立刻活跃起来。
她站起来,走到无线电机跟前,将她那只纤细的、几乎透明的手放在天蓝色的箱子上。她感到金属冰凉,急忙把手缩了回来。
“巨大的幸福,伊凡·阿列克谢耶维奇,”她继续说,泪眼模糊地望着远处。“有时我似乎觉得,我将很幸福……而有时……我是这样痛苦……洒尽了泪水……这些日子里,我比近十年来哭得还多。我可以坐在您床上吗?您的手多大……请告诉我,您难道不相信,您一定能听到信号吗?”
“我相信,玛申卡……我相信……我整个的生命现在都在这一信念之中了。在这之前,我认为,我要这个是为了人类……可还是为了自己……而现在……”老人闭上了眼睛,沉默不语了。
玛丽娜抚摸着他放在毯子上的手,温柔地望着老人那双颊塌陷、眼睛深凹、有一绺一绺白胡子的瘦削的脸庞……她抚摸着他的手,看到先从一只眼睛里,随即又从另一只眼睛里缓缓地流出两滴泪水。
“而现在是为了您而想要这个,全心全意为了您想要……并且感谢您用美好的感情唤醒了我心中的……您看,我流了泪,但我不感到害羞……上一次流的眼泪是属于莫德的。”
玛丽娜用她散发着




![燃烧的玫瑰[np]封面](http://www.aaatxt.com/cover/7/752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