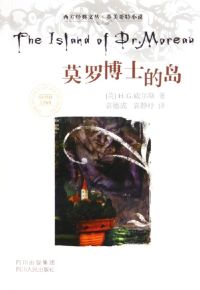熊熊燃烧的岛-第4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是的,我见过这样的人……我还能叫出他们的名字……科学界都知道他们。”
“他们之中有些人也没有考虑过他们的后果不亚于伯恩斯坦所造成的后果。公正地对待伯恩施坦,就应该指出,他的美国同行根本不急躁。”
“类似这样的杀人刽子手,我改说,您总还能再举出一些。只要考虑一下吧!有伯恩施坦,有我,还有许多我们的西方同行……我们大家原来比近视眼还要近视……无知得犯罪了!所以结果就……不是地球的原子火灾,就是地球的空气火灾!怎么办啊?”
老教授双手紧紧抓住了头部。他也许在思考,也许在同自己的头痛作斗争。谢尔盖耶夫注视着他。教授那不断变化的眼神一刻也没有离开过他的视线。他猜透了教授的某种心思。教授挺直了身子,他的背再也不弯了。接着,他站了起来。部长也站了起来:
“我们走吧,伊凡·阿列克谢耶维奇,去参加科学家的会议吧。已经快到九点钟了,”他说道,“您今天将看到您的许多同行,他们来自西方国家,来自中国、印度,来自邻近的兄弟国家……问题涉及到大家。那里也需要您。”
第十章 救生公司
玛丽娜怕马特罗索夫担忧,在信上什么也没有告诉他。但他却从妹妹克谢妮娅的来信中知道了一切。克谢妮娅坦率地将可怕的消息告诉了他。
马特罗索夫从信中只明白一点:他将永远失去玛丽娜,于是,请准了假,在收信后半小时,就乘飞机飞往莫斯科了。
三个小时以后,他连即将降下来的电梯也等不及,就三步并作两步地登上了十层楼,一面想象着躺在枕头上的那张疲惫不堪、洁净可爱的脸蛋,披散着的头发,半暗的房间,药味……
当他一看到前来开门的玛丽娜,一看到她那因快活而诧异得睁大了的眼睛和她头发中突然出现的一绺白发,就将她一下抱在怀里,使她幸福得呻吟起来。接着他抓住她的肩膀,把她推开一些,以便好好地看看,仔仔细细地看个够……
容光焕发的玛丽娜满怀喜悦地笑着,总想把脸埋到他的胸前。
娜佳向前厅瞥了一眼,把门关上了。她把双手贴在胸前,眯缝起双眼,站在餐室里。
玛丽娜身上发生了什么变化,德米特里无法立刻弄明白。她变得更加美丽,更加成熟,更加娇艳了……不,他不知道她身上发生了什么变化。啊!这绺白发使她起了变化,使她更美丽了。但他对亲爱的人什么也没有说。他象是怕失去她似的,搂住了她的肩膀,和她一起走进餐室。
机灵的娜佳悄悄地溜进了姐姐的办公室,闭着眼睛站在门边想道:“这多么不平凡啊!她是多么幸福啊!”
后来,他们,玛丽娜和德米特里一直在谈话,他们说得前言不对后语,没有条理地讲述一些琐碎小事,互相答非所问,就这么说呀,说呀,说个不够。而且,当然是接吻了。娜佳相信,至少是接吻了!那时,他们没有声音,娜佳的心儿收缩得似乎要停止跳动了。
“这不危险吗?辐射不影响你的健康?”德米特里不住地问。
玛丽娜摇摇头。
“他们已经用盖革-弥勒计数器①帮我检查过了,我没有危险。我并不发射伽码射线。”她笑道。
【① 盖革-弥勒计数器:可以计算各个荷电质点以及光子的仪器。——译者】
“我应该会会这位卓越的人!希望能握握他的手。我们生活中能得到的一切都要归功于他。”
“握手?”玛丽娜悲伤地重复一遍。马特罗索夫拍了一下自己的前额。
“你会见到他的。我们一起……现在就……到医院去看望他吧。”
“我可以和你们一起去吗?”娜佳从门后问道。
他俩没有带她一起去。她把她在这世界上最爱吃的块菌状巧克力糖强塞给他们,要他们转送给有病的医生。
他们步行前往。一面走,一面不停地互相对望,而且好象一路上什么活也没有说。不过,话又说回来,不是这样!马特索夫老是向玛丽娜提议做这做那,要不就是到商店弯弯买个什么小玩意儿,要不就是买点冷饮或者鲜花,要不就是喝点汽水。
玛丽娜笑着。
卖汽水的售货员向他们微笑,刚才还在对不听话的孙女生气叫骂的老妇人也向他们微笑。而那个约摸三岁光景的小女孩,还和他们一起走了几步,不时地瞟瞟他俩的脸。
他们沿着新阿尔巴特走到花园环行路就向右转弯。这里街道十分宽阔,没有走廊般的人行道。街当中排着一行等车的人。
玛丽娜感到城市的环境特别惊人地优美,好象她从来没有到过这里—样。她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德米特里,他惊讶地环顾了一下四周,接着就象害怕会失去时间似的,重又目不转睛地望着玛丽娜,看着她的侧面的身影,仿佛这倩影已永远铭记在他的心头,保留在他的记忆里,映印在他的想象中。总之,已永远镌刻在他马特罗索夫的心中,从此和他永不分离了。
起义广场的一幢大楼附近,有一座带圆柱的古老楼房,这大概出自一位伟大的建筑师之手。他们在入口处附近站住了。
“你把巧克力给我。”玛丽娜要求。
“以后我可知道了,你是个爱吃美食的人,”马特罗索夫说。他俩都觉得,他们互相说出了某件重要的、深刻的、对今后具有重大意义的事儿。
年轻的女医生已在等候玛丽娜和马特罗索夫了,因为事先已接到通知说他们要来。她郁闷地把他们带进一个特别的房间,为他们作了杀菌照射。这一对探访者一到小屋里,就悄悄地象小偷似地接起吻来了。女医生在送给他们白衣大褂时尽量不看他们,真的,小间里还是有一个小窗的啊!
马特罗索夫个头大,穿上了一件瘦小的白褂子显得格外可笑、可爱,显得分外强壮,逗得玛丽娜笑出了眼泪。
很快,三个穿白大褂的人走在高大明亮而又无人的走廊上了。地板上洒满了殷红的光点,这是透过挡住窗户的树叶照射进来的夕阳的余辉。
三人在一扇高大的房门前站住了。门毫无声息地打开了:有个护土站在门口。
“在等你们。”她轻轻地说。
“请吧,”女医生请他们进去,她好奇地望着在这医院里难得遇见的幸福的一对。
一股药味儿。马特罗索夫想起了他不久前经历的惊恐不安,更加感到这儿的宁静。玛丽娜望望德米特里,兴奋地朝他微微一笑,他尽量既起脚尖走路。
窗边放着一张白色的床。什瓦尔茨曼医生的头躺在枕头上,不戴眼镜显得有些异样,脑袋又圆又光滑,两鬓有一些卷曲的头发。
“您也许以为我不知道您把什么人带来看我啦?没有的事!这是马特罗索夫。”
“我带来了一个人,他想向您致谢……为了我。”
“好吧,可我还要为他感谢您呢!我已经恨我的同事了。他们除了我自己的病人以外,不准一个人来看我。你们可以想象,现在他在给我治病,规定我吃带髓的饮食,却又不愿告诉我,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自己却跑到部长那里去了。我素来说他是条短吻鳄。那么,年轻人,你们为什么要感谢我呢?不过,不必回答!我会根据沉思的脸色来诊断的,不过,你们别生气,我亲爱的。你们以为我成天不作声,连报纸也不看?”
“可我随身带来了,”德米特里说,“我猜到您对什么感兴趣。”
“您啊,我亲爱的!我的好人!让我用双手拥抱您吧。”什瓦尔茨曼看看自己的被褥大笑起来。
马特罗索夫被医生的这种目光,和对他们大概有点傻乎乎的脸色而说的这番话弄得十分尴拉,他急忙把话题转到当天轰动一时的消息上来。
“《巴黎晚报》六月十三日报道……您还一点都不知道吧?军火公司的老板魏尔特先生向太平洋的一个岛派出了一个考察队。某位伯恩施坦教授研究成功了点燃空气……”
“等一等,等一等!怎么点燃空气?我不明白。”
玛丽娜插话了:“空气是由氮和氧组成的。这两种气体的化合物至今都很难搞成,这就是燃烧空气。”
“太有趣了,太有趣了!”
“下面就不那么有趣了,”马特罗索夫接着说。“这位教授本人自我牺牲了。”
“牺牲?”什瓦尔茹曼医生悄悄地望了望玛丽娜。
“是的,他为人类牺牲了自己,在阿列尼达岛上点燃了空气。这个事件在一段时间里引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严重关注。这是伦敦的《泰晤士报》,罗马的《网报》,美国的《纽约时报》,他们都反复唱一个调子。科学家们都对燃烧空气的可能性的说法子以驳斥,他们断定这充其量不过是个骗局。总之,整整闹了五天。从七月十九日起,报纸就整版地报道别的问题了。”
“哦,是这样。七月十九日又是什么事儿喧嚣一时啦?”
“危机,艾萨克·莫伊谢耶维奇,所有的交易所一片混乱。”
“您大概认为这是新闻?”
“是多少有点儿新!报纸报道了交易所采取的不寻常做法,报道了大企业的破产,报道了魏尔特难以置信的投机勾当——他突然买下了在肯塔基的有名的马摩斯山洞。”
“依我看,应该在这一点上找找联系。”玛丽娜说。
“当然!联系是很明显的。他先是恫吓人民,然后就开始掠夺。我请你们相信,这是老的手法。我还记得,曾经有过这样的强盗,他们穿着白色肥大长袍,脚下安着弹簧一跳一跳,然后把吓坏了的过路人抢劫一空。”
“报纸上纷纷报道:所有的地下铁道,美国的地下铁道和有大隧道的铁路都已被魏尔特公司买去、大家都在问自己:这是什么意思呢?”
“是啊,真怪!”
“很多企业突然停业,美国已陷入一片慌乱之中。魏尔特甚至关闭了自己的军火工厂,取消了一系列国家的军事订货。”
“全是怪事!”
“这引起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张惶失措。不久以前,魏尔特还是那么希望接受他们的订货哩!千百万失业者涌上街头。同时,魏尔特又开始了某项宏大的工程。无论是德国,还是丹麦,还有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的报纸都报道了这个消息。他们指出,魏尔特对格陵兰岛表现了巨大的兴趣。”
“喂,马特罗索夫!我已经听腻了您那个魏尔特!”
“那有什么办法呢!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现在全在忙这件事。您忘了,他是许多垄断集团的头目!”
“他究竟想要干什么呢?我不懂。”
“谁也弄不懂。”
“这与太平洋的灾祸有着某种联系。”玛丽娜又一次指出来,她偷偷地向德米特里微微一笑。
“一切很快都会解决,艾萨克·莫伊谢耶维奇。今天,国外报纸通篇都在报道,正是这位当今的知名人物弗雷德里克·魏尔特博士将向全世界发表广播演说。”
“真的向全世界演说?”什瓦尔茨曼笑了起来,随即双眉紧皱。大概他感到疼痛了。
玛丽娜站起来为他盖好被子。
“是的,艾萨克·莫伊谢耶维奇。国外认为这个讲话具有重大的意义。谁都还没有一下子就对全世界讲过话呢!”
“不过,他是个美国人,喜欢一鸣惊人!您说,他会用英语讲吗?”
“是的,”马特罗索夫说,“但他演讲之后各电台将用地球上的各主要语种转播他的讲话。”
“象是一个很庞大的美国广告。也许,你们以为我会浪费时间去听他那资本主义的胡言乱语?没有的事!”
马特罗索夫的脸也变得阴沉了。
“不过,我认为,艾萨克·莫伊谢耶维奇,这会使您感兴趣的。”马特罗索夫从口袋里掏出了表。
“您看什么?我无论如何不会放你们走的!您已经给我讲了那个魏尔特的事……您最好说说我们这儿发生了一些什么事。”
“我们这儿,艾萨克·莫伊谢耶维奇,一切都很平静。昨天进行了最后一场国内的足球锦标赛。全苏电网七月十五日开始送电。这个电网现在连接了西伯利亚、伏尔加河和第聂伯河的动力系统,与此同时安加拉工程的涡轮机也开始运转了。库尔斯克冶金工厂的第一座高炉出铁。格里尼奥夫教授昨天出示了一匹没有心脏的马,在马鞍的位置上安装了一个空气压缩机以代替心脏。格里尼奥夫教授骑着他的马在练马场绕了两圈之后,马死了。电线断了。”
“可惜,可惜!这很有意思。您为什么不一来就讲给我听呢?
马特罗索夫又看了看表:“今天,七月二十一日按中欧时间六点钟,通过广播,魏尔特将向全世界发表演说。”
“现在儿点钟了?”什瓦尔茨曼问道。
“差一分钟八点。”
“那您为什么不早对我说明?啊,多可惜!也许他还没有讲完?”
“他还没有开始呢,艾萨克·莫伊谢耶维奇,有两小时的时差。再过一分钟就要开始了。”




![燃烧的玫瑰[np]封面](http://www.aaatxt.com/cover/7/752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