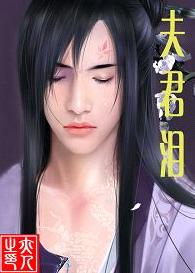帝宫岁记(女尊)-第1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颜莘放下手里的参汤,连带汤匙一起递还给他,又看他一眼,微微笑道,“这些事情,可跟朕的洪福没有关系。”
温敢言双手接过,笑道,“然而陛下爱惜百姓、励精图治,又怎能不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呢。”
颜莘忍不住笑了出来,道,“你呀。”却伸出一手揽在他腰间,将他挽到怀里,道,“你母亲为人嫉恶如仇,眼里半分沙子也揉不进去,即便是对朕,也没什么畏惧回避的,真是叫人讨厌得很。不想却有你这么乖巧懂事、惹人喜爱的好孩子。”
温敢言忙顺势倚过去,应声笑道,“谢陛下夸奖。”
颜莘这边看他如丝媚眼;如花笑靥,娇俏地立在面前。眼里不禁晃过柳臻的娇柔温润,心下便是一疼。
温敢言见她再没说话,便早已猜到了几分,却只装作不知。然而后来见她若有所思般,迟迟不肯再说话,便一面看她脸色,一面小声谨慎询问道,“陛下……是不是又想起柳昭林了?”
颜莘被他打断了思绪,只愣了下,却丝毫不想掩饰,轻轻地点了点头。
温敢言眼见她守了自己,心里却依旧惦记着柳臻,便不免生出了几分酸楚。然而他毕竟修养到位,便只忍痛道,“柳昭林……也是诚心思过了。陛下也该多疼他一些。”
颜莘摇摇头,缓缓道,“你不明白。别人制造的痛苦,朕尚且可以承担得起。他的……朕真的承担不起。”
温敢言几分似懂非懂,却也不敢再问,只得点了点头。却看了看时辰,笑道,“更深露重,陛下还是保重身体要紧。臣侍服侍陛下早些歇息吧。”
颜莘看他一眼,轻轻“嗯”了一声,却有几分苦涩道,“柳臻……若是有你一半懂事就好了。”
又是一个柳垂金线、桃吐丹霞的夏初。时光就在期待中缓慢而飞快地流逝了。
晚间,柳臻再次躺在文源阁的榻上,心里却另有打算。
这一个晚上,他在她身下婉转承欢,放弃了所有抵触,对她的粗暴和敌意不予丝毫在意,却仍旧不忘时时处处讨她喜欢。
然而颜莘一翻身下来,不待她开口叫人,他便勉强撑起酸软的身子,伏身到她身旁,抬头虔诚看她,道,“陛下,臣侍……有几句心里话想跟您说。”
颜莘披上睡袍,只蹙了蹙眉,斜倚在一旁靠枕上。却偏去了目光,看也不看他一眼地道,“说吧。”
“臣侍……臣侍知道自己犯了大错。”柳臻不顾她一脸的漠然,只满心诚恳地道,“但是臣侍……也反省了这么多日子,早已经把错处都想清楚了。”
见她不语,他又掂量了措辞,道,“也是因为臣侍年纪小不懂事。并不是成心要惹您生气的。”
“臣侍……保证这是最后一次。以后便再也不敢犯了。”柳臻满心希望地看她,道,“您便再给臣侍一次弥补错处的机会,好不好?”
“柳臻。”
只这两个字,他心里便一沉。
自从出了那件事以后,好像总是在回避什么似的,她便再也不肯喊自己“臻儿”了。偶而不得不叫他,也只是连名带姓的叫。
他有些担心自己刚才那准备了很久的一番话算是白说了。
果然听她冷冷道,“你这话说得好似是朕把事情做绝了,不肯给你什么机会了。”
她看他一眼,却完全不想详细去解释事情的来龙去脉和自己的难过,只淡淡道,“你并不是什么年少无知。你只是兴致使然。仗着朕喜欢你,便大了胆子叫朕这般的刻骨铭心。”
言毕,她起身,唤了声“元遥”。
她起的快,柳臻反应得更快。
他虽然还没来得及想清楚她话里的意思,却早已飞快地随她翻身下地,“扑通”一声跪到她身侧,牢牢抱住她腿,止不住便是泪眼婆娑地道,“您……您打臻儿吧……您打臻儿一顿就能消气了……”
元遥应声进门,他也只作不见,哭声却越来越大地道,“臻儿真的知道错了……您便再给臻儿一次机会……臻儿定然好好改过……”
见她不语,却也并未动身,他想了想,又哭道,“陛下便是臻儿眼下活着的全部……您不要臻儿了……臻儿实在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再活下去……”
这句话总算是戳在她心上了。
毕竟是先前自己那么心尖尖儿上的人,话说到这个地步,凭她有多决绝也再难坚持下去了。
颜莘低头看他,见他□地委顿在地,小小的人儿哭得一抽一噎的,却还仰着脸一脸委屈地看着自己,要多可怜就有多可怜。
她便再也板不住脸,只得叹了口气,伸手从榻上扯下睡袍将他裹了,又弯腰将他从地上半揽半抱地扶起,这才挥手叫一旁怔住了的元遥退下。
等到扶他在榻上坐下,颜莘便拿起身边绢帕给他轻轻擦了擦脸,放缓了语气道,“好了。别哭了。”
柳臻怕再哭惹她心烦,忙敛住了哭声。一时却掩不去呜咽,又不敢在她动手之前先往她怀里靠,只得蜷在睡袍里浅浅地抽泣,双肩无声地抖动,单薄地叫人心疼。
颜莘心里纵然抵触,却也架不住他这般叫人柔肠百结的委屈。便又叹了口气,替他轻抚了抚背心,帮他顺气,这才真正柔了声音道,“好了好了,不哭了。”
柳臻又哽咽了几声,才渐渐顺了气息。
“朕去沐浴,你先睡吧。”颜莘实在是不想和他再多说什么,只一面起身,一面道。
柳臻诧异地抬头看她,泪眼迷蒙中带了几分欣喜道,“您……肯留臻儿了?”
“你忙了这半晚上,不就是为了这个么。”颜莘直白戳穿他,语气却依旧淡淡地道,“睡吧。朕很快回来。”
言毕她便转身朝后面走。
不想身后柳臻却只犹豫了一瞬,便喊了声,“陛下”。
她顿住了步子,却并未回头,也没有接话。
“臻儿……知道……”柳臻依然有些哽咽地道,“您……待臻儿的好……臻儿一辈子……也报答不了……”
颜莘只怔了一瞬,便仍旧一言不发地去了。
夜已深了。外面月色正浓。屋子里被透窗而入的月光照得明亮,叫人心绪萦回。
颜莘侧身,去看自己身旁卧着的人。他安稳地熟睡,双睫也早已不再沾染丝毫萦泪,只略咬紧嘴唇,脸上甚至还有几分释然的浅笑。
她实在是忍不住为这人的没心没肺有些失笑。
也难怪,他还不过是个孩子。快乐与忧伤,之于他,不过是过眼云烟。当时之痛,终究不会像自己这般如丝如缕地铭刻于心。
她起身,披了外袍,轻轻地推开外间殿门,示意几个守夜的宫侍不需服侍,只自己一个人站到廊下。
月光之下,院子里有树的地方都是树影婆娑。穿透树冠而出的那一丝丝暧昧不定的光亮,好像什么人明净的眼眸,清凉中又带了几分深情。
院子一角有几株杏树。时值初夏,早春盛放的花朵早已全落,只留一片稠密翠绿的叶子,在月光下轻晃,好似自己的被践踏而过的心,摇曳不定。
她不是那种善于悲春伤秋的人,然而独立静静立了好一阵子,最终却依旧摇了摇头,转身回去。
外间的明月,依然漠视着人间的悲欢,漠视着夜半醒来、情谊阑珊的人。
眼看快要天明,颜莘早早醒来。回头看身旁的柳臻还在睡着,便也没去吵醒他,只自己轻了动作起身。
不想她一动,柳臻竟也醒了。他并没有像以往那般继续赖在床上,反而忙着翻身起来,抱歉道,“陛下,是臣侍起得迟了。”
颜莘从未想到他竟也会有早起的时候。虽然心里多少有些诧异,却一语不发。
柳臻只给自己简单收拾洗漱了,便过来帮忙伺候颜莘洗漱更衣。他多少看出了她脸上的异样,便一面忙着,一面小心地笑着解释道,“臣侍先前是不懂事。如今早已改了懒惰的性子。陛下就不用再顾着迁就臣侍了。”
颜莘透过镜子,看他一脸的踏实。
屋子里的人大都端了东西出去了。柳臻见她心情还好,便趁无人,小心询问道,“臣侍白日里可不可以……像以前那样……过来伺候着?”
颜莘看他许久,轻轻点了点头。
看朱成碧思纷纷1
柳臻只在文源阁重新呆了三天,便发觉今后的日子比先前要难过得多了。
首先,文源阁允许他涉足的地方不再包括内书房。
这一方面是因为先前他被纵容可以随便出入的时候,曾经带了来路不清的外人进入过的缘故。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本来这书房也就是不允许有人在她不在的时候进入的。
好在能不能进去对他来说,原本就是无所谓的。因此他也没有太多的不适意或是不舒服。
他本来就从来没有在意过那里是什么样子的,何况也没有什么东西是他想要的,所以不去想这事儿甚至将它遗忘,都不是什么费劲儿的事情。他在乎的,只是能在她在的时候,过去上杯茶,或是送些东西,看她一眼,在她身边陪上一阵子,也就足够了。
其次,不论他在文源阁呆了多久,一日忙下来有多累,除去该当他侍寝的时候,晚间他都必须要回到广内宫安歇。
毕竟没有皇帝的特殊旨意,代表他身份的册子也好,他的一应待遇也好,都仍旧归属于广内宫。他本人,也自然完全不能算是文源阁的人。
这个他努力了几天,发觉自己也可以接受。毕竟这其实与先前容千青的待遇完全一致。无论如何,总是与他人不同,叫人艳羡的。
唯一叫他难以接受的,也是他感觉最明显的,便是她对待他的态度,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比起肉体的疼痛,这种精神上的折磨更加叫他难过。
其实面对自己的真实情感,他虽然不会再那么幼稚,那么天真,然而也仍旧会随着她的喜怒哀乐,沉浸于忧伤或痴迷的纷扰中,失神地遐想着,期盼着。
她眼里滟滟的笑,无意中伸手的动作,都常常会叫他心旌摇荡。然而当他发觉那一切都不属于他,他苦楚哀伤,而又心痛。
曾几何时,他发觉自己不知不觉间,变得敏感,变得容易伤怀。他会去在意她的有意无意的言语,她的若有若无的安排。仿佛她的一举一动都主宰了他的呼吸,他的命运,意味了他还能否有信心撑过下一刻。
而那一天,这种折磨达到了极致。
二公主回宫的那一天,是一个雾气弥漫、久久不肯消散的早上。一改或大雨滂沱、或艳阳高照的放肆的盛夏,天气阴沉得叫人心烦。
他从凤栖宫晨省回来,又去了承明宫看了惠侍君,便急匆匆地往文源阁赶。一路上被这一片迷朦搅得莫名地心烦意乱。远近的景色若即若离,叫人好像在潜移默化中产生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留恋,却又因为透出的冷意而敬畏和远离。
就好像是受过伤的人,徒然有着温柔的外表,却掩饰不住强硬的心态,永远不会让人再走进心里。
他不需要通报,就进了文源阁。然而不待走进内殿,便看见门口守了几个自己从来没有见过的人。他便知道里面该有客人。
他仍旧没有却步,一直朝里面走。直到进了内殿,远远冲坐在上首的颜莘行了礼,便立在一旁,稍稍抬头却又不失礼仪地简单打量了一下下首坐着的人。
那人眼瞅着二十四五岁的年纪,也是该有儿女的岁数。样貌虽不是十分出众,却也是俊俏漂亮的。一身的富贵挺阔之中,却又不掩婉约雅静。他穿了一身大红滚芙蓉色边儿的软绸直身长袍,袖口有葱黄色盘金镶边儿,设计得十分精致。
柳臻是知道京城显贵家中夫侍着装规矩的。一眼便看得出这位身着大红正装的也是位正房夫君。只是颜莘无意给他介绍,他也只能自己在一旁暗暗好奇。
他是从没见过这位皇帝最宠的燕郡公主的。同样的,颜映亦也完全不认识柳臻。自打柳臻进门起,他便一直把他当作是文源阁的宫侍,不过料想可能只是个品级高一些又得宠的,不用穿宫装罢了。
然而颜映亦是从小便得颜莘喜欢的。又嫁得了算是位极人臣的妻主,富贵自在得要命。自打颜莘登基以后,他更是如鱼得水,肆无忌惮地一发不可收拾。
先前为了他腊月违禁入宫,和温敢言的母亲温棠发生争执的事情,颜莘好一顿不高兴。然而却心疼他,不舍得直接说他,却叫了他妻主路静柏来好一顿训斥。结果倒仍旧惹了他一个老大不高兴,闹起了小脾气,近半年了都不肯再入宫请安。
好在颜莘也一直忙,无暇顾及他,倒也没觉得怎么样。
如今他在颜莘面前虽然没发牢骚撒娇,却也明里暗里没少指派温棠的不是,继而便表达了希望颜莘疏离温棠的儿子温敢言的要求。颜莘自然把他这些话当作笑话听了,却把一旁不明就里的柳臻弄得心里发紧。
二人闲话了一阵子,颜莘又安慰了他几句,便叫柳臻重新给添上茶。
原本柳臻便是品级并不算低的侍君,只要伺候颜莘就好,是不需要给客人上茶的。如今这规矩也改了,显见她是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