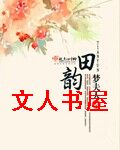田韵-第15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董嬷嬷和荣嫂子一前一后的掀起帘子,脸上露出喜色。
“给宜人贺喜,给亲家太太贺喜,给两位姑娘贺喜,咱们府的两位公子,这次在京中都榜上有名,京里有人过来报喜了。”
雪梅和刑氏对视了一眼,露出欢喜之色。
“快……”董宜人大喜过望,急忙让报信的人进来。
报信的人,是叶家的家生子。为人极是伶俐,便将京里科举过程中发生的事情大大小小事无巨细都给讲了一遍。
当满屋的人听到姜恒中了头名解元后都是齐声恭喜。
“那快说说阿鸿是第几名?”董宜人刚刚只顾得高兴,却忘记了这京城中只能有一个解元,如果姜恒中了解元,那么叶秋鸿又是何位置?这叶秋鸿的学问按理来说比姜恒还要强上一两分哩。
董嬷嬷看了一眼荣嫂子。见到她垂着头,乐滋滋地数着宜人赏的铜板,便暗地里撇了撇嘴,上前一步道:“回宜人,鸿公子中的是第十名举人,也是一甲之内哩。”
董宜人长吁了口气,拍了拍胸脯。这满京城光科举的举子们就上千,要想在京城中考出好名次是非常难的。主要是因为路途太远,有些举人们秋闱时科举便来不及参加明年三月会试,所以就有很多把握比较大的生员们,提前到京城应举。在京城应举可以不用考虑原籍贯,只要拿着路引和当地官员所开的凭证既可。
而京城本地的生员们则是必须回京城应试。
当然。如果路途过远,比如随着父母去广西任职的官员子弟,便不在此例之内。
而叶秋鸿和姜恒,因为身在中原,离南京只有半月路途。就只有回京城应试这一条路。
如今俩人都得了好名次,怎不叫人欢喜呢?
“恭喜宜人,贺喜宜人……”满屋的吉祥话如同不要钱似的堆到了屋檐之上。
院外,叶管家正喜气洋洋地命令仆役们将大红灯笼高高地挂起。
“给我仔细着点,这可是京城头名解元,可是从咱们府出去的……”叶管家的嘴角几乎要咧到了耳根,站在梯子下面指挥着众仆役忙碌。
“你们也别在这呆着了,既是阿恒中了头名解元,你们身为外家也理应庆贺起来。我就不留你们了……”董宜人看到了同样一脸喜色的刑氏,笑着道。
“喛!”刑氏喜得不知说什么才好,只会胡乱的点头,她袖子里的荷包早已空空如也,里面藏的赏银早散个干净。饶是如此,她看到哪个人没得她的赏银,恨不得把身上的衣裳脱下来赏给别人,也好叫别人知道知道她的喜悦。
“解元公啊……”
刑氏一想到这三个字,就幸福的头发懵。
听到董宜人说让她回家,点了个头就往外走,结果走得急促,一头撞到了柱子上。
雪梅急忙上前扶住,想笑又不敢笑,憋得要死。
……
叶府书院的气氛和知府衙门相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个是欢快,一个则是阴雨密布。
书房外面的相明和子侍,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噤若寒蝉。
“你说,你为何要如此?”姜恒痛苦的看着叶秋鸿。
叶秋鸿则是风轻云淡,毫不在意,“什么如此?不知你在说甚?”
“阿鸿,我看过礼部外墙张贴的卷子了……”姜恒蹙紧了眉头,深深吸了口气,“这和你往常的水平相比,简直不值一提,你为何要故意藏拙?”
“藏拙?何意?”叶秋鸿嗤地一笑,“只听说有人打得头破血流争当解元的,却没有见过解元公来责怪别人卷子写得不用心……”
“你干嘛要让我?我不要你让!我要公公平平堂堂正正的和你比上一场!”姜恒用力捶了捶胸,眼中泪如雨下。
“奇了怪了,这解元公居然还可以让?真是头一次听闻。”
听到屋里传来的声音,相明和子侍骇得面色青白,不约而同的向院门处挪了挪脚步。
……
……
ps:
《种田不忘找相公》一句话简介:相公,我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你跟村头的那块地,都被我承包了!
正文、第207章 农为国事
姜恒深吸一口气,直直地看向叶秋鸿。
“我本已做好屈居你之下的准备,甚至能想到你今年的文章定是能大放异彩成为千古佳话。可是未曾想到你这篇八股做得不偏不倚不温不文,竟是叫人挑不出一点毛病来。”
叶秋鸿闻言嗤地一笑,“你这人倒也是真奇了,八股就是八股,难不成我竟还得写一篇策论上去不成?”
姜恒一噎,面上换了表情,露出愤怒来,“你三岁就请先生开蒙,读的是《四书》、《五经》,十一二岁就能讲书、读文章,伯父又亲自教你做“破题”、“破承”、“起讲”、“题比”、“中比”成篇。你资质高,记性又好,一篇制义做下来花团锦簇,令人爱不释手。怎地你此次的文章便做出一个‘四平八稳’来?竟还不足你十二岁时的文采?”
叶秋鸿笑了笑,颇有些不以为然,“想必是临场发挥得不好,你也知道,那棚子里抬出来昏厥的可不是一个两个,我这几日身上有些不耐烦,能坚持着写完已是不错了。”
姜恒看他如此漫不经心,不由得气恼,“伯父伯母还盼着你中状元呢,若是让他们知道你考得不好,岂不是叫他们伤心?”
听到姜恒提起了父母,叶秋鸿脸上突地露出一丝伤感,却又转瞬不见。
“若是……让他们知道你是故意考得不好……该多难过……”姜恒说完这句话,便转过脸去,默默流泪。
他不是木头,在知府后院受到的冷落让他知道了自己的身份,所以他更加倍的努力,希望能在学业上有所建树,将来中举中个进士,也好养活家里人,也好让自己身边的人不受人欺负。
可他从来没有想过中解元。在他的眼里,解元应该是属于叶秋鸿的。
论文采,他比不过叶秋鸿,论制义他更比不过……
可是。怎么解元公就落在自己头上了?
若是别人中了解元只会狂喜。
叶秋鸿是他的兄弟,是亲兄弟。亲兄弟中,财产可以让,衣裳可以让,甚至就连女人也能让,可是这功名却不能让。
功名?
想到这里,他蓦地转过头,看着表面漫不经心的叶秋鸿,一股悲凉涌上心头。
此情此谊,他拿什么来还?用什么来还?
“若是会试之时。你再如此,我宁愿一起落第回家,同做田舍翁。”姜恒正色道。
叶秋鸿原本笑嘻嘻的,可是看到姜恒面色严肃,不由得也严肃了起来。
八月的窗外。一团团金黄雪蕊在阳光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折桂是一个好兆头,所以很多人的书房外都会种几株桂花,为的便是蟾宫折桂的寓意。
一阵风吹过来,树枝轻轻摇晃,清香四溢。
俩人都不说话,一同看向窗外……
敬民这一段在京城的日子可谓是如鱼得水,杨大学士对他极为看重。派了府里的一个外事管家跟在他的身后,天天听候他的命令。
敬民是一个厚道人,性格又好,人又听话,每日早出归晚的在‘杨大学士府的田里’劳作。虽说田里的农活不需要他做,只需要将经验传授给几个经年老农就好。可他觉得自己本来就是一个农夫。做田里的活那是天经地义,便时常和人抢着干活,后来被杨府的外事管家略略提点了几句,这才不下地。但是若是有人来问他问题,凡是他知道的一概传授。
敬民虽是只跟着雪梅学了不到一年。可是雪梅那是跟着老师学出来的,在全国也是拨尖的农业人材。只教一个敬民那是绰绰有余,虽然后来也教了顾二虎和重山,也不过是多费几句口舌罢了。
敬民的农业技术和现在的农夫相比,绝对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就光那一整套的精翻细作就让所有的农夫全部傻了眼。
尤其是当他们听到敬民家里的产量最高亩产达到了五石左右,更是睁大了眼睛细细盯着敬民,不舍得放过他任何一个动作。
尤其是种子培育技术,更是令人咂舌。他们根本就想不到,单单只是培育一个高产种子,会费多大的力气。要在田里选择产量最高的那一株,不仅产量要高,还得颗粒饱满。这些还不算,还得把它们给分出公母来,公母相交才可以培育出高产种子。
这个在后世人人都知道的人工授粉技术,在明朝就是天书。
直让那些经年老农看得眼花瞭乱,直呼开了眼界。
杨大学士喜爱他为人厚道,再加上又知道他是姜恒未来的大舅子,也不愿过于埋没他。下了个手令,将他安排到户部管粮食的粮科做了一个不入流的知事。
虽然每月只拿五斗米的俸,可是好歹也是吃上官粮的人了。
这个消息随着姜恒和叶秋鸿中举的喜讯一起传回了刘家,令南河村的村民们羡慕不已。刘家居然有人当官了?虽然是个吏,可是好歹也是京城的吏啊。
还是管粮食的。
天大地大,粮食最大。
一时之间,刘家人在南河村风头无两。
就连顾二虎和重山在村子里,别人也得敬他们一声哥哥。
敬民虽说是管粮食的知事,可是粮科里的事情他也弄不清楚,他还是愿意去田里和农夫们呆在一起。粮科里的那些知事干事都是有学问的人,和他们在一起说不了三句话就犯晕。
再加上他性格单纯,实在不合适在衙门里办公。
万幸,粮科里的人也都知道他本来是干什么的,倒没分派给他事情做。他虽说是在粮科里做事,可是一天倒是有一大半时间在田里。
要说敬民没脑子那也是假话,他天天往田里跑,如果说不知道去的地方是皇庄那真是做假。那几个老农莫看样子是农夫,可是个个身上都有官职,不是博士便是知事。
可是没人告诉他,他也只装作不知道,每日乐呵呵地和几个老农谈论农事。
这一日,他粮仓里教几个老农如何对种子进行增产培育。
“……这种子下地前先洒了农药。成苗后抗倒伏能力就强些,而且更抓土,根系也旺,最重要的是一些幼苗期常见的苗病就少出了……”
敬民一一列举了幼苗期苗株会出现的各种病症。以及如何利用农药将这些病症给杀死在萌芽状态。
他一边说,那些老农手里拿着炭条在记录。
说到兴起之处,竟是都未曾发觉粮仓门口站了几个人。
中间一人三绺髭须随风飘动,身穿书生们常见的宝蓝缎直裰,脚下粉底皂靴,头戴方巾,看起来和普通人没什么分别。只是从身后众人对他的恭维和畏惧感来看,此人必是身在高位。
那人站在粮仓门口听了一会,满面笑容,不时的点头。显见得是听到心里去了。
又站了一会,见到里面的人依旧是谈兴正浓,身边的一个侍从模样的人忍不住了,要进去唤人。
那人连忙阻拦,“莫要惊扰。且让他们说去,我们先走吧……”说着便悄悄抬腿,如同来时那般,静悄悄地离去。
从来到走,粮仓里的众人没一个发觉的,都在聚精会神地听着敬民讲课。
侍从低头随着那人慢慢离开了粮仓,心里却不停的叹息。怪只怪姓刘的这个小子没好命。竟未能得见天颜,不怪他没将事办到。
敬民不知道,他这辈子唯一一次和皇帝见面的机会,这样的开始,又以这样的方式结束。
他唯一知道的是,晚上回去应卯准备下班回家时。粮科里的知事们待他突然热情了起来。
“小刘,下班呐?”因敬民不是读书人没有字,那些知事们不好以名字称呼他,便直接唤他的姓。
“几位先生好,你们也下班呢。”敬民躬着身。一一的施礼。
“嗯,下班,下班……一起走?”几位知事笑盈盈地,递过了橄榄枝。
一位姓吴的知事,已经半白了头发,此时走在人群最前例,招手唤过了跟在最后的敬民,亲切的和他说话。
“田里辛苦吧?”
敬民颇有一些受宠若惊,急忙答道:“不辛苦,不辛苦,在家时就是做的这个,惯了……”
“听说,你家搞的那个种子,能亩产十几石?”吴知事皱了皱眉头,问道。
“啊?”敬民连连摆手,“吴知事这是哪里听来的?是亩产三到五石,哪里有十几石啊?这可吓死人了。”敬民一边说,心里一边思忖,怎么今天这些知事老爷们都变了脸孔?一个个都亲热了起来?
听到三五石,吴知事脸上的表情轻松了起来,冲着身后的众位知事笑道:“就知道是家中的小儿信口雌黄,这世上哪里有亩产十几石的种子?必是小儿们听差了!”
说了这句话,不等身后的从知事们回话,便又转向了敬民,亲亲热热地道:“小刘呀,你来了粮科有小半月了吧?咱们还没有一起聚聚,今天我做东,大伙去南来楼给你接接风……”
敬民愣了愣,露出迷惑的表情。
吴知事却不等他反对,执住他的手,携着他往粮科大门处走去。
一边走,一边问道:“小刘呀,你来和我说说,这上田能产几石,下田能产几石……这湖广地力丰厚,每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