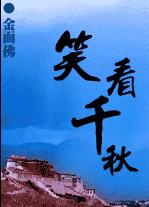笑看千秋-第5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谁要能回答就好了,起码说明我找到了同样穿越来的难友。
“这是我以前的家里请的先生说给我听的,清儿驽钝,居然从来没有想过问她是什么意思。”
“你以前的先生想必也是个很特别的人。”他点了点头,不知褒贬地评价道。
我笑了笑,不置可否。第二次从他口中听到“特别”这个评语了。
“还有其他的吗?”他兴起了意味,“你的师傅有没有教你其他的诗歌,这样的。”
“有,怎么没有,她说在她以前生活过的地方,是不喜欢作律诗绝句的。他们认为的诗就是这个样子的,你听着‘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这可是一首很有名的诗。虽然我表示很明白它的意思,倒也很喜欢。”
“我好象听懂了。”他笑,眼睛沉沉地盯着我。我没有回应他的话,平静地看着窗外。
清风拂动,纷纷扬扬的落叶,一片一片,蝶儿蝶儿满天飞。
我想起了纳兰容若的词,转头对他笑笑,“我写首词给你看好不好?”
见他没有反对的意思,就着他办公的纸笔,刷刷刷地写下:
谁念西风独自凉
萧萧黄叶闭疏窗
沉思往事立残阳
被酒莫惊春睡重
赌书消得泼茶香
当时只道是寻常
纳兰容若虽然号称“清朝第一词人”,他的词,我喜欢也不过只有最后的这句“当时只道是寻常”和那句着名的“人生若只如初见”。然而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多的是在时间长河中湮没的人,能够在史册上留下一笔,已是极好极好。
“你可不可以不要这么忧伤。”他叹气,起身抱住我,下巴上的青茬轻轻摩挲着我的额头,麻麻痒痒。
是他误会了,还是我误会了。我不知道任何开口宽慰他也宽慰我自己,只好任凭他抱着不说话。
远和近
“王爷,蓝妃娘娘回来了。”王爷的侍从有着视而不见的魄力,改天试着劝劝灵妃美人跟他学学,眼睛要会自动过滤自己不想看不能看不该看的东西。但如果她爱他,那么我的规劝就没有效果了。爱情是世界是最没有道理的东西,我们只能把它归诸于上帝和女娲造人时的失误,或者是前世的罪孽。因为这样东西,无法解释,也只好推给前世,明明没有道理可喻的感情,偏偏这么多。
等等,这个蓝妃又是谁?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
楚天裔松开我,对侍从点点头,“你叫她进来见我。”
回头见我想避开,喊住我:“不用回避,你们姐妹以后会常见面,不是生人。”
我踌躇了一回,点头应允了。
见我不是很乐意的样子,他又加了一句:“洛儿是个很好相处的人,你会喜欢她的。”
“像你一样喜欢?”我大着胆子问。
“不错。”他笑,“总算咂摸出三分酸意了。”
“无聊!”我忍不住淬了他一口。
“表哥!”清清脆脆的嗓音伴着清爽的香气一阵风似的卷了进来。芙蓉面,冰雪肌,杏黄色的衫子,细细长长的笑眼。眼睛滴溜溜的,一落到楚天裔身上,全化为了缠绵的柔波,波光荧荧。有些人是天生的笑脸,(奇*书*网。整*理*提*供)即使(他她没有明显的情绪,你也会觉得他(她)是在微笑的,真心实意地微笑。不同于我的堆砌。
“你回来了。”相教于女孩的柔情似水,缱绻万千,楚天裔的回应就平静的多,礼貌而疏离。
也许是顾忌我在场的缘故。
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如此不受欢迎。
我咳嗽一声,准备开口请辞。女孩先说话了。
“你就是清儿吧,表哥一早就跟我提过你,可惜你来的时候,我生病了,去外面静养,到今天才见着。”
“没大没小!叫姐姐。”楚天裔白了她一眼,转向我,“清儿,这是洛儿,我母家的表妹。”宠溺的表情确实像是在看一个小妹妹。
我忽而就微笑了,过去捉住她的手,转身望着他,道:“你说的没错。我确实很喜欢她。”
像地窖里苍白的番薯喜欢阳光下娇艳的鲜花一样喜欢她。
我一直以为,女孩子只有眼睛大才好看,却不想世界上还有一种女孩天生适合笑眼,就像《东京爱情故事》里的莉香,一笑,眼睛就成了弯弯的月牙。清甜的,纯净而美好。二人转很快变成三人行,伊若与蓝洛儿极为熟稔,算起来,她要叫洛儿一声“姑姑”。我只是略微有些奇怪,为什么以前她从来不曾在我面前提到这个人。
也许我把小女孩的世界想的太简单了。
现在的我看七年级生,一定会觉得他们只是一群什么都不懂的小孩子。可是当年我脱下红领巾的时候可是认定了自己是大人的。
没有谁的世界是一张简单的白纸。
洛儿是个极美的名字,总会让我想起曹植笔下的洛神宓妃,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还有洛城,繁华美丽,承载着我温馨美好的回忆的洛城。然而这个名字难以配姓,无论多尊贵的姓氏配上她都有一种唐突佳人的亵渎。
幸而“蓝”这个姓氏是不错的。堪堪足以匹配。
蓝家的权势也适合她的身份。
楚天裔没说错,我会喜欢她的。
当今太皇太后的侄孙女,楚天裔的表妹,伊若公主的表姑兼姨娘。
没错,蓝洛儿也是楚天裔的妃子。
古代普通的农户倘若碰上丰年也会纳上一房妾氏,以喜上加喜。相形之下,当今皇帝的御弟,中土王朝的二王爷只有五位妃子,着实可以算是寒碜。搁现代,估计可以视为对亡妻一往情深的新好男人的典型。
我不能用现代女性的观点去评价古代男人,所以我只好冷眼旁观。
不是我愿意当过客,作壁上观,别人就会拿我当不相干的路人甲。庭院深深深几许,豪门里永远不缺乏争风吃醋、勾心斗角的故事。我在河边走,岂能不湿鞋。
只是没想到全身都湿了。
后花园的墙角那里有一架紫藤,从夏天到秋天,紫藤花一直沉沉地开着,从我的窗户可以看见那些紫色的如浮云飞絮的花朵在秋风中摇曳,渐渐的冷清。我想起大学校园里,也有这么累累实实的紫藤花。当时年少春衫薄,最爱的就是在那一藤的烟光紫的花朵下,对着书静静地冥想,常常是几个小时过去了,手里厚厚的《病理学》还停留在绪论的那一页。
蓦然回首,一切都恍然如梦。
当我追忆自己遥远的过去,真实与想象的界线总是那样令人失望地模糊和混乱。
波兰斯基在他的回忆录如是说。
紫藤架下有条小路逶迤着通向湖畔,闲暇的时候,我会上那里溜达溜达。现在伊若的课程也是名存实亡,我见他们父女都无意把她往才女的方向靠,也就懒得当公公去操这份闲心了。
世界上没有不好的学生,只有不好的老师;前提是学生愿意学习。
没必要强迫席慕容去学习她永远也考不过的几何,也没必要去要求比尔盖茨精通七国语言,当然如果需要的话,我相信他有这样的能力,只是真的没有必要。
伊若的兴趣在玩闹和舞刀弄枪。
所以她的文课程就被我精简为背诗。我坚信诗背多了,终究不是什么坏事。
所以闲极无聊、不安分守己呆在屋内的我,落水也不足为奇。
两位王妃娘娘姐妹情深,前后夹攻之下,一直在神游太虚的我就很自然的被挤到水里了。
我进水后,好一晌才反应过来。
彻骨的寒意,已经是深秋。
我忽然一激灵,立刻扑腾着向边上游。两个娘娘大呼小叫,却没有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帮助。好在我也没指望她们。
倒是绿衣聪明,一早就拿来毛毯子在旁边候着,她知道我会水。临了到了岸边,又和鸳鸯一人一只手,把我给拽了上来。严严实实地用毛毯将我裹好,关键时刻还是自己人可靠些。她轻轻附在我耳边:“姑娘,没事的。我已经叫下头备上了热水,泡上一泡,再喝碗红糖姜水去去寒气。”
我冻的嘴巴哆嗦着说不出话来,只是冲她点点头,里头蕴着的感激赞赏想必她看的出来。
热气腾腾的香汤白雾袅袅,水汽氤氲着,扑面的温暖。我待不及脱掉身上的湿衣服,直接就坐了进去。
真温暖,温暖的让我忍不住颤抖。白茫茫的蒸汽摇曳而上,木通的周围皆是模糊暧昧不清的。
“姑娘,喝口姜糖水吧。”静悄悄地,绿衣递来一碗黑红的的药汤,散发着生姜的辛辣气味。
我摇了摇头,低哑着嗓子道:“不用这个,把我的包袱拿来。”
“我去。”鸳鸯自告奋勇地跑去橱子边。
我见绿衣面无表情,心头一动,疲倦地笑道:“我的身子自小就虚,幸亏碰上了个云游的老道士给我配了瓶药,要是不舒服了,就赶紧吃一颗,否则病气一上来,就怎么也止不住。回头问问你纱衾姐姐,就知道我病起来有多吓人了。”
“不必问,我见着过。”绿衣把手里的碗放到了一边,冲我淡淡地微笑,“昏睡了三天三夜,王爷也不合眼地在旁边守了三夜。他白天处理公务,晚上就在你床边看着。绿衣在王府里呆了这么些年,还没见王爷对谁这么上心过。——姑娘怕是记不着我了吧。”
我尴尬,对于人的相貌,除非我特别留心观察过,否则是很难在我脑海中存档的。
我笑,道:“那时候我病的阎王殿里都进进出出好几遭了,什么都忘的干干净净。”
“可你忘不了王爷吧。”她宽宽地笑,眼睛被水雾遮挡着,看不清楚里头的情绪。手上却很麻利,用干毛巾擦着我的头发,被水蒸气一熏,上头也带了些腾腾的白汽。
“原先就是认识的,想忘掉也难。”我往身上浇着热汤,暗暗赞赏她的仔细,桃花香气虽然普通,用来给我这个体质虚弱的人泡澡却是很好。难为她弄了这包干花来。
心里想着,嘴上就说了出来,没有人会讨厌别人诚心实意的夸奖的。
这时候,鸳鸯也拎着包袱走到我跟前,听我这么一夸,立刻抿嘴一笑,道:“姑娘,你还是谢你自己吧!听说是你要用,库房里哪还有不给的道理。”
我面上讪讪,赶紧叫她把包袱递过来,低头在里面一阵翻找,鼻子已经有些发塞,迟了病倒可就惨了。
病急乱投医,阿司匹林简直成了我的灵丹妙药。
手上一抖,什么东西沉沉地掉进水里了。我伸手一摸,不由“啊——”的一声惨叫!
我的手机,我的三星。
我哭。我有生以来的第一笔奖学金唉,居然真的打了水漂。
我悲愤欲绝地看着湿淋淋的手机,上面还有水不停地流下来。早知如此,当初怎么也要咬咬牙,一跺脚,买个防水的,贪小利而吃大亏。
“希望清洗烘干以后还能用。”我怀着亿万分之一的侥幸心理看着它,招手示意鸳鸯过来,两个丫鬟都被我脸上变幻莫测的表情唬住了,唉,跟她们也解释不清楚。
吩咐鸳鸯把手机放到太阳底下晒,我急急忙忙地吞下药片。我的身体比在现代的时候更加不如,长生不老也是有代价的。
洗好澡我就蹲到火炉边上,楚天裔知道我怕冷,一入秋,我的房间里就升上了火,烧的碳也是上好的,不见一点烟气。
我捧着小手炉,背上披着的狐狸皮氅衣也抵不住那彻骨的寒气,仿佛离了热水,所有的空气都是冷飕飕的,寒气袭人,真的是寒气袭人。
楚天裔过来时,我正瑟缩成一团,蜷在床上小小的一角。被子是冷的,硬的,把寒气紧紧的裹在里头,我怎么挣扎都逃不了这种寒冷。小小的手炉只能温暖靠着的那一小块地方,那点微微的暖意散不开,只能盘旋在胸口,提醒我身上的冰冷。
他没说话,伸手就抱我,我的身体本能地朝温暖的地方靠,拼命地想多汲取一点暖气。
“清儿,清儿。”他低低地呼唤我的名字。我颤抖着,夹着三分委屈,三分恐惧,轻轻地呜咽:“冷,我冷,我不要生病。”
说不清是对生病的害怕还是对未来的畏惧,我的泪水止不住的往下掉,抱着他,就好象抱着遭逢海难时侥幸被我抓住的浮木,只要一松手,剩下的就只有深海的黑暗和冰冷。
“清儿,我的清儿,我在,我不会让你生病的。”身体腾空,我被他打横抱起,昏昏沉沉地抱到了他的房间。不知是不是吃了药的副作用,我瞌睡的要命。楚天裔的房间比别处暖和,因为伊若最爱赖在她父王的房间里,小孩子禁不住寒,为了迁就女儿,这里也就格外暖和。他的房间就在我隔壁,当初为了照顾晕倒的我,他就近将我安置在他旁边的屋子里,后来我出宫后,便长住了下去。
他放下我以后,我还是不愿意放他离开,只是一个劲的嚷:“我冷。”,沙沙的嗓音里夹杂着哭腔,寒冷总是很容易将我变得脆弱不堪。对于生病的恐惧让我越发不想松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