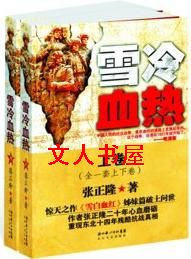雪冷血热-第10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用当地老人的话讲,是有大营就有“日本窑子”。
已经查明的39个慰安所近千名慰安妇中,朝鲜、韩国慰安妇800人左右,其余为日本慰安妇。与“关特演”期间驻东宁县日军比例,约为1∶100。
东宁镇及周边有10余支日军,第3师团师团长昭原中将住在城北万鹿沟。为这些日军服务的是8个慰安所,其中5个是日本慰安妇。镇里老人都知道,现在百货路那一带当年都是“日本窑子”,叫“田胜”、“大路马”、“青春馆”、“大东旅馆”什么的,那鬼子出来进去黄糊糊的,赶集似的。
新城子沟是第12师团司令部驻地。肖秀云老人说,现在水库南边当年有几排房子,对面铺,中间小走廊,小屋间壁得鸽子笼似的。老人当年赶车去那里送东西,见过。后山坡有个大楼,里面有电影院,有十多个日本女人,去那里都是坐小车、骑大马的鬼子。
二道岗子驻1个旅团,有5个慰安所。许传德老人,当年赶车给大营“拉卫生”,就是运垃圾。老人说有两个“日本窑子”是“背小包”的(穿和服的日本慰安妇),他家这一片当年都是“窑子房”,头几年翻盖房子,还挖出些避孕套,就剩个套口的胶皮圈了。
老黑山镇当年驻日军万余人,有6个慰安所,老年人能记起名字的有“看月”、“十七八”、“东京亭”。西老黑山那儿是朝鲜女人,当地人至今仍称那里为“高丽窑子”。
绥阳镇今属东宁县,当年为绥阳县城,日军第8师团司令部在那儿,有8个慰安所。“关特演”后,日军陆续撤走。1944年夏大营空了,慰安所也没人了,传说是跟鬼子去南洋了。
前面写过的郭庆仕老人,在石门子修公路,劳工队有个朝鲜会计,跟“伊吉玛之”的老板川崎挺熟。川崎说他那儿缺个挑水的,让那会计给找个人,不知怎么的就让郭庆仕去了。先挑水,后做饭,直至“八一五”日本投降。
老人说,每天早晨3点来钟起来,走出一里多地挑水,吃喝洗涮一天得20多担水。挑完水就烧洗澡水,有个澡堂子,“姑娘们”洗完澡就开始梳妆打扮,准备接待小鬼子。“背小包”的20来个人,接待当官的,姑娘相对少,当然官也少。逢上星期天,好歹也应付得开。“爱简所”、“苏苏浪”那边就惨了,多时那小鬼子在外边排长队。“康德九年”(1942年),四十多岁的川崎当兵走了,剩个老板娘带俩女儿,跟中国人一样吃高粱米、大麦米了,后来也吃不饱了。那些朝鲜姑娘就更不行了,黄皮寡瘦,有气无力的,那也得接待呀。听说有的被糟蹋得昏过去了。唉,不能说了,说不得了。
苏联红军进攻东宁要塞,炮声隆隆,老板跑了,鬼子也没影了。
池桂兰告诉姐妹们跟她往南跑,经老黑山到牡丹江,再去图们回朝鲜,回家。
刚来时,连到了中国的什么地方都不知道。成天圈在慰安所里,“证明书”都在老板手里,又没有盘缠,不会说汉话,周围除了大山,就是大营,还有警察、宪兵,根本跑不了。而现在,池桂兰想的那条路线,也只能是理论上的。郭庆仕在东宁走了那么多地方,在山里还常转向,更不用说这些两眼一抹黑的女人了。
黑灯瞎火跑了一夜,跑到太平川跑不动了,40多人躺在山上等天亮。天亮后听说老黑山让苏军占领了,一些人不敢走了,就在个朝鲜族屯子留下了。池桂兰和几个姐妹继续往南走,不敢上路,就在山里钻。天亮一打听,又转回大肚川了。村里人看她们那样儿,劝道:别瞎跑了,趁早找个人家待着吧。
东宁县道河镇敬老院李风云老人,平壤人,当年被“招工”到“苏苏浪”。跟着池桂兰跑到大肚川,就留在当地了。老人一辈子没生育,丈夫经常打她,骂她“窑子里出来的破货”。那事能瞒得了别人,还能瞒得了丈夫吗?
最先发现并报道慰安妇的东宁县新闻中心主任陈学泉说,开头他们写文章涉及到具体人时,用的都是化名。
有关部门在调查取证时,有的子女闻讯赶来阻拦,怒气冲天,又尽力压低声音,唯恐被街坊邻居听见。有的老伴站在门口,手持一把斧头,一副不惜拼命的架势。
日本投降半个多世纪了,可对于这些曾为慰安妇的人来说,那场战争结束了吗?
☆‘文‘☆;
☆‘人‘☆;
☆‘书‘☆;
☆‘屋‘☆;
☆‘小‘☆;
☆‘说‘☆;
☆‘下‘☆;
☆‘载‘☆;
☆‘网‘☆;
第38章 “日本话不用学,三年后用不着”
“地上天国”
星原稔,1914年出生于日本熊本县下益城郡半川村,家境贫寒,小学毕业便不得不回家务农。1935年应征入伍,因文化低,难以升迁,一年后即退伍还乡,靠租种土地维持生计。人生就像没有尽头的隧洞看不到光亮,突然接到叔叔的一封信,要他去“满洲国”。1936年9月,这个身材高大的日本青年,筹措一笔路费,踏上改变命运之旅。
叔叔在满洲炭矿株式会社任职,推荐他到阜新煤矿任矿业所本部的警备员,就是看管工人干活、防止逃跑的武装监工。任职不到一年间,他怎样亲手打死三个工人,在此期间及后来担任煤矿管理系、招募系、劳务系的负责人,又怎样折磨、虐待工人就不说了,只说说这个穷光蛋怎样变成大富翁的。
工人每天下班时,由星原稔开出工票,月底凭工票到账房领钱。多则80%,少则只有一半,星原稔以各种理由少计工票时间,工人工资从未足额过。工人每天最多要干16个小时,加班费只有实际工钱的10%,其余的自然也都揣到他的腰包里了。
星原稔手下有4个把头,每个把头管理300个工人。工人的劳动保护用品和日常生活用品,是按人数配给的,星原稔和把头不发或少发,攫为己有。吃饭到他们办的食堂,买东西到他们开的卖店,先记账,月底从工资中扣除。这样,工人相当数量的收入,又进了他们的腰包。他们还开个小钱庄,向工人放高利贷。仅此一项,星原稔每年即可获利数万元。
星原稔与把头开设赌场,从中渔利,再以维持治安为名抓赌,没收赌资,再抓人罚款,每年又有数万元揣进腰包。
最大的进项,还是侵吞招工费。
星原稔经常到山东、河北、内蒙古等地招募劳工,在东北各地摊派劳工、抓“浮浪”。1942年4月调至珲春煤矿后,专职干这个。对于清廉之人,到处奔波,是个苦差。对于星原稔之流,可就是肥差了。在东北招名劳工,招募宣传、劳工食宿和运输开支,需要35元,到关内费用要增加一倍。其中的1/3左右,都被这小子克扣侵吞了。
不知道星原稔的叔叔是何时来东北及怎样发迹的。“九一八”事变前,每年从关内大量闯关东的人们,借用今天的一个词,他们才是真正的“农民工”。无论拖儿带女的,还是春来秋去的“跑腿子”,他们几乎都是农民,也基本都是来种地的。因天灾战祸跨越国界闯关东的朝鲜(族)人,也大抵如此,只不过他们耕种的大多是水稻。而像星原稔的叔叔那样的,凭学有专长、亲朋推荐、自身奋斗,在满炭或满铁这样的大企业谋得一个职位,或者在个小镇开家诊所什么的。有军方背景的人,甚至打入胡子队中,乃至当上胡子头,在日俄战争中充当日军的别动队,“九一八”事变前则为“张氏政权”制造麻烦。可像星原稔这样的穷光蛋,没有任何技能、关系、背景,想落草为寇当个喽啰都摸不着门,弄不好只有成那大烟泡中的死倒了。无论日本在东北有多大的势力,那毕竟不是“满洲国”。
但是现在不同了。无论多么穷困潦倒,多么狗屁不是,只要是个日本人,踏上这片黑土地,就可以把肚子腆得老高,就是人上人。
1932年5月,《关东军司令部对驹井长官等满洲国官吏的希望事项》(草案)中说:“在发展经济方面,虽然提倡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但首要的是谋求日本和日本人的利益。”
“满洲国”的日本人,因工作地区的不同,地区补助津贴为50%到100%。加上供给住宅,物价便宜,生活水平比在日本提高两倍左右。战犯坂田义政等人写的《伪满警察罪恶史》中说:“1935年滨江省五常县日本人警士的月工资为90元,而中国人警士只有8至12元。”
“满洲国”的日本人,教育是义务制,就学情况比日本国内还好。开拓团只有两个学生,也要办所学校。伪满总务厅长星野直树说,“满洲国”的“所有日本人都要上大学”。
满铁编写的《满洲读本》,在谈到日本人的生活、教育、医疗等情况时,说“满洲国”是日本人的“地上天国”。
日本在苏联、在远东地区有那么多间谍,150万红军共分四路集结、开进,关东军竟然没有知觉。1945年8月9日苏联对日本宣战的消息,是事后从满洲通讯社的无线电讯中得知的。关东军最后一任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将,一个其貌不扬的小老头,当天正在大连观看歌舞伎演出。就让人想起“九一八”事变时的张学良,及其手下那帮东北大员,就开始了关东军和日本人的总溃败、大逃难。
“新京”火车站已不是“人满为患”所能形容的了,全是“地上天国”的人。客车、闷罐车、敞篷车,不管什么车,只要能挤上去,就是天照大神的“神佑”了。一列列火车开走了,更多的人还在涌来,把道路都堵塞了。苏联飞机不时来轰炸,广播电台成天播军乐,那感觉就是哀乐。8月13日后连降大雨,男女老少落汤鸡般蹲在雨里水里,大人把孩子搂在怀里,不敢动窝儿,唯恐轮到自己时上不去车,被扔在这昨天的天国,今天的地狱里。
最惨的是远离城市和铁路线的人们,主要是开拓团的移民,特别是靠近边境地区的。
东宁县三岔口镇泡子沿村,有个开拓团。村里老人说,他们是“康德三年”(1936年)来的,有男有女有孩子,一家一家的,“背包摞行的”(意为背扛许多东西),还有锄头、镢头、三尺钩子什么的。看那样子,在日本过的那日子,也不比俺们强哪儿去。可人家那日子很快就好起来了,“满洲国”向着人家,好事都是人家的。后来看见他们还有枪,除了种地还训练,这叫什么庄稼人呀?苏联人打过来那天晚上,那炮响的呀,老百姓都猫在家里,也不知道谁先动的手,谁打到谁那边去了。第二天下半晌,有人说开拓团那边不对劲,去看,屋子里碗朝天、瓢朝地的,猪都上炕了。炮一响,那人就跑了。
东宁有铁路,军用铁路,动作快的乘车走了一批,铁路被炸断后就用“11”号(指双腿步行——编者注)。从东宁向北奔牡丹江、哈尔滨,再向南经沈阳、安东到朝鲜,乘船回日本。他们来时就是这样一条路线。苏军占领朝鲜,被憋堵住了,大都迟滞在东北的大中城市,惶惶如丧家之犬。
有老人说,咱是守家坐地当的亡国奴,他们是大老远跑到咱这地场当了亡国奴,那是什么滋味呀?无论什么滋味,无论知不知道回国去也是亡国奴,那工夫算是彻底明白了,只有在自己的国家里的那个家,才是最安全牢靠的。
开拓团空了,各地通常都有的日本人住宅区也空了。拖儿抱女的,推车挑担的,就像上下班高峰期的人流,却不是。因为他们要躲避钢铁翅膀的飞机,还要与地面急速推进的摩托化军队赛跑。远远地看到后面尘土飞扬,一支支主要由女人、孩子构成的逃难队伍,就赶紧隐蔽在附近山林,或青纱帐里,看着那汽车、坦克远去了,再继续上路。如是反复。有的遇上溃败的日军,有人觉得好像有了依靠,往往招来更大的灾难,甚至屠杀。遇到村屯,开头多是绕开,后来就去讨宿,要些吃的。有的被接纳,有的被拒绝,有时还会受到攻击。不断有人失散,大队变成小队,再聚合,再失散。有人“麻达山”了,有人陷进沼泽地,有人病死饿死,有人被狼撕狗掳。
曾为关东军士兵的日本作家五味川纯平,其长篇小说《战争和人》中的主要人物之一阿苫,在从虎林开始的逃难路上,被苏军士兵扔到车上,糟蹋够了再扔下去。
被当地人收养的孤儿,留下来成了“东北媳妇”的女人,有数。谁也说不清的,是究竟有多少人暴尸荒野。一个比较一致的说法是,苏联出兵东北后,包括关东军在内的日本人中,开拓团移民的死亡率是最高的。
而许多远离战场,包括一些边境地区的开拓团,还沉浸在“铁打的满洲国”、“大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喧嚣中的人们,得知日本投降、完蛋了,如雷轰顶。路途遥遥,缺乏运输工具,又多是女人孩子,往哪儿跑啊?绝望了,再有一两个叫嚣“玉碎”的头头,有的开拓团就向天皇遥拜,然后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