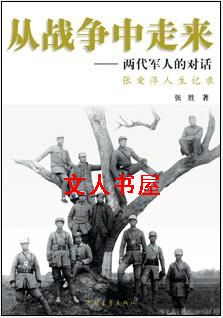军人机密-第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题是《救救孩子》。原来,本案的真相是,当年邵老先生在察觉杨仪已身怀有孕之后,不忍其母子被害,于是谎称有一条密语要紧急送出,将杨仪诓出监狱。此事完全是缘于一位民主老人的善意而发生的不幸。一九五一年六月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部为杨仪案正式做出结论,杨仪同志遂被定为革命烈士。结语:在战争时期,这种情况亦属十分个别。杨仪同志,以及那个未出生的孩子,确实应当被视做是为革命事业献身的。杨仪烈士永垂不朽!”
荧光中,贺紫达的面颊上两行老泪滚滚而下。随着文字的跳动,他看见的是一张张脸:杨仪、楚风屏、姜佑生、谢石榴……
沉默良久。女军官轻声问:“贺副司令员,您是否需要休息一会儿?”贺有些气滞地回答:“刚才,我说过,我当年是红三军团的,你能说得出三军团第三师有两个连队政治委员的故事吗?他们一个叫石元祥,一个叫曾彬农。”
女军官操作一阵:“石元祥同志、曾彬农同志的事迹见于一九八九年四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黄克诚回忆录》上卷,文章记录:肃反委员会有一次提供的所谓‘AB团’分子名单上的人,大多是连队基层干部。记得其中一个名叫石元祥,一个名叫曾彬农,我根本不相信他们会是反革命,便派警卫员悄悄告诉他们暂时上山躲起来。每天,我派人偷偷给他们送饭吃,打起仗来就叫他们下山,各回自己的连队带兵参加战斗。战斗一结束,马上再上山躲藏。他们两人明知上边要抓他们,但并不逃跑,打起仗来更加勇敢。他们曾向我表示,希望以此表明自己无愧于党和革命。可是,大约过了两个星期,事情终于被肃反委员会发觉了。在一次战斗刚刚结束之时,石元祥、曾彬农几个人尚未来得及躲避,就被肃反委员会抓捕,不久就被杀掉了。我痛惜万分,悲愤地质问肃反委员会,何以滥杀无辜!并同他们大吵了一通。因此我也被怀疑有问题,也被抓起来‘审查’。幸好彭德怀同志得知情况后,进行了干预。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有人说我支持彭德怀的‘意见书’,是为了报救命之恩,就是指的这件事情。其实,在庐山会议之前,我对肃反委员会是由于彭德怀干预而将我释放的情况根本不知道,别人没有告诉过我,彭德怀也从来没有跟我谈起过此事。”
贺紫达重重地叹了一口气。他的脑海中又浮现着两个年轻红军干部英勇作战的场面。
屏幕上打出三条字幕:
石元祥同志、曾彬农同志永垂不朽!
黄克诚大将永垂不朽!
彭德怀元帅永垂不朽!
缅思良久,贺紫达突然问道:“好几年过去了,《黄克诚回忆录》的下卷为什么还没出?”女军官:“贺副司令员,您的问题已经超出范围。请问您在杨仪同志的问题方面,还有什么需要重复查询的吗?”
贺紫达似乎显得有些疲惫,缓缓说:“没什么可问的了,不过你得改一下,杨仪和我的儿子没有死,他起了个和我一样的名字,现在他就在洞外面。”
女军官起身,准备为贺穿风衣:“您有权更改这条资料。欢迎贺副司令员下次光临。”贺猛然坐直身体:“慢着!别关机器!干什么,我的正事还没开始呢!”
女军官回答:“贺副司令,杨仪同志的资料已全部提供。”
贺紫达激动着说:“谁说的这就是全部?你回到你的座位上去,我要你听着,并且一个字一个字地弄到你的那个机器里,你们是历史。将来不论谁再到这里了解杨仪,不论是她的儿子、孙子来,还是她的战友楚风屏来,你都得把真正的全部情况如实告诉他们。我最近感觉不怎么妙,恐怕很快就会找那个姜佑生去了,我得把实话,把埋了一辈子的良心话告诉你!你们是历史,历史他妈的得完完整整、彻头彻尾地是真的!我不能饶了姜佑生,但杨仪她不能饶了的却是我!杨仪在自杀之前,心就被我狠狠地伤了。她的死,有我贺紫达的一份大罪啊!我要告诉你们,全部告诉你们……”
急切中,贺紫达大口大口喘着粗气。女军官忙问:“贺副司令,您哪儿不好……”为防万一,女军官按响了茶几上的电钮。
值班室里,一台仪器上的灯亮,铃声随之响起。中尉严文久立即起身冲出门。正在值班的一名男军官马上提起药箱,一名女护士抱起氧气袋,跟着奔出。
咨询室内,医护人员围住贺,有准备输氧的,有拉开衣链准备用听诊器的,贺紫达推开众人的手:“干什么,干什么,你们是从哪儿冒出来的?老贺就是喘了两口大气,又不是咽气!”
“您真的没事?”中尉问。贺不耐烦地使劲挥手。
女军官用眼神示意了一下,中尉和军医、护士退了出去。
贺紫达:“搞什么名堂,这鬼地方还有战场救护的一套。”
女军官把茶杯放在贺的手里:“对不起,来我们这儿的老同志在接触到历史中的某些事情时,经常会……”
贺紫达沉默一阵,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唉——我们这些老家伙呀,别人不知道,自己还不知道吗?心里沉哪……”
女军官轻轻地走回微机操作台,缓缓坐好,将双手放在键盘上,望着那颗银发如戟的头颅,庄严地准备输入什么。
军官休息室。小贺子答看着一本英文的外军军事杂志。看着看着,他掏出一个本子摘抄了几句。放下杂志,他看看腕上那块硕大、复杂的军用电子表。
山林幽幽,风过飒飒。极富老人气韵的苍红色枫叶,遒劲而祥和。
咨询室。贺紫达已讲述完毕。他按了按含泪的眼窝,缓缓地喝了一口茶,将杯子放下。女军官为他穿上风衣,同时说道:“鉴于您提供的情况比较特别,我们将做出研究。贺副司令员,谢谢您。”
女军官显得感动至深,直视着贺的眼睛:“我非常非常想冒昧地多说一句,作为一个女人,我为您能讲出这样的情况,真的很感动,真的。”
贺有些心力交瘁。女军官从地板上捡起拐杖,双手递给贺。贺拄着,慢慢朝门走去。在门口,贺回过身,特意说了一句:“谢谢你,小姑娘。你就是一个小姑娘。”
贺紫达像是完成了他人生的最后一件事,精神彻底松懈,双手拄住拐杖,如同整个人都俯在那根弯弯曲曲的树棍上。他喘息片刻,沿着幽深的洞库通道离去。他的背影显得迟笨,拐杖的声音孤独而沉重。
女军官快步追上,搀扶着贺。洞内长廊的紫光,成了一条迷蒙的有些晃动的雾道,贺什么都看不清。不久,一双皮鞋的声音加入进来。贺的眼前十分模糊地走来一个人影,这人影靠住他的另一侧,一只手很隐蔽地搀扶着他……
似乎走了很久,突然迎来一片刺眼的光亮。那片光中又渗出一个模糊的人物,
于是朦胧中是三个人小声的对话:
“贺军长,贺副司令看起来非常疲劳。”
“怎么会这样?他到底查了些什么样的档案?”
女军官的声音:“您不知道吗?”
儿子的声音:“他不说。”
女军官:“唔,很正常。”
儿子:“什么正常,我想他的知密范围根本不会比我大。”
女军官:“您说的是军事秘密,而不是军人秘密。”
儿子:“什么意思?”
女军官:“对不起。请搀好您父亲。”
儿子:“活见鬼,一个中校跟少将谈什么秘密,居然还无可奉告!”
中尉的声音:“请小心……再见,贺副司令,再见,贺军长。”
重重的关车门声。引擎轰鸣。
贺紫达靠在“奥迪”后座上,双目紧闭,脸几乎埋在立起的风衣领子里。轿车有些颠簸。他的耳畔响起一串骤急的马蹄声……
山路上,二十八岁的贺子达(即后来改名的贺紫达)与两个警卫员身穿国民党军装俯在马背上狂奔,子弹“嗖嗖”地从他们头顶划过。在后面紧紧咬住他们的是七八个游击队员。
——那是一九四七年夏末。
贺子达等三人被追杀得狼狈不堪,不得不闪入路边树林。
枪声惊动了公路前方的国民党一辆满载士兵的卡车。押车军官用望远镜观察一阵,嘟囔道:“好大胆子,光天化日之下,共军打国军……准备战斗!”
卡车上立即架好了机枪。
游击队见敌有重兵,拨转马头,但已有些来不及了。卡车边追边扫射。
林子里,贺子达看到公路上的情形,拔出枪,大叫一声“跟我来!”冲下山坡,向卡车拦腰截去。奔至车前,贺子达扬手一枪,卡车上的机枪手应声倒毙。贺的警卫员都是双枪在手,一阵突袭,车上七八个国民党兵一一歪倒。贺子达马不停蹄,一划而过。
远处,游击队员得到机会,斜向山林。只是他们纷纷疑惑地回头呆望。
俯在驾驶楼里的军官,看看公路两头战马留下的烟尘,骂道:“他妈的,这是谁打谁呀!”
贺子达大笑不已。
解放军总部所在地。机关伙房门前,贺子达一边脱着国民党军服,一边笑着对失去一条腿,另一条腿却打着绑腿的炊事班长谢石榴说:“共军打共军,国军打国军,是要多悬有多悬!本来想冒充国民党,在穿越敌占区时方便些,没想到被自己的同志杀了个屁滚尿流!哈哈哈哈……”
谢石榴择着菜:“鬼点子,撞鬼。伢子,你什么时候才能规矩一点儿呢?”
“老号长,还好吗?”
“还好,一日三餐,保证首长吃饱吃好。就是组织上总要我下地方,我不干。”
贺:“对,要下地方,也得等打回你的老家,再下不迟。老号长,我去看看楚风屏。”谢:“去吧,我也该做饭了。唉,二万五千里长征最后一站,腊子口上的一炮,把腿给弄丢了一条!”
山脚原野。贺子达与二十岁的女机要干部楚风屏边走边谈。
楚风屏问:“贺司令,总部不是通知分区政委们来开会吗?你怎么?……”贺道:“听说你要去大石山,想来送送你,就替政委跑一趟。”
“什么来送我,说得好听。”楚伸手,“拿出来吧,是给小姐捎情书,还是带东西。”
贺子达看看左右,小声地:“别小姐小姐的,多难听。”
楚风屏:“她是杨大老板的千金小姐,我是她的陪读丫环,这可是千真万确。”
贺连忙道:“小声点,我的姑奶奶,让我的警卫员听见,你叫我的脸往哪搁。多少年前的事儿还提它!现在,杨仪是我老婆,你楚风屏是姜佑生老婆,姜佑生是我老战友,你是杨仪老战友,这里面只有男人、老婆、战友之分,没有阶级之分。”
楚笑:“好,刚整完风,我们不开这种玩笑。拿出来吧。”
贺子达的手冲身后十余步的警卫招了一下,警卫员跑步上前,从公文包里掏出两个不大的小包裹,一个上面写有“姜”字,一个上面写有“杨”字。
楚拿到手里:“哟,给战友的这么轻,给老婆的这么重,打开看看。”
“别,别。”
“我偏要看看。”
贺子达:“千万千万别打开,为这东西,本司令肯定得吃个处分,但求你把它送到杨仪手里,我再向组织坦白。”
楚风屏大惑:“什么东西?你得告诉我。”
贺胡乱比画着:“……是……是个……黑的……”
“是鸦片?”
“不是,有点,也有点白……”
“白面?”
“瞎猜!是……是个……钢家伙。”
“大洋?!你哪弄来的这么多大洋?”
“别胡说!”
“那到底是什么?”
贺子达窘急:“是……是……是……嘿,有你这么当丫环的吗?给你家小姐带东西,你盘查那么细干什么!”
楚风屏笑:“好,好,奴婢该死,不问啦……怕水吗?”
贺:“不怕。给姜崽子的那包怕。”
楚:“瞧你们俩,都是当旅长、当司令的人了,还你叫他崽子,他叫你伢子的。”
“那有什么,想当年在井冈山的时候,谁不知道彭老总的三军团有一个不怕死的湖南崽子,还有一个死不怕的江西伢子。”
远处响起了军号。贺子达听了听:“总部叫我呢。好,等杨仪生下儿子,你让崽子给我分析分析,哪点像我。明天什么时候出发?”
“早饭后。”
“我一定来送你。”
贺子达与警卫上马而去。一中年干部走近楚风屏,看了贺的背影片刻,问道:“楚风屏同志,准备得怎么样了?”
“李部长,全都准备好了。”
“这一路一千多里,难免遇到各种复杂情况,千万多加小心。”李部长严肃指令,“你一定要赶在九月一日之前到达大石山独立旅,将杨仪从电台上替换下来,并开始启用新密码。机要纪律你是知道的,这个密码只能你自己掌握。如果九月一日不见你联络,我们会从临近军区另派同志,这个意思你懂吗?”
楚风屏:“我懂,万一我出了什么事,也不可能由杨仪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