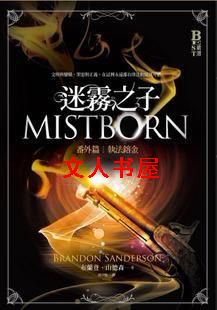林中迷雾-第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缪斯一言不发地坐下,甚至没向我挥挥手。
我又把注意力转向弗莱尔。“你想怎么样?”我又问。
“首先,”弗莱尔说,“我想让夏米克·约翰逊道歉,因为她破坏了两个可爱诚实的年轻人的声誉。”
我更专注地盯着他。
“但如果她能立即撤销所有指控,我们也可以接受。”
“你就继续做梦吧。”
“科普,你这个人啊就是这样。”弗莱尔摇摇头,不耐烦地啧啧几声。“我说过那不可能。”
“你表现出男子气的时候,真可爱。不过你已经知道这点了,是吗?”弗莱尔抬眼望了望缪斯,脸上现出一种受打击的表情,“天哪,你穿的都是些什么啊?”
缪斯坐直身子:“你说什么?”
“我说你的衣柜有问题。简直就像福克斯公司出版的令人恐怖的新版现实剧:《女警察的衣着》。亲爱的上帝啊。瞧那双鞋……”
“这鞋很实用。”缪斯说。
“甜心,时尚的第一原则:‘实用’和‘鞋’这几个字千万不能出现在同一个句子里。”弗莱尔眼睛都没眨一下,就又转身对我说,“我们的当事人犯的只不过是轻罪,你就给他们一个缓刑吧:
“不行。”
“我能向你说几个字吗?”
“不会是‘鞋’和‘实用’吧?”
“不是,是对你来说可怕得多的几个字。恐怕是:‘卡尔’和‘吉姆’。”
他顿了顿。我瞥了缪斯一眼。她在座位上动了一下。
“就是这两个小名字,”弗莱尔声音轻快地继续说,“‘卡尔’和‘吉姆’。这几个字我听上去不亚于悦耳的音乐声。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嘛,科普?”
我没上钩。
“在我们所谓的受害者的陈述中……你向她读过她的陈述,对吧?……在她的陈述中,她明白无误地说强奸她的人叫卡尔和吉姆。”
“这说明不了什么。”我说。
“嗯,我说,亲爱的,你可得当心,因为我觉得这对你的案子可能非常重要:我们的当事人叫巴里·马兰兹和爱德华·詹雷特。他们不叫卡尔和吉姆,而叫巴里和爱德华。和我一起大声地念他们的名字吧。快啊,你能行。巴里和爱德华。现在,这两个名字听上去根本不像卡尔和吉姆了吧?”
莫特·帕宾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咧嘴笑着说:“不像,弗莱尔,不像。”
我继续保持沉默。
“而且,你瞧,那还是你的受害者所作的陈述。”弗莱尔继续说,“真的很精彩,你不这样认为吗?等等,我来找找看。我就喜欢读这句。莫特,你带来了吗?等等,找到了。”弗莱尔戴上月牙形的阅读眼镜。然后,他清了清喉咙,变了一种腔调。“那两个强奸我的男孩叫卡尔和吉姆。”
他放下手中的纸,抬起头来,好像在期待我鼓掌。
我说:“她阴道里发现了巴里·马兰兹的精子。”
“啊,没错,但顺便说一下,巴里是个英俊的小伙子一我们都知道,这点很重要一他那天晚上早些时候可能是与你那个急不可耐的约翰逊女士发生过两相情愿的性行为。我们都知道,夏米克那天在他们兄弟会。你对这点没有争议吧?”
我不喜欢他这样说,但我还是说:“没有,没有争议。”
“实际上,我们俩都知道,夏米克·约翰逊前一周还去那里当过脱衣舞女。”
“是表演脱衣舞。”我纠正道。
他看着我:“因此,她又回去了。当然是做金钱交易。我们也都同意这点吧?”他没等我回答又接着说,“我可以找到五六个男孩子证明她和巴里之间很友好。得啦,科普。你过去也处埋过这种情况。她是个脱衣舞女,未到法定年龄。她偷偷溜进大学兄弟会聚会场所,被那个富家子弟看上了。他会怎样,把她打发走,或者不招呼她,或者无论其他怎样。她便生气了。”
“但身上的许多伤痕怎样解释?”我说。
莫特用一只看上去像被碾死在马路上的动物一般的拳头砸着桌子,
说:“她只不过是想要一大笔钱。”
弗莱尔说:“暂时别这么说,莫特。”
“去他妈的。我们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她之所以不放过他们,都因为他们有钱。”莫特最最冷酷地瞪了我一眼,“你其实知道那婊子有前科,对吧?夏米克”一他用一种嘲讽的声音念着这个名字,我非常生气一一“已经有一个律师了,想敲诈我们的男孩子们。对那头母牛来说,这就是个发薪的日子。就这么简单。一个他妈的伟大的发薪日。”
“莫特?”我说。
“怎么啦?”
“嘘,现在是成年人之间在说话。”
莫特嘲讽地说:“科普,你也好不到哪里去。”
我等他说下去。
“你要起诉他们的唯一原因是因为他们有钱。而且你知道这点。你还在扮演影视中那种劫富济贫的角色。不要假装不是。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吗?你知道是什么真正让我屁股着火吗?”
我今天上午才让一个人的屁股痒瘅了,现在又让另一个人的屁股着火了。真是不寻常的一天啊。
“说来听听,莫特。”
“在我们这个社会,这是普遍现象。”他说。
“什么现象?”
莫特猛地举起双手,狂怒地说:“憎恨富人。你随时都能听到这样的话:‘我恨他,他太有钱了。’看看安然丑闻和其他丑闻吧。现在,这已经成为一种受到鼓舞的偏见一憎恨富人。如果我什么时候说:‘嘿,我恨穷人。’那我会被吊死。但咒骂富人会怎样呢?嗯,你可以随心所欲地骂。人人都可以恨富人。”
我看着他:“也许,他们应该成立一个互助小组。”
“去死吧,科普。”
“不,我是认真的。特朗普,还有哈里伯顿公司的人。我的意思是说,这个世界对他们是不公平的。互助组。对,他们应该有个互助组。也许搞个电视马拉松或者其他什么。”
弗莱尔·希科里站起来。动作当然是戏剧性的。我还以为他会向我行屈膝礼呢。“我想,我们还是到此为止吧。明天见,帅哥。还有你。”一他看着洛伦·缪斯,张开嘴,又闭上了,浑身战栗了一下。
“弗莱尔,怎么啦?”
他看着我。
“卡尔和吉姆那件事。”我说,“只证明她说的都是事实。”
弗莱尔笑了:“怎么会呢?”
“你的男孩子们很聪明。他们一定是自称卡尔和吉姆,因此她才会那样说。”
他耸起一道眉毛:“你认为这可能吧?”
“弗莱尔,你认为还有别的什么原因会让她那样说吗?”
“你说什么?”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夏米克想陷害你的当事人,她为什么不直接说出他们的正确姓名?她为什么要去编造与卡尔和吉姆的那些对话?你读过她的陈述。‘把她向这边转,卡尔。’‘让她仰起身子,吉姆。’‘嘿,卡尔,她很享受呢。’她为什么要编造这些?”
莫特回答了这个问题:“因为她是个想钱想疯了的婊子,笨得要死:但我可以看出来。我击中了弗莱尔的一个要害之处。
弗莱尔倾身向着我:“科普,问题就在这里:其实我们完全没必要这样。你知道这点。也许你是对的。这也许是有些说不通。但你也知道,这会让事情混乱起来。而这正是你这个我最邕欢的美男子最希望出现的局面。我说得对吗,合理怀疑先生?”他笑了笑,“你可能有些物证。但是,嗯,如果你把那个女孩子放到证人席上,我也不会善罢甘休。这将是一场游戏,一场比赛。我们都知道。”
他们向门口走去。
“再见,朋友,庭上见。”
04
缪斯和我一时没说话。
卡尔和吉姆。这两个名字让我们灰心丧气。
首席调査官的职位几乎总是由男性职业军人担任。多年来看到过的—切已经让他们疲惫不堪。他们身穿破旧的军用防水短上衣,态度生硬,大腹便便,喜欢高声叹气。这个人的工作,就是帮助正直的郡检察官一比如我这种出于政治原因而被委派到这个职位上的人一一在埃塞克斯郡法律系统政治竞赛中获胜。
洛伦·缪斯身高可能只有一米五多一点,体重大约相当于四年级学生的平均体重。我选择缪斯担任我的首席调査宫,曾经在老兵中引起过―些令人厌恶的波澜。我也妇道这样做会引起争议,但我有自己的偏好:我喜欢雇用上了一定年纪的单身女人。她们工作更努力,对雇主更忠诚。而且我已经发现,几乎在每一个案子中,这一点都已经得到证实。你会发现,如果一个单身女人已经上了一定年龄,如三十三岁,那她一定是为了事业而活着,她们给予你的工作时间和对你的忠诚度,都是有孩子的已婚女人永远无法给予的。
公正地说,缪斯还是一个有着不可思议的天赋的调查官。我喜欢和她谈论事情。我还会说这是对那些事情的沉思(在英文中,‘缪斯’与‘沉思’是同一个单词。一一译者注)但在这种“沉思”过程中,你可能会突然茅塞顿开,这也不难理解。此刻,她正盯着地板。
“你是怎样想的?”我问她。
“这双鞋真的那么难看?”
我看着她,等着她往下说。
“简单地说吧,”她说,“如果我们不能找到一种办法来解释卡尔和吉姆,我们就麻烦了。”
我抬头盯着天花板。
“怎么啦?”缪斯说。
“我在想那两个名字。”
“它们怎么啦?”
“为什么?”我已经无数次问过这个问题了,“为什么是卡尔和吉姆?”
“不知道。”
“你又问过夏米尔了?”
“问过了。她说的话前后一致得惊人。他们一直在用那两个名字。我想你是对的。他们是故意用那两个名字做掩护,让她的话听上去显得荒唐。”
“但为什么是这两个名字呢?”
“也许是随便挑的。”
我皱皱眉头:“缪斯,我们一定忽略了什么。”
她点点头:“我知道。”
我一直很搜长分割我的生活。我们都擅长这个,但我特别擅长。我可以为自己的世界创造独立的宇宙空间。我可以处理好生活中一方面的问题,而且不让它以任何形式干扰生活的其他方面。有些人看了警匪片也会纳闷:为什么匪徒们在大街上会那么暴力?因此,他们喜欢待在家里。但我就不会那样。我有那种分割生活的能力。
我并不为此骄傲。这也不是什么必须具备的伟大素质。但这能保护我。是的,我看到过这种能力能让哪些行为变得更理性。
因此。在过去的半小时里,我一直在回避这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如果吉尔·佩雷斯一直活着,他在什么地方?那天晚上树林里发生了什么事?当然,最大的问题是:如果吉尔·佩雷斯在那个可怕的晚上活了下来……
我妹妹是否也活下来了?
“科普?”
是缪斯在叫我。
“你怎么啦?”
我想告诉他。但现在还不是时候。我需要自己先理清头绪,想想这―切究竟是怎么回事,确认那具尸体是否真是吉尔·佩雷斯的。我站起来,走到她身边。
“卡尔和吉姆,”我说,“我们必须弄清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而且要快。”
我的妻姐格蕾塔和她丈夫鲍勃住在一座麦氏豪宅中,豪宅位于一条新的死胡同中。那条胡同看上去几乎与北美洲的任何其他死胡同完全一样。相对于胡同中那些巨大的砖结构奈宅来说,停车场显得太小。尽管每座房子形状各异,但看上去仍然几乎完全一样。每一样东西都打磨得太厉害,主人本想让它们看上去更陈旧,结果却显得更假。
我先认识格雷塔,后认识我妻子。我还不到二十岁时,妈妈就离家出走了,但我至今还记得卡米尔走进那片树林前几个月妈妈告诉我的車情。我们是我们那个人口相当混杂的城市里最贫穷的公民。我们是移民,在我四岁时从以前的苏联移民过来。刚开始时,我们的情况不错——我们是作为英雄到达美国的。但很快,情况就变得非常糟糕起来。
我们当时住在纽瓦克一座楼房的顶楼,楼里住着三家人。不过,我们在梅普尔伍德的哥伦比亚中学上学。我的父亲,弗拉迪米尔·科皮斯基(他将其英语化成了科普兰)以前曾在列宁格勒当医生,但在美国却搞不到行医许可证,最后只好成为一个油漆匠。我的母亲是个身体虚弱的美人,名叫娜塔莎,曾是一对贵族大学教授的女儿,非常骄傲,受过良好的教育,现在却在肖特山和利文斯顿的富人家里担任不同的洗涤工作,但每份工作的时间都不很长。
在一个特别的日子,我妹妹卡米尔放学回家后,用一种滑稽的声音宣布说,城里有个富家女喜欢我。我母亲听了很兴奋。
“你应该约她出来。”妈妈对我说。
我做了个鬼脸:“你见过她吗?”
“见过。”
“那你就应该知道,”我像任何一个十七岁的小伙子一样说,“她是头野兽。”
“俄语中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