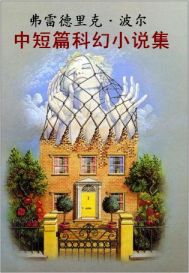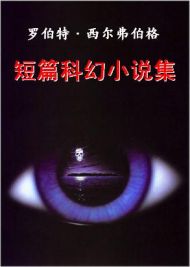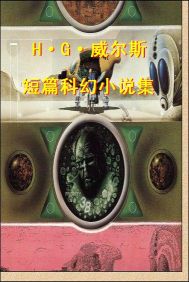科幻纵览-第14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第三节:反乌托邦名作
上面这些作品,均创作于科学技术的上升时代,是在乐观主义底色下渗透的一点点警示。它们往往是“小叙事”,只涉及个人、局部、个别灾难,描绘的是整体正确的科学事业进步中出现的一点点小偏差。到了二十世纪,这份乐观被许多科幻作家抛在脑后,反科学思潮在科幻小说中得到了直接和充分的体现。在二十世纪前半叶,反乌托邦小说是这一倾向的集中代表。
“面对威尔斯对进步的信仰,特别是他后期小说中大力宣传的乌托邦理想社会主义,文学派则针锋相对地提出反乌托邦。最近文章中一直称之为‘反面乌托邦’,此语即希腊语‘病的’、‘坏的’意思。这些文章认为科技的进步非但没有给社会带来好处,反而每况愈下,更不要说完美了……”詹姆斯冈恩《科幻之路》二卷,20页,福建少儿出版社出版。
反乌托邦的先驱,是英国作家福斯特创作的一个短篇《大机器停止运转》。1909年发表于《牛津和剑桥评论》秋季号上。小说将背景放在未来某个不确定的年代。那时,地面上已经无法生存,人类只能戴着防毒面具才能上来。在原子能还没有被发现的年代里,福斯特设想不出什么样的巨祸能够给地面带来这样的破坏,干脆便隐去原因不表。完全生活在地下的人们由一个无所不包的机器系统结成一体,没有国家、民族之别。这个背景设置,意味着作者要描写一种全人类共同面对的处境,而非只是某国某族的“私事”。人们住在完全一样的个人房间里,“北京和希伯来一样”。在大机器的饲候下,人们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通过类似电视电话的装置随意和千万里之外的人打交道,一个人可以认识几千人,但从不面对面交往。生下的孩子都交有机器哺养,亲情淡漠。一本大机器的使用说明书象圣经般摆在每个人的家中。
小说主人公是一位叫凡许蒂的中年妇女。她的儿子库诺已经成年,生活在另外一个大陆上。两人经常几个月不直接见一面。有一次,库诺通过通讯设备,一定要求直接面见母亲。他告诉母亲,自己曾经上过地面,看到那里有人生活在原始环境里,并且感受到了不依赖机器的自然体验。凡许蒂闻言,斥责孩子大逆不道,只有以大机器为依归才能有文明幸福的生活。几个月后,大机器慢慢停止转动,已经失去独立生活能力的人类无计可施,走向灭亡。
福斯特是标准的文人,对科学技术并不在行。小说里的技术描写只有轮廓缺乏细节。不过这并不重要,“大机器”只是作为科学技术的隐喻出现在小说里。作者生动地描写了人类对机器的依赖。这种依赖已经形成了宗教般的狂热:“他们竭力陈述:‘机器供我们吃、供我们穿、供我们住、通过机器我们得以互相通话、互相见面,有了机器,我们才得以生存,机器是思想的朋友,怀疑的敌人。机器是万能的,永久的,神圣的。’不久,这一训谕就被印在书的扉面,在随后的版本中,这一仪式变成了复杂的赞美和祈求的形式。人们小心地避免提到‘崇拜’这一字眼,从理论上讲,机器仍然是人的创造物和工具,但事实上,除了少数倒行逆施的人,所有人都把它当作神一样来崇拜……”(同上,49页)
除了这种反讽的形式,作者还通过代表人性挣扎的库诺之口,直接表达自己的思想:正在死去的是我们,这儿唯一真正活着的是机器。人创造了机器来按照我们的意愿办事。但现在我们办不到了,它已经剥夺了我们的空间感觉和触摸感觉,它混淆了每一个人的亲属关系,它使亲情淡漠到仅剩肉欲,它使人们头脑空白,四肢无力。现在它又使我们对它顶礼膜拜。(同上,43页)
与后世反科学思潮代表人物的论述相比,这些观点可能不算深入或者新奇。但考虑到它产生于二十世纪之初,我们仍然要钦佩作者的远见。
反乌托邦作家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认为科学技术导致了个性、多样性、丰富性的抹杀。这或许是把科学进步与工业化大生产必然结合起来的原因吧。在《美丽的新世界》里,赫胥黎就将两者直接结合在一起,让小说里的人类干脆使用“福特纪元”,将流水线生产的发明人视为新的耶稣基督。和《大机器停止转动》一样,小说里也设置高度科技背景下的“文明社会”和自然状态下的“野蛮世界”的对立,也有代表着“原始人性”的人物。双方之间也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冲突。在这批有巨大影响的反乌托邦作家里,或许只有赫胥黎出生在自然科学世家,小说里对科学技术的描写十分到位,这样也更突出了作品的主题。
在刚刚诞生的苏联,扎米京亚也创作了《我们》。和福斯特一样,不熟悉科技的作者只是粗线条地描写着未来高度发展的技术。但对那种数字化的、高度统一的生活的恐惧感则跃然纸上。科学统治和政治独裁之间的联系是随着扎米亚京一起诞生的,此后,这种联系和反乌托邦的题材就密不可分了。《科幻小说》45页,(法)加泰尼奥,商务印书馆1998年出版。
站在今人的角度回头看,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工业化初期的流水线生产似乎并无必然联系,后者更不是前者的必然产物。亨利福特虽然最早享受了这种新生产方式带来的巨大财富,但终因汽车产品样式多年不变,让出了世界第一汽车公司的位置。到了今天,个性化、小批量生产,正在成为许多高科技企业提倡的时尚。不过,直到二十世纪中叶,流水线产品的单调整齐还是工业与科技留给世人的主要形象。
需要指出的是,《一九八四》和《我们》、《美丽的新世界》一起被后人并称为三大反乌托邦名著。但它们的笔锋所指稍有不同。《一九八四》主要批判极权统治。在那部书里,“英社”统治下的大洋国,其科技水平和物质生活较以前大大倒退,一片破败景色。仅有的“电幕”、“海上浮动平台”等“先进技术”也只是统治工具。而在另外两部著作里,作者都给我们描绘了远远超过现代的科技水平,社会生活可谓物质丰足。所以,如果要以反科学思潮为题来分析这些作品,那么《一九八四》应该排除在外。
第六卷:科幻与科学 第六章:沉重的科幻主题——反科学思潮(4)
第四节:其它例证
除了反乌托邦小说这样的典型外,那个时代还有个别作者,在作品里提出了自己的怀疑。捷克作家恰佩克便是其中一位。在他的不朽名著《鲵鱼之乱》里,各国科学家不顾“深海鲵鱼”拥有智慧的明显事实,将他们作为实验动物对待。在“第一届有尾类动物代表大会”上,作者通过一个与会者的记录,讽刺了在会上作报告的职业科学家:请原谅我,我真不知道他讲的是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我在绞尽脑汁地想,如果我把德沃里安特教授的右大脑叶切除,教授可能发生什么样的失调现象;如果我用电来刺激带微笑的冈川博士,他会发生什么反应,还设想如果有人把雷赫曼教授的内耳迷路弄破,他会有什么反应。我也有些拿不稳究竟是我分辨颜色的能力如何,究竟我解决我的运动神经反应的七因素能力如何。我很苦恼,因为我怀疑,在我们切除彼此的大脑叶并切断感觉脉管以前,我们在纯科学意义上说来是否有权利谈论我们(我是指人类)的精神生活。事实上,为了研究我们的精神生活,那就必须彼此手里拿着手术刀来互相解剖。就我来说,为了科学的利益,我真想打碎杜布斯克教授的眼镜,或者使代阿顿教授的秃头内部受到电击,然后发表一篇文章来报告他们的反应。《鲵鱼之乱》16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不过,那时的科幻文学主流并非反科学思潮,对科学进步的歌颂仍然占据主要地位。这一点,从美国黄金时代科幻小说的代表作里就可以看出。
一:反科学思潮的主流化
到了最近二十年,科幻作品里反科学思潮的代表集中在好莱坞的科幻大片里。虽然无论是英国、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还是巴基斯坦、墨西哥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都拍摄过自己的科幻片,但把科幻电影拍到一定水准,形成广泛影响的,仍然只有美国科幻片。而美国科幻电影的一个潮流就是反科学。
《机器战警》就是一个反科学影片的典型。
在著名的科幻系列片《终结者》的第二集里,第一集那个娇弱的女子萨纳康拉变成了一个狂热的恐怖分子。她囤积军火,袭击计算机公司。编导给她这些行为以一个科幻的解释:萨纳康拉从未来战士那里知道了人类的命运,不顾一切想阻止它的到来。但从社会意义上讲,萨纳康拉身上完全有着当时西方一些“绿色恐怖分子”,如卡钦斯基的影子。在《终结者》第二集里,萨纳康拉试图刺杀计算机专家戴维斯,因为此人即将研制成功的“天网”会导致人类毁灭。面对戴维斯,萨纳康拉最后心软了,没有开枪,但她把愤怒转成怒骂:正是你们这些自以为有创意的人,发明了核武器。这一观点是当时反科学思潮的重要特点。
二:深入第三世界
“在一般的观念中,科幻小说应该是为科学唱赞歌的,但这只是中国科学主义语境下的科幻小说给人造成的印象。而在欧美的科学幻想小说中,科学却很少是被歌颂的形象,”田松《唯科学反科学伪科学》这一概括是很准确的。不过,即使在欧美这些工业化的先驱国度里,这一主流也是到了二次大战以后才确定的。如今,象《龙卷风》那样正面歌颂科学工作者献身精神的作品已经是凤毛麟角了。
不过,如果把全世界的科幻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最能突出体现其反科学倾向的,应该是第三世界的科幻作品。如果在那些尚未完成工业化的地方,科幻作品也渗透着强烈的反科学思想,岂不是更能说明它已经渗透到科幻文学的血液里。
拉什曼隆德赫是印度科幻文学的代表人物,而《爱因斯坦第二》又是他的代表作品。这个短篇的主题,正是反思科学对人性的剥夺。“爱因斯坦第二”是印度科学家斯里尼瓦博士桑的绰号,以示其超人的天赋。象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那样,斯里尼瓦桑作为国宝级科学家,受印度政府的保护和供养。他的健康甚至要由军方负责,身边经常围绕着特种兵。他的任务就是完成爱因斯坦未竟的“统一场论”研究事业。但是六十七岁那年,博士身患肺癌,无法医治。不过为了国家荣誉,他的生死由不得自己。医学家奇塔莱醉心于脑科学研究,利用政府不择手段保护斯里尼瓦桑生命的态度,说服有关部门支持他进行手术,将博士的大脑取出来,靠生命维持系统存活,并继续统一场论的研究。斯里瓦尼桑当然不愿意让自己变成实验白鼠。但在威胁和蒙骗之下,他的大脑还是与身体分了家。在科学家求知欲的支配下,仅存大脑的斯里尼瓦桑最终还是完成了统一场论的研究,但却拒绝把这一成果公布给世人。“每一个新的发明都让我们变得越来越残暴,这种文化没必要四处传播,因为在我看来,人类还没有文明以可以接受统一计场论的程度。”《科幻之路》六卷,677页。最后,主人公用无法理解的方法熄灭了自己的智慧之火。
在泰国科幻小说《克隆人》中,作者塞尼暧也塑造了一个“唯科学主义学者”的典型形象。那是一个叫斯宾塞的西方医生,为泰国富翁披楼敏主持秘密的克隆人实验。作者细致地描绘了斯宾塞的思想形成过程:五岁时,斯宾塞和家里的多伯曼种狗相嬉,忽生疑惑,怀疑这条狗的身体里有什么东西能够让它运动、吠叫,于是便用刀杀掉狗进行解剖。由于年龄幼小,屠狗的经过自然十分漫长,但斯宾塞竟然一直坚持到将狗杀死为止。当然,这件事令他受到家长的严责,但这种“科学家的灵性”却顽固地保留下来。斯宾塞读大学时选择了医学专业,痴迷于解剖人体,甚至废寝忘食。在他的钻研中,人性慢慢被排除在视野之外。这样,斯宾塞能够和披楼敏合作,进行毫无人道的“克隆人养殖事业“,就显得非常可信。在小说的后半部分,他先后切割了两个鲜活的生命却无动于衷。小说家用大量的手术细节,突出了斯宾塞的这一性格。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冷血,而是在理性主义过度侵染下,对人类社会其它方面无动于衷的表现。
三:中国大陆科幻的表现
五十年代,科学必胜的信念充满了那时的中国科幻小说。到了七、八十年代,最初一些拥有怀疑色彩的科幻作品诞生了。进入九十年代,反科学思潮成了中国科幻的主流。再寻找一部歌颂科技进步的科幻小说反而很困难。单从这个角度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