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鬼出没的世界-第2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国影视荒漠中出现的时尚?你是被外星人绑架的人这种发现至少使人们从乏味的日常生活中获得了一点新奇的刺激;你引起了同行、治疗专家,甚至媒体的注意;你会获得一种被发现、兴奋而又有点害怕的感觉。随后你将会记住什么?你开始认为自己就是未卜先知者,甚至是促成我们这个时代不断涌现的重大事件的人物;你不想让你的治疗专家感到失望;你渴望得到各种人的肯定。我想,你成为被绑架者定会获得具有预知未来的特异功能的褒奖。
与外星人绑架事件相比,在产品上做手脚的事件,想引起人们对UFO和外星人绑架事件的惊讶的情感则收效甚微。有人声称在普通饮料罐中发现了针头。这成为轰动一时的事件是完全可以想象的。报纸、特别是电视新闻对这个事件进行了报道。同样的报道在全国范围内很快大量出现,而且愈演愈烈。但是人们很难理解一个针头是怎么会进到饮料罐里,而且没有一个目击者能够向我们提供当时原封未动的饮料罐被打开并发现里面有个注射器的现场证据。
逐步积累的证据表明,这实际上是一种“一味模仿他人”的犯罪行为。人们只是假装在饮料罐中发现了针头。为什么人们要这样做?他们这样做的可能动机是什么?有些心理学家认为其主要动机是贪婪(他们可以向制造商索赔),渴望被注意和希望扮演受害者。值得注意的是,没有治疗专家借此事件大肆宣扬饮料罐里发现针头的真实性,鼓动病人——隐晦地或直接地——向公众宣扬这个新闻。产品中发现异物的厂家受到严厉的罚款,甚至被谎称产品中有异物的也受到处罚。但是,那些鼓动被绑架者向公众宣扬他们编造的故事的人和治疗专家仍然存在,对于谎称自己被UFO绑架的人也没有适宜的法律处罚条例。不管编造这种故事的人这样做的理由是什么,让别人相信他们被更高级的生物出于难以理解的原因而选中,要比他们在可乐罐中发现有个注射器这种偶然事件更让人感到心满意足。
第九章 治疗方式
在没有掌握资料之前就建立理论是一种严重的错误。这时人会不知不觉地扭曲事实以适合理论,而不是让理论符合事实。
歇洛克·福尔摩斯
阿瑟·柯南·道尔《波希米亚的丑闻》(1891)
真实的记忆看起来像幻影,而错误的记忆却如此令人信服,以至能够取代事实。
加布里尔·卡希亚·马奈特
《奇怪的朝圣者》(1992)
约翰·麦克是哈佛大学的一位精神病学家,我们已相识多年。
很久以前他问我,有没有什么与UFO有关的事件。
我回答说,不太多。不过从精神病学方面看倒有一些。他进行了调查,会晤了被绑架者,结果改变了自己的观点。现在看来他接受了被绑架者的看起来是真实的说法。这是怎么回事?
他说:“当时我并没有想到会这样。我没有任何接受这些外星人绑架故事的思想基础。但这些经历所具备的情感力量使它们很有说服力。”在他的《绑架》一书中,麦克明确提出了一个非常可怕的说法,即某些事情让人感受到的“力量或强度”,会对人们判断它的真实性产生一种引导作用。
我个人也承认这种情感的力量。但是,我们的梦不是就总有一种强大的情感成分吗?我们有时不是会在极度的恐惧中惊醒吗?麦克自己就写过一本有关梦魇的书,难道他不知道幻觉的情感力量吗?麦克的一些患者说过,他们从儿时起就有过幻想的经历。而催眠师和精神疗法医生在对“被绑架者”进行治疗时,是否尽职地学习过幻觉和感知功能障碍方面的知识?如果他们相信这些目击者,为什么不相信那些具有同样说服力的,遇到了神、魔鬼、圣徒、天使和精灵的报告呢?还有那些说自己体内有不可抗拒的命令声音的人?难道让人感受强烈的故事都是真实的吗?
我认识的一位科学家说:“如果外星人扣留所有他们绑架的人,那我们的世界就更神智健全一些。”不过她的结论过于严酷并让人感到不舒服,这不是理智的问题,而是别的。加拿大心理学家尼古拉·斯潘诺斯及其同事认为,那些报告被UFO绑架的人都没有明显的病理症状。不过,
一般来说,倾向于相信神秘事物的人,特别是相信有外星人的人,以及用外星人假设来解释特异感受和幻想体验的人,更容易产生UFO体验。在相信UFO的人当中,嗜好幻想作品的人尤其可能有这种体验。而且,当他们在某些特定的感觉环境中时,这种体验发生的可能性更大,更有可能被说得像真实的事情而非想象……(例如,发生在夜里的体验以及在睡眠中所产生的体验)。
具备较多批判精神的头脑将其看成是幻觉或梦,更易轻信的头脑将其看成是难以理解的,但却是深奥的客观现实。
一些被外星人绑架事件的描述想来可能是一些不甚清晰的被父亲、继父、叔叔或母亲的男友所强奸或童年性虐待的记忆。他们把施暴者当成是外星人,而非所信任的、亲爱的人,当然会感到舒服一些。但将那些外星人绑架的传说当做真实的事情接受的治疗专家们却对此持否认态度,他们说如果他们的
病人曾遭到性虐待的话,他们是能够了解清楚的。据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美国有高达1/4的女性、1/6的男性童年时受到性虐待(尽管这些统计数字可能偏高)。如果有数目很多的在外星人治疗专家面前出现过的患者没有受到过这种虐待,其比例甚至并不高于普通公众受到性虐待的比例,那才会让人感到非常吃惊。
性虐待治疗医师和外星绑架治疗医师都会花费数月、有时是数年的时间,鼓励他们的治疗对象记起被虐待的经历。他们的方法相似,目标也一样——恢复痛苦记忆,而这种记忆通常是很久以前的。对于这两种情况,治疗专家们都认为,无论是遭受精神创伤的还是遇到可怕事件的患者,其记忆功能都受到某种程度的抑制。我发现一种令人注目的现象,那就是,外星人绑架案的治疗专家很少发现性虐待的案例,性虐待受害者也很少向这种专家求医。
可以理解,性虐待或乱伦的受害者对于任何可能减少或否认自己经历的事情,都表现得非常敏感。他们会为此发怒——他们也有权这样。在美国,至少1/10的妇女被强奸,其中差不多有2/3是在18岁以前受到的这种伤害。一项最近的调查显示,向警方报案的强奸受害者有1/6在12岁以下(而这类强奸报案比例最小),这些女孩中有1/5是被她们的父亲强奸的。她们是被诱奸的。我想明确指出的一点是:在很多真实的案例中,父母或扮演父母角色的人是残忍的性施虐者。有的案例中揭露了一些有力的证据,如照片、日记,儿童所患的淋病或衣原体属疾病。虐待儿童被认为是社会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根据一项调查,因暴力犯罪入狱的人当中,有85%在童年时受过虐待。十几岁的未婚母亲中,有2/3在童年或青少年时期遭受过强奸或性虐待。强奸受害者中,酗酒和滥用药物的比例比其他妇女高出10倍。这个问题确实存在,而且急需解决。而在大部分案例中,这些无可否认的儿童性虐待悲剧,其记忆会一直留存到成年以后。他们没有需要恢复的隐藏的记忆。
我们今天有比过去更好的报告,每年医院和执法机构报告的虐待儿童案似乎有了显著增加,1967至1985年间在美国增加了10倍,达170万件。酒精和其它麻醉品,以及经济压力,被认为是今天的成年人比过去更容易虐待儿童的原因。日益受到公众注意的儿童虐待案,使成年人记起了他们曾受过的虐待。
一个世纪以前,西格蒙德·弗络伊德提出了压抑的概念,它是维持心理健康的一种反应机制,即为了逃避强烈的心理痛苦而忘掉一些事件。它尤其可能出现在被诊断患有“歇斯底里”症的病人身上,歇斯底里包括幻觉和麻痹的症状。一开始弗洛伊德认为,在每个歇斯底里病例的背后,都有一个被压抑的童年性虐待事件。最终,弗洛伊德改变了他对童年性虐待幻觉——并不是所有的幻觉都是不愉快的——引起的歇斯底里症状原因的解释。他认为这是罪恶感从父母转移给了孩子。至今这方面的争论还十分热烈。(关于弗洛伊德内心变化的原因今天仍有争议——从他在维也纳中年贵族中引起的暴怒的解释,到他承认他认真听取歇斯底里症患者所说的事情的解释。)
那些记忆突然浮现(特别是在心理学家和催眠师的帮助下的记忆浮现),而且第一次的“往事追忆”中有鬼怪或具有梦幻般性质的例子,是很值得怀疑的。有很多声称受到性虐待的案例看起来是编造的。埃墨里大学心理学家乌尔里克·奈瑟尔说:
确实有儿童被虐待,也有被压抑的记忆这样的事例。但这样的事例中也有很多是虚假的记忆和信口开河,这种情况并不少见。记忆错误是常有的事情,并不少见。这种情况总有发生。即使是在记忆主体绝对自信的情况下,即使记忆中是似乎不可能忘记的强烈闪光,是一幅含有隐喻的内心画面。在有生动暗示的情况下,记忆会按照治疗过程中医生对病人强烈的指示,进行塑造或修改,因而这样的情况更有可能发生。而一旦记忆以这样的方式被改造,再想改变将是十分困难的事情。
这些一般的原则并不能帮助我们确定,哪个个别事件,哪个陈述是真实的。但是一般来说,通过对大量这样的案例的了解,我们应该把宝押在哪里,已经很明显了。记忆失误和在回忆中对过去事情的重新编造是人的一种天性,这种天性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存在。
纳粹死亡集中营的幸存者为我们提供了最清楚的例证,即使最令人发指的虐待也能够一直留在人的记忆中。实际上,对很多的大屠杀幸存者来说,最大的问题是使自己和死亡集中营之间保持一定的情感距离,即遗忘。但是,假设在一个难以形容的邪恶的世界里,他们被迫居住在纳粹德国——我们假设一个强盛的“后希特勒”国家,其意识形态丝毫未变,只是改变了反犹太的思想——那么想象一下那些大屠杀幸存者的心理压力吧。那时他们也许能够忘记,因为记忆会使他们当前的生活无法忍受。如果存在对可怕回忆的压抑以及其后的重新回忆,那么可能需要两个条件:(1)虐待确实发生过;(2)要求受害者长时间内装做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理查德·奥夫希解释说:
当病人被问起记忆是如何唤起的,他们说是把影像、概念、感情和知觉的碎片集合起来,勉强凑成连贯的故事。当这种所谓的记忆工作持续数月之后,感觉成了模糊的映像,映像成为人影,人影又变成认识的人;身体某个部位的隐隐作痛,转而被当做是儿时遭受的凌辱……最初的身体感觉,有时被催眠的作用放大,被称作“身体记忆”。人体肌肉能保存记忆,其机理让人无法理解。如果这些方式不能说服人,治疗者可能会求助于更强硬的治疗方式。有的病人被编入幸存者小组,让他们承受同组成员的压力,并要求他们通过加入某个小圈子,来证明其在政治上有相同立场。
美国精神病学协会在1993发表的一份谨慎的声明中,承认作为一种应变的方式,有些人会遗忘童年时受的虐待,但声明警告说:
目前尚不知道,如何准确地区分基于真实事件的记忆和来自其它来源的记忆……。反复询问可能使某些人说出从未发生过的事情的“回忆”。不知道在宣称有受性虐待记忆的成年人中,真正受过虐待的比例有多大。……精神病医师先入为主地相信存在性虐待,或别的因素——不论是不是病人问题的原因,都可能会干扰诊断与治疗。
一方面,麻木不仁地无视对耸人听闻的性虐待的指控,这是毫无同情心的非正义行为。另一方面,篡改人的记忆、炮制虚假的童年性虐待故事、破坏完整的家庭,甚至将无辜的父母送入监牢,同样是毫无同情心的非正义行为。应该对这两种情况都持怀疑主义的态度。而在这两个极端中选择道路,是件非常棘手的事情。
在艾伦·巴斯和劳拉·戴维斯所写的很有影响的书《痊愈的勇气:童年性虐待女幸存者指南》(Perelinnial Library,1988)的早期版本中,给治疗专家们提出了一个启发性的忠告:
相信幸存者。你必须相信你的病人遭受过性虐待,即使她自己也怀疑这一点。……你的病人需要你坚信她曾受到虐待。与一个心存疑念的病人打交道,和跟一个相信自杀是最好出路的人打交道很相似。如果患者不能肯定她是否曾被虐待,只是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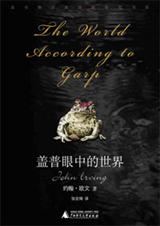


![[综]有村民出没请小心封面](http://www.aaatxt.com/cover/7/7159.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