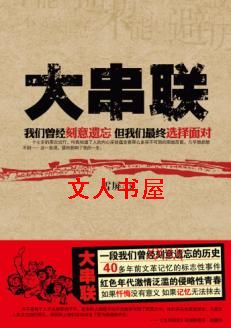红色家族档案-第2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们打了人,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听说北京干部和公社都曾经调查过此事,但最终不了了之。
如果你问一个陕北婆姨他的男人到哪里去了,她回答:上山受苦。这是下地劳动的意思。陕北话把下地叫上山,劳动叫受苦。农民一律自称受苦人。所以受苦人这称呼在陕北并不是指阶级分析意义上的受压迫受剥削之贫下中农。我们这些知青这时候也是受苦人。
话说初夏里的一个艳阳天,我和杨家湾的,一群受苦人正在山上受苦。此时繁重的农业劳动正在日益失去革命的浪漫意义,正在对我们进行不折不扣的磨炼,并且带领我们向着它的本质——受苦接近。
时近正午,所有人都已饥渴难当,大家都盼送饭的人快点从那条小路转弯处出现。
红桩子是一个健壮的中年人,有好看的长腰和筋腱毕露的长腿。他被公认是一个全面的庄稼把式,所以当组长,是我们这帮子上山受苦人的头儿。此刻我正怀疑他中了魔法,因为他坚定挺拔的背影说明他除了上下挥舞老镢③之外,脑子里完全没有别的想法。我也怀疑周围的一切部中了魔法,包括天上的太阳,因为它牢牢地粘在我们所有人的脊背上,半天不肯动一动。我脑子里则是挥之不去的毛主席《愚公移山》中的语录:“每天挖山不止,祖祖孙孙挖下去……”有一阵儿我悲哀地认为我们已经变成了愚公,永远不能停止挥舞手中的老镢了。
但我毕竟是个头脑灵活的人,因为我很快发现,左顾右盼对缓解挥舞老镢的疲劳很有作用,我便开始愈来愈频繁地向四处张望。
正是万物生长的季节,延河两岸,也就是当地人称为“川”里的青纱帐已经密密地遮严了黄土地。从我们受苦的黄土山上远远看过去,川里除了庄稼,还有一群驴。
这些驴是杨家湾拉车转磨的宝贝,所以队里派三娃的公公,人称老队长的稳妥老汉经管它们。老队长对这群牲口十分上心,一有空闲就吆着它们出来吃草,使我在饥渴难当的时候能够看见这样一幅悠闲的放驴图而稍感欣慰。忽然,这幅图画中的景物发生了使人不安的变化。我看见一头大驴爬上另一头小一点驴的背,小驴躲了一下,但是大驴不肯甘休,再一次爬上去,这次小驴不再躲闪,而且我有点儿觉出它实际上是半推半就。这还不算完,像受了传染似的,几头大一点的驴都先先后后地爬上了小一点驴的背。小驴们也都是半推半就。按说,就算我从来没有见过,或者是我再傻,也应该从大小驴们的暧昧态度上会意出这是个传种接代的仪式,以及这类仪式的不可言说或者不宜言说性。但我的智力那时一定因为不停上下挥舞老镢而出了问题,我只觉眼前驴们的游戏生动活泼,与上下挥舞老镢比较显然更有趣和新奇。所以我就干下了平生最大一件傻事。
我对所有人大叫:“看呀!驴打架!”
我一脑门子想,这至少可以使那些上下挥舞的老镢停下来。
果然见效,魔法被解除。所有人在回头看了一眼之后都停止了挖山。男人们大多抱着肚子笑倒在地下,女人们或者羞红了脸,或者追打身边笑倒的汉子们,嘴里骂着:和尚!和尚!好像男人们犯了大错。陕北人骂人家和尚,大约是咒人娶不上媳妇,或者断子绝孙的意思。但我一直觉得这句话逻辑上有问题,因为出家当和尚的人是出于信仰,是主动选择没有妻小家室的。而娶不上媳妇则大部分是出于无奈,是没有办法生儿育女。这里面有个精神境界的问题被混淆了,所以我一时还是不能从众人的态度中领会发生的事情。
组长红桩子先还想压住阵,绷着脸说:“悄悄儿(安静的意思),悄悄儿,笑甚哩!”但是看着这一山坡笑倒的人,又看看仍然蒙在鼓里的我,终于也憋不住,对我说了一声:“好饿(我)个你哩!”和众人一起笑倒尘埃。
我终于恍然大悟。在我的人生经验里,从来没有碰上过如此尴尬的事情。我面红耳赤,张口结舌,真希望黄土山立时三刻裂个缝子,好让我钻进去。幸好这时候送饭的人挑着担子,一摇一晃地出现在小路上,红桩子率领受苦人中几个仁慈点儿的奔向午饭,这才给我解了围。
从此刻骨铭心,对鸡牛猪狗的类似行事均能举一反三,心明眼亮。
一夜,烦躁莫名辗转难眠。夜空晴朗,月到中旬。后半夜,窗纸依旧白花花耀人眼。披衣起坐,无所适从。忽耳有所闻,心有所动,屏息静听时脑畔飒飒作响,似风过竹林而清奇诡谲,如雨洒荷塘更生动神妙,渐渐由远而近,徘徊反复,先寻寻觅觅,后愈发密集,不多时竟觉六合充溢,近在咫尺。然环顾左右,除身边朵朵、毛毛两位姐姐酣睡沉沉,惟一窗明月流泻如水。
忐忑难耐,捻破窗纸凝神向外张望时,不觉目瞪口呆,心旌摇荡。
对面山上一群狗,足足有50条以上的狗,正静悄悄在银色月光下散步。这回我一眼看出,这集体散步的性质和传种接代有关。如风如雨之声竟是狗们的脚步。灿烂的星月之光下,狗的队伍显然正在不断扩大。新来的无声加入,如先前的一样静静地走,先三五成群,摩肩接踵,渐渐耳鬓厮磨,成对成双。整个队伍首尾相衔,似漫无目的,细细推敲,又分明是一场规矩华丽的爱情圆舞。只见狗们的眼睛闪闪烁烁,愉快而激动。它们的步子始终镇定,队伍始终有秩序。干燥黄土正在狗脚下发出沙沙天籁。黄土山在夜空中形成巨大剪影,酷像舞台上的布景。在神秘的表演气氛中,狗们都面露庄严进入冥想,虽与我隔山相望,却高傲地沉浸在一个视我为另类的,不可知的世界里。
我被深深震撼,一股强大的力量从宇宙深处,飞越日月星辰,飞越五湖四海,越过我至今建立起来的一切审视和分析生活的方法,不远万里地撞击着我要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的愿望。眼前这一群眼睛亮闪闪,正在发情的狗,使我惊异莫名,使我在那个高尚的革命愿望之外,对自然和宿命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敬畏。这种感觉以后我还多次产生过,如面临一个垂死的病人,看到一件出神入化的艺术品或者美丽得吓人的自然风光。最使我惊奇的是,我发现这种庄严伟大的情感竟然和任何高尚的革命愿望无关。我相信,大自然是在这个春末夏初,差遣了这群眼睛亮闪闪的狗,向我首次昭示庄严。直到今天,我一想起这个夜晚,想起如昼月光下目光如炬的狗群,就禁不住喉头发紧,汗毛倒竖,就进入一种不能自禁的对大自然的崇拜。
我和狗都正入神,忽然村里传来嘈杂的人声和什物碰撞的声音。看样子有人像我一样发现了狗们的行动。他们弄出种种声音把狗驱散。受了惊扰的狗群很快从我的视线里消失了。不知它们是换了地方还是真的被人们躯散。一直到天亮,四下里老有狗在狺狺地叫,使这天清晨怪异而不安。整个白天没有人提这事,当然也没有人出来对昨晚的驱散事件负责。我非常想问问除了我还有谁看见了昨晚对面山上狗们的行事,而且十分想问那些半夜大动干戈的人为什么要将它们驱散。但我记住了上次的教训,所以像人民大众一样成熟地守口如瓶。
时间长了,对这类事儿我也没了问的兴趣,因为在这个不止草木萌动而是许多东西都在萌动的春末夏初,我见到太多畜牲们的类似行事,以及人们反复演出的驱散事件,所谓司空见惯是也。有一次,我竟完全像个当地婆姨一样,下意识地对一只正在踩蛋的公鸡大骂“和尚”!还如临大敌地高举起双手作威吓状。站在母鸡身上雄纠纠的大公鸡着实受了惊吓,落荒而去。之后当我悠悠地意识到什么时,很为自己的举止也变得那么滑稽和没来由而惊异。
人的记忆是最不可靠的东西之一。最近,一起插队的北京知青聚会。大家对当年事情的记忆简直是南辕北辙,相差千里。他们说我曾经在杨家湾引娃娃,就是带一些学龄前的儿童,让他们的母亲可以无牵挂地上山受苦。我说我完全不记得了。但是现在我想起来是有这事,因为要不然我记忆里的以下这件也是发生在春末夏初的故事就失去线索了:有一个男娃和一个女娃,都是四五岁的样子吧。有一天我带他们和一群娃娃出去散步,忽然发现这两个娃娃不见了。我在一个僻静的角落里找到他们,我再也想不到他们会在做这样的事!他们竟然在仔细观察,然后抚摸对方的生殖器!显然对它们的截然不同十分好奇。好在农村小孩子惯穿的开裆裤,使他们的举动保住了起码的雅观。这时候的我虽然已经成熟老练了许多,但对眼前的事情仍然大紧张起来。我真拿不准自己是应该呵斥他们,还是上演一次驱散事件。但最后还是决定不动声色的好。
我联想起一些事情。好几次我和娃娃们散步,碰上过村里无聊男人,他们往往会脸上带着粘糊糊的表情问:“娃娃,夜里你妈在上面还是你大在上面?”
对他们问完后满脸的得意和愉悦,娃娃们大多能够老练而镇静地开口就骂:“和尚!”比我的反应准确迅速得多。
这使我逐渐明白了一个事实:村里的成年夫妇和他们的未成年子女自古以来从不分室而居。所以这些屁大的孩子从记事起就耳濡目染,知道了我们这些城里学生在生理卫生课上勉强了解的那些神秘知识。发生在我眼前的这个惊世骇俗之举,实际上只是男女孩童之间的游戏吧。而所有游戏中的主要成分只是摹仿。
不久,传来一个坏消息,这件事情让我今天想起来还难受万分。我们班一起来插队的同学中,有一个分在另外的生产队。她和外校的一个男生在劳动和生活中发生了感情,所谓感情充其量是拉拉手,亲亲嘴的事情。但不知道为什么就闹得沸沸扬扬,不晓得哪一级领导还把他们当阶级斗争新动向抓了典型。他们问这个女同学是否和那男生发生过肉体关系,偏这个女同学属于精神世界最纯洁的那种,竟然以为拉手和亲嘴就是肉体关系,懵懵懂懂就说那男生和她发生了肉体关系!结果那男生因此吃了大亏,给当做“流氓”抓到县大狱里。在以后漫长的日子里,男女双方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想,同样的问题如果让我带的这些屁大孩子,甚至让过完了春末夏初的我来回答,一定不会出这种令人痛心的错误。
秋天的时候,我被队里派到公社的水利工地上,是在一个叫李家湾的地方修水电站。我是队里派出的唯一女生,所以和不同队里派出的女劳力住在一起。
原来和这些婆姨女子睡一条炕还不是对我最大的考验。我很快发现在同住的少数几个人中有一种奇怪的关系。她们总是在大家都睡了以后开始不安分。我原以为她们在聊天或讲故事,后来发现她们不只动口还动手。那时我还不知道什么叫同性恋。也不知道人可以同时是同性恋,又是双性恋。所以我虽然被这事搅得心烦意乱,虽然在又一次抓阶级斗争的时候,有人把这件事半通不通地汇报上去,说有人搞流氓活动。但由于我已经经历了春末夏初的季节,我现在至少知道它是一种和阶级斗争或者革命理想完全无关的东西。我对前来调查情况的女干部说,女民工干那么重的活,睡觉时已经个个像死人。再说都是女人,耍什么流氓?那个女干部是个回乡知青,脸嫩得要出水;想必是属于精神世界纯洁的一类,听了我的话遂羞得满脸通红,无言而去。
但是我以最快的速度,很坚决地换了一个窑洞住,而且对那些女人说她们必须收敛,必须避人!
她们故意装糊涂,乜斜着眼睛问我:“咋了?”
我强硬地说:“不咋,畜牲可以不避人,你们得避!”
说这话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成熟得简直像她们的妈。
不过为了避免进一步的尴尬,趁她们还在我的复杂逻辑中打转转儿的时候,我赶紧拔脚而去。
春末夏初真是一个深刻的季节。当我穿行其中,终于走完这个季节的时候,我成了一个复杂的人。我的精神世界不再洁白如雪。但我却更加镇定、老练和有力量,或者套用海德格尔的话,更加“诗意地生活在大地上”。
但是30年过去了,无论怎样镇定或者诗意,我至今没有勇气再回杨家湾,因为我不知道怎样面对现在大概已经做了祖母的三娃。这件事情对我们这些当年动手打人的人来说显然是没有权利要求宽恕的,甚至没有权利再在三娃的面前提起。它只能永远留在我们自己心上,它只应该在那里永远不愈合,永远疼痛。深夜醒来,我又常常暗自庆幸,这伤口幸好没有留在脸上,因为它是一个永远抹不去的羞耻标记。
当我纯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