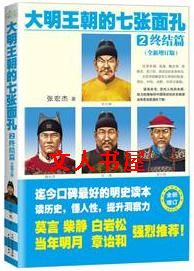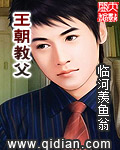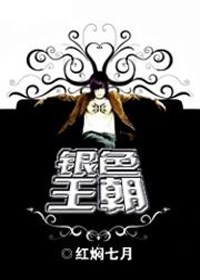龙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第7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发表了这样的任命。王安接到任命,上表辞谢,这本来是一种政治套路。这时,不得不提到一个叫王体乾的人,时任司礼监秉笔太监,做梦都想当上一把手,听说王安辞不就任,决心抓住这不是机会的机会。他马上想到一个人——那是唯一可以依靠的人——“急谋于客魏【一开始,实际上只与客氏单独密谋】夺之”{85}。客氏一直不喜欢王安,甚至有点怕他,因为此人太“刚直”,如果王安出掌司礼监,日后她出入宫禁以及在所有其他事上,必多有不便;相反,王体乾则是一个“软媚”之人,如助他登上司礼监首脑宝座,他不会不识时务,不会不听话。客氏这女人相当有政治头脑。她的设计是:让王体乾当一把手,让相好魏忠贤当二把手。这种安排,一箭三雕——第一,送给王体乾这样的人情,结成同盟,扳倒王安;第二,王体乾不论居何高位,总归会是傀儡,平时具体事务让他出面张罗、兜揽,更好;第三,相好魏忠贤,直接当司礼监第一把手,实在太过夸张,不好办,王体乾将二把手位子腾出来给魏忠贤,已是一步登天,将来设法让魏氏以司礼监秉笔太监兼领东厂,实权更大。客氏、王体乾之间达成协议,遂找来魏忠贤一起商量。魏忠贤乍闻此事,很不雄才大略的“小人物”心态又表露出来——他居然念及王安在“移宫案”后,保护过他,救己一命,“犹预【豫】未忍”。王体乾见状,私下又“以危言动客氏”,客氏在枕边把魏忠贤好好训斥了一番:“外边【指廷臣】或有人救他,圣心若一回【皇上一旦改变主意】,你我比西李【李选侍】如何?终吃他亏。”这个提醒很关键,“移宫”中魏忠贤站在李选侍一边,很积极,虽赖王安遮挡,安然解脱,但把柄终捏于人手,万一哪天“旧事重提”,那可……这么一想,“贤意遂决”。
可见魏忠贤并不是一步到位,从一开始就频作威福、玩弄事机、骄横恣肆,他也是“在斗争中成长”,慢慢地学会颐指气使、恣威擅权。
骤列大珰,短短数年,从魏傻子摇身而为“九千九百九十九岁”(只比万岁朱由校少一岁),史无前例。但表面上的不可一世背后,这位有史以来最大的政治暴发户,向来就不曾从微贱的往昔和记忆中完全走出来。有件事很说明了这一点。魏忠贤跃升司礼监秉笔太监之后,当年那个曾经为难过他的四川税监邱乘云,撤任回京,魏忠贤故意派一名太监专程到南郊迎接,邱赏了来人三十两银子,那人回来向魏忠贤汇报,魏竟当时落下泪来,说:“我先年被徐贵谮害,止给我十两路费,今赏尔如此,便三倍我了。”说完,“叹息者久之”。创巨痛深,可见一斑。穷其一生,不管这个人怎样一手遮天,归根结底,他骨子里仍旧是“小人物”,到最最关键的时刻,“小人物”心态还是让他安安静静地引颈就戮。关于魏忠贤,人们对这一点以往谈论得很不够。
大计既定,一切由客氏斡旋。她径见朱由校,“劝帝从其请【指王安辞不就任的请求】”{86},同时,经唆使,兵科给事中霍维华于天启元年五月十二日疏论王安,加以攻击。这开了先河,“是为奄党第一功也”{87},霍也成为后来声势浩大的阉党的先驱。有人弹劾,客氏加大了嚼舌头力度,不断危言耸听。朱由校至愚至昧,分不清好歹,唯对客氏百依百顺,良心也教狗吃了,居然将一手把他从险境中救出并扶上龙床的王安,发往南海子净军;客氏“遂矫旨准安辞免,将司礼监印付体乾掌之”{88}。
王安死得很惨。先欲将其饿死,后失去耐心,一说勒死,一说纵狗咬死。王安亲手救过朱由校和魏忠贤,却恰恰由这两人联手消灭。
王安被除,内廷座次全部重新论定。由于客氏这个背景,在司礼监排名第二的魏忠贤,却是整个内廷事实上的核心人物。王体乾首先把自己的位置摆得很正,“故事【惯例】,司礼掌印者位东厂上。体乾避忠贤,独处其下”{89}。自他而下,内廷有头有脸的人物,咸唯魏氏马首是瞻。
应该佩服客氏这个女人,头发虽长,见识却一点不短。她拍板与王体乾结盟,除掉王安。这很有先见之明。干掉王安没多久,就发生了外廷请求皇上将客氏遣散出宫的事件,假设王安仍在,与朝臣里应外合,朱由校十有八九是抵挡不住的。眼下,只是外廷单独闹事,处境就好很多。朱由校和客氏,一起咬住牙关,顶了四五个月,终于击退群臣。天启元年十二月,先将主要干将之一的吏部尚书周嘉谟罢免,翌年三月再驱逐另一干将——大学士刘一燝,六七月间,刑部尚书王纪、礼部尚书孙慎行分遭革职、罢免,十月,都察院两位高层左都御史邹元标、左副都御史冯从吾也被赶走。
七搞八搞,转眼间力量对比的天平就偏向了魏氏集团这一边。这带来什么结果呢?当然是“阉党”的形成。
假使在嘉靖以前,像这样力量平衡的打破,不至于成为产生“阉党”的温床。那个时候,士大夫气节很盛,骨头很硬,不要说一时的逆境不足以让他们俯首,就算到头破血流的地步,坚持抗争者也大有人在。不妨回想一下朱棣篡权之初的白色恐怖,成百上千地杀人,也不曾把大家吓倒。即便到了嘉靖年间,“大礼议”之中,正气也仍占上风,左顺门请愿时有那么多士大夫站出来,不避斧钺和大棒。我曾经说过,明代士风是历来最硬的,没有哪一个朝代比得,非常了不起。可是这么刚正的一个群体,也慢慢地教明代历任君主摧眉折腰,销蚀成明哲保身、贪生怕死甚至卖身求荣的无耻之辈。到嘉靖后期,士风向劣坏方向转化,已是大势所趋;再经万历一朝,基本上都堕落了,正人君子仍有,但与整体比仅属星星之火,天启朝中他们与阉党可歌可泣的战斗,迸射出耀眼然而也是最后的火光,而其命运,则如恩格斯所定义的悲剧:“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90}他们有正义在手,却不合时宜。什么合乎时宜?“趋利”二字耳。道义一旦被摧毁,精神一旦无可守护,人就是唯利是图的动物。天启年间的“阉党”,实起自万历年间的“党争”。彼时,士大夫阶层因政见不同,各为门户{91},此一现象本不足奇,如能良性竞争——例如现代民主政体下的党派政治——其实不失为进步。然而,由于士林的基本精神尺度和原则沦失殆尽,“党争”纯以个人攘权夺利、荣华富贵为宗旨,但能达此目的,不问手段,廉耻全无,遂造成一种极黑暗极卑鄙之后果。崇祯朝进士李清用两句“知”与“不知”概括这种现实:“人知崔【崔呈秀,阉党巨头】、魏,不知朝廷;人知富贵功名,不知名教气节。”{92}
孟森先生对万历年间的“党争”如何演化为天启年间“阉党”的原委,辨析甚明:
至是【天启年】凡宵小谋再起者,皆知帝【朱由校】为童昏,惟客、魏足倚以取富贵,于是尽泯诸党,而集为奄党;其不能附奄者,亦不问其向【从前】近何党,皆为奄党之敌,于是君子小人判然分矣。神宗【朱翊钧】时庙堂无主,党同伐异,以儌利而为之,至是以奄为主,趋利者归于一途,故只有奄党非奄党之别。{93}
自甘供客、魏驱使,参劾王安的兵科给事中霍维华,是“阉党”的首位加盟者,级别不高。第二年,随着周嘉谟、刘一燝、孙慎行、邹元标等重量级反阉人士的倒台,“阉党”加盟者的档次开始提升。自沈——即前面提到过的那个据传与客氏有私的高级官员——始,这档次已提至大学士级别。到天启三年,顾秉谦、魏广微入阁,“阉党内阁”形成;天启四年,以首辅叶向高辞职为标志,“阉党”彻底控制政局,“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94}。
“党”之一字,今义与古义有很大差别。首先,在出现简化字以前,“党”与“黨”本非一字,两者各为一字,前者只用于姓氏,简化后,“党”与“黨”并为一字。其次,“黨”在古时,基本是贬义,从黑,本义为晦暗不明。《说文》曰:“党,不鲜也。”《论语》曰:“吾闻君子不党。”孔颖达注:“相助匿曰党。”古人主要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党”字的。
“东林党”的名称不是东林党人自己命名的,这个晚明的政治派别起源于讲学,以东林书院为学术和思想基地。朱由校、魏忠贤为了安排罪名,把有关的人称为“东林党”,意思是这些人借讲学为名朋比为奸。
毫无疑问,“阉党”更是一种指控,甚至咒骂,里面丝毫没有今天人们所理解的政党的含义,直译过来,大约相当于“附集在被阉割过的人周围的那群丑类”。
这样的咒骂不算诬蔑,事实正是如此。在“阉党”一词中,“党”比较彻底地回归于它的“相助匿”的本义。如果说“东林党”还有自己的政治主张,隐然可见政党雏形,对“党”字开始向近代语义过渡发挥了作用,那么,“阉党”则完完全全是为污浊之个人私利汇聚起来的乌合之众,他们走到一起,与理念无关,与抱负无关,与社会责任和构想无关。
依附魏忠贤的人,不外三类。一是渴望富贵者,二是作奸犯科欲而向魏氏寻求保护者,三是品行低下、为正人君子所排斥而志在报复者。正应了一句话: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魏忠贤就像黑社会老大,吃得开,有靠山,违法的事别人干不得他干得,可以放手作恶。这样,全体的丑类就都赶来入伙,投靠他,为他做奴才和打手的同时,也吃上一份自己的黑饭。
无论怎么看,“阉党”都不是一个政治派别,而像地地道道的犯罪集团。唯一特别之处,一般犯罪集团见不得人、东躲西藏、总是担心被抓获,“阉党”却堂而皇之、大摇大摆地干坏事,甚至整个国家机器都为他们服务——因为有朱由校先生的特许。但尽管连皇帝都表示支持,他们仍然不像一个政治集团,仍然像犯罪集团。这就是历史和社会法则非常可爱的一面:罪犯终归是罪犯,黑社会终归是阴沟里的产物,哪怕全部合法的机构和权力都归他们掌握,也不能由黑洗白。
例如,由魏氏引入内阁的顾秉谦、魏广微,不要说政治家意识,连“做官”的意识都没有,自动把自己摆到魏忠贤家奴的位置,俯首帖耳,唯命是从。“秉谦票拟【起草诏令】,事事徇忠贤指。”{95}职为首辅,实则没做过一日宰相,杨涟送给他一个称号“门生宰相”,这实在还算客气,其实他从来只是魏忠贤的哈巴狗而已。魏广微处理一切政务,都会事先打份小报告,请示魏忠贤,“签其函曰‘内阁家报’”{96},毫不掩饰家奴面目,对他大家也有绰号相赠——“外魏公”,意思是“在外面的魏公公”,不过是魏忠贤的一个影子,根本不把他单独看做一个人。
在这个集团,只有主子和仆从两种人。里面有个叫崔呈秀的人,当时是御史,品质极坏,他因为贪污案子事发,都御史高攀龙、吏部尚书赵南星处理他,他就跑到魏忠贤那里,摇尾乞怜,魏忠贤答应保护他,他则索性自认为魏的干儿子。时下坊间流行一语:“见过无耻的,没见过这么无耻的”,用在崔呈秀身上最恰切——崔呈秀以前,谄附者固然不少,但还没人能够发明以儿子自居的拍马屁手法。因同姓之故,魏广微原先对魏忠贤一直自称“宗弟”,后来赶紧降格,自贬“宗侄”{97}。这种无耻,竟然成为一种攀比,一种竞争。崔呈秀叫魏阉一声爸爸,或已自觉厚颜之极,无人能出其右了,没想到“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后来更有一大堆人把他的“想象力”加以发挥,围着魏忠贤喊“爷爷”——这就是“阉党”十孩儿、四十孙的由来。
不要以为这很丢人。“阉党”内部无人感觉这是耻辱,事实上,能够名列儿孙辈,已属莫大荣耀。到得后期,各地如云的谄附之徒,欲认干爹、干爷爷而不能,连这点“名分”也没有了。
倘若这些人不曾接受过什么教育,也还罢了。但他们大多饱读诗书(一小部分武人除外),对圣贤之言可谓滚瓜烂熟,由此可见,社会风气一旦败坏起来,教育得再好也顶屁用。我前面曾说,历代士风从不见像明代这么正派的,现在我该说,到魏氏弄国之际,历代士风也从不见这么卑下的。知识分子应为一国一民的最优质文化资产的传承人和守护者,他们往往是历史和现实的脊梁,也应该是脊梁,然而某些时代,他们非但一点不起这种作用,反倒最无是非和廉耻。后来大狱兴起之时,是各地普通民众勇敢地站出来声援和抗议。杨涟被押解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