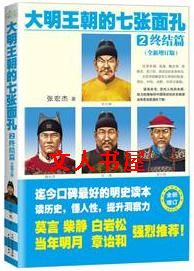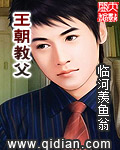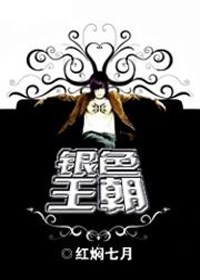龙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第6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古来奶妈界之翘楚,就这样灰飞烟灭了。
魏忠贤
阉祸,这个自永乐以来与明王朝共生共长的毒瘤,到魏忠贤,终于发展到极致,亦就此画上句号。不过,对这样的人、这样的事,读《明史》读到后来,人们可能都有一种厌倦与麻木。因为实在太多,如过江之鲫,连绵不断、层出不穷,以致失去兴趣。我在提笔叙述魏忠贤的故事前,就突然生出无聊之感,从王振想到汪直,从汪直想到刘瑾,从刘瑾想到魏忠贤,二百年间,到处活跃着此辈的身影,专权、恃宠、浊政、殃民,无所不为,以致偶尔不见此辈动静,反倒诧异,会单独地特别指出(例如嘉靖朝)。所以,在司空见惯的意义上,阉祸在明代确实缺乏新意,从内容到形式颇相雷同,本质不变,无非为害或大或小而已,慢慢会让人提不起兴致。
但说到天启、崇祯年间的政治、历史,不说魏忠贤不行。一方面不说不行,另一方面阉祸大同小异又让人心生倦意,怎么办?只好在落笔之前,先去思索和寻找有“魏式特色”的东西。通盘想了一下,觉得“魏式特色”表现于两点:一是登峰造极,二是造就了“阉党”。尤其第二点,是十足和独一无二的“魏氏特色”,《明史》为“阉党”辟出单独一卷(第三百零六卷)、在《列传》中拿出单独一个单元(列传第一百九十四),完全由于魏忠贤——《阉党传》除了开头拿正德年间的几个人凑数外(其实不足称“党”),入传者,全部是魏氏集团成员。
一阉而可以致党,这才是魏忠贤的历史价值与分量之所在,也是这次“阉祸”不得不说之处。没有“阉党”,魏忠贤不过是一个很可恶然而也很普通的丑类,有了“阉党”,魏忠贤顿时提高了档次,一下子超越王振、汪直、刘瑾,把“阉祸”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阉党”的产生,可谓明朝晚期政治的焦点,是精神、道德、风气彻底败坏的标志。也就是说,“阉党”虽因魏氏而起,但所反映的问题,远为广泛、深刻,表明明朝的肌体已整体溃烂。
叙表之前,还有一点尚需澄清:魏忠贤搞出“阉党”,王振、汪直、刘瑾等却不曾搞出来,是魏忠贤特别能干、才具过人吗?绝对不是。魏忠贤其实是个很平庸的人,论才具,休说与“知识分子出身”的王振比,即比之同样不通文墨的刘瑾,亦远不如也——刘瑾专政期间,着实显露了一些政治能力——魏忠贤其人,既无见识,处事也相当拙劣,以他罕见的熏天之势,天启帝崩后居然束手就擒,其愚可知。魏氏独能在明代巨珰之中登峰造极,只是时势使然。第一条,是永乐、宣德以来形成的倚信太监的政治机制;第二条,是嘉靖以来士风严重椓丧堕落;第三条,是赶上熹宗那等极度缺心眼儿、“至愚至昧之童蒙”{73}的皇帝。有此三条,魏式人物必然出现,而不在于是谁。甚至可以推断,幸而此人是憨头憨脑的魏忠贤,假若换做另一个见识、处事都更厉害的角色,朱明的天下极可能就被别人夺了去,而不能再苟延残喘近二十年,思宗朱由检连充当亡国之君的机会都不会有。
魏忠贤,直隶(河北)肃宁人。其父亲名叫魏志敏,母亲姓刘。{74}他娶过妻子,生有一女。他的为人,《酌中志》和《玉镜新谭》的描述出奇一致,咸用“亡【无】赖”一词。怎样一个“无赖”法?道是“游手好闲,以穷日月”,“日觅金钱,夜则付之缠头【客人付与艺伎的锦帛,白居易《琵琶行》:“五陵年少争缠头。”代指买欢】”,“邀人豪饮,达日不休”,{75}“孤贫好色,赌博能饮”{76}。总之,他虽然出身贫贱,却生就一副纨绔子弟性情,从来不务正业,唯知声色犬马。
这样鬼混了几年,他又做出一项惊人决定:自宫。关于此事缘起,说法有二。《明史》说:“与群恶少博,少胜,为所苦,恚而自宫。”{77}亦即因为赌博欠债,走投无路而自宫,以便入宫混碗饭吃。《玉镜新谭》则记为:“忽患痬【疡】毒,身无完肌,迨阳具亦糜烂焉,思为阉寺【太监】,遂以此为净身者。”{78}后说虽不为正史采,却似乎更合于情理。
明代宫廷,每隔数年,会增补数千名太监,基本取自畿辅之地的河北。此地民贫,居然因此形成一种风俗,“专借【入选宫中】以博富贵”。本来按正常程序,应该先向官家报名,录取之后再行阉割,洪武时还规定,“擅阉有厉禁,其下手之人,罪至寸磔”。但长久以来,此禁实际已“略不遵行”,北京周遭州县,自宫成风,“为人父者,忍薰腐其子,至有兄弟俱阉,而无一人入选者”,每次入选人数与擅自自宫者之间的比例,仅为十分之一,大多数自残之人只好沦为乞丐甚至抢劫犯。沈德符北上来京途中,一过河间、任丘以北,经常于“败垣”之中得见此辈,他心惊肉跳地写道:“聚此数万残形之人于辇毂【圣驾】之侧,他日将有隐忧。”{79}
自宫的魏忠贤,便是这“数万残形之人”中的一员。他显然也没有能够立即入选,度过一段“丐阉”时光。“敝衣褴褛,悬鹑百结,秽气熏人,人咸远之。竟日枵腹,无从所归……昼潜僻巷乞食,夜投破寺假息。”{80}老婆也弃他而去,不知所终。
但他总算运气不错,流浪一段时间后,进入某内宦府中充当伙夫,担水烧火,因做事“獧捷”,赢得赏识,替他打通关节,于万历十七年——是年二十一岁——入选宫中,终不致枉然自宫一回。
虽然进了宫,但魏氏一直处在太监群体底层。“选入禁中为小火者,盖中官最下职,执宫禁洒扫负荷之役。”{81}做最脏最苦的清洁工、搬运工,跟从前吃同一碗饭,无非从宫外挪到宫内而已,一干就是许多年。
而他恶习不改,在宫中仍旧与人赌博、相邀嫖妓。曾因手头窘迫,远赴四川税监邱乘云处“抽丰”(借钱)。邱乘云与他同出于大太监孙暹门下,宫中规矩,净身入宫者都要分在某高级宦官名下归其管理,其关系“犹座师之视门生”,因此魏忠贤与邱乘云相当于同门之谊,这才不远千里跑去求助于他,但因事先太监徐贵把魏忠贤素日种种无赖告知邱乘云,令邱心极厌恶,待魏到来,不但不给钱,反把他吊在空房中三天,险些饿死。这件事说明:第一,魏氏进宫后境遇基本没有改变,很长一段时间仍然维持着百无聊赖的“流氓无产者”生存方式;第二,他毫无地位,邱乘云并非高级宦官,但魏氏距他尚有十万八千里,以致邱可随意取他性命——以这情形推测,魏氏本无可能爬至后来的高位,之所以能那样,实为运气极好的奇迹。
魏氏在四川被和尚秋月所救。秋月劝说邱乘云发十两银子作为路费,打发魏回京,又致书所熟识的内官监(宫廷基建处兼总务处)总理马谦。马谦是个好心人,魏忠贤私自出宫,是重罪,马谦看他可怜,兜住此事,并让他到甲字库(宫廷染料供应科)落脚,仍旧干清洁工、搬运工。
魏氏时来运转,是在万历末年。他年逾五旬,在宫中打杂已三十来年,眼看这辈子就这么交代了。那时,朱由校生母王氏“无人办膳”,魏忠贤运作一番,得到这份差事。对他来说,跟以往在宫中纯粹做苦力相比,不失为一种改善。但绝不是什么美差。盖因当时太子朱常洛,也如同乃父万历皇帝昔年一样,由于替自己生下长子的女人身份低贱而对其极其冷漠,所以王氏才落到“无人办膳”的地步。奴才的贵贱,全视主子的荣辱而定;给如此边缘化的主子当奴才,不可能意味着有远大前程,稍有能耐和靠山的人,都瞧不上这份差事。魏忠贤愿意给王氏烧火做饭,只觉境况稍强而已,不存更多奢望。但,王氏毕竟乃皇长孙生母,由这条线索,引出其他千丝万缕的关系,不知不觉间,谁都不放在眼里乃至谁都可以踹上一脚的老魏头,命运一点一点地发生着变化。
首先,他得以“亲密接触”当时的小皇孙、日后的天启皇帝朱由校,经常设法弄来“财物、玩好,以至非时果品、花卉之类”,“转献先帝【指朱由校】”{82},在朱由校童年记忆中占据有利位置。其次,由于工作,他先是结识了太子朱常洛的心腹太监王安手下的红人魏朝,与之八拜成交;进而与魏朝的“对食”——朱由校奶妈客氏接近,彼此除工作关系外,又有了私下来往的理由与空间,以至暗中“相厚”——这种关系后来成为他崛起的最坚实基石。第三,万历四十七年,王氏病亡,朱常洛所宠爱的李选侍认为失去母亲的朱由校奇货可居,争得了对朱由校的监护权,这样,魏忠贤作为服务人员一同进入李选侍宫中,不久就在光宗(朱常洛)去世后的“移宫案”中充当重要角色,虽然险些因此完蛋,但这番经历却是他真正走上政治舞台的开端,对扭转自己一贯的卑微心理,唤醒对权力的渴望和野心,极具价值。
这段经历的重要,不在于魏忠贤能捞到多大实际好处,而在于帮助他完成了从“小人物”向“风云人物”的心理转变。
魏这个人,刘若愚有几句话{83},把大家对他的看法、印象归纳了一下——当然,是宫中那些知根知底的老相识的看法、印象,至于他发达起来以后外面人的看法、印象,肯定就是另一种样子了。
刘若愚说:“忠贤,少孤贫,好色、赌博、能饮。”这是一个侧面的概括。好色,酷爱赌博,酒量大。这三个特征很突出,在同事中间是出了名的。
又说他平时的为人“啖嬉笑喜”,是个挺快活、挺随和或者挺没正经的人,涎皮笑脸,打打闹闹,滑稽圆通。如果把这看成一种身体语言,它通常出现在社会地位低下,意识到自己的身份、能力和处境比较弱势的人身上。一方面是自我保护、防卫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主体的不自信的心理。反之,一个人感到自己很强势,断不会在人前采取这样的姿态和形容——谁见过“大人物”们的脸上,会有一副“啖嬉笑喜”的表情呢?
还有两个评价:“担当能断”、“喜事尚谀”。前者讲他够义气,敢作敢当,冲动;后面则讲他爱出风头、特别爱在出头挑事之后接受别人的吹捧。这两种表现,也都透露了魏忠贤的社会处境和内心秘密:有一种长期被人瞧不起的焦虑,很需要以强烈、引人注目的举动来寻求补救,证明自己;这些举动,时常带有轻率和刻意的色彩,目的就是取得群体的认可,并且迫切地渴求表扬。一般来说,这不是在社会或人群中享有优越、稳固地位与声望的人之所为。
他还喜欢“鲜衣驰马”,炫耀膂力和箭术(他似乎是一个左撇子,“右手执弓,左手彀弦”,通常多是左手执弓、右手拉弦),且“射多奇中”——看来,这是能够带给他“英雄主义”自我感受的不多的一个方面,故而尤为热衷于表现给人看。
总的来看,魏忠贤素日举止既不得体,心态也不沉稳,轻躁易激,多动少安,心虚气浮。这样的人,很难令人敬重,也不值得惧怕、避让,相反,一看即知骨子里乃是一个十足的“小人物”。所以大家对他的态度,多为轻视戏蔑,从没人把他当回事,“人多以‘傻子’称之”。
“傻子”的外号,活画出魏氏发迹前的卑微可怜,以及他在众人心目中的地位。从事后看,魏的“傻”,并非智力缺陷,并非缺心眼儿,而是卑微可怜的地位折射到心理和行为上,使别人对他产生轻视。
这样当然也有好处。朱由校让客氏在二魏中挑一个替自己“管事”,她做了一番比较:魏朝“狷薄”,而魏忠贤“憨猛好武,不识字之人朴实易制”。狷薄是固执、偏拗、器量狭小、不宽容、难相处;魏忠贤没有这些毛病,“憨”而“朴实”。这与其说仅仅是性格不同,不如说也很符合他们各自在宫中的地位,而客氏在这里则本能地流露了一点女权意识,在两个“男人”间,挑选了比较弱势的一个。
傻人有傻福。这种“傻”,这种“憨”,不单使他赢得最有权势的女人的芳心,进而更享受着这女人亲手替他安排的飞黄腾达的前程,“逾年由小火者躐进【越级提升】司礼监”{84}。与一般想象的不同,这颗政治巨星的诞生,主要并不是他本人孜孜以求的结果。从对史料的分析来看,久已养成的“小人物”心态,起初严重制约了他的野心;当巨大的权力摆到他面前时,他甚至显得木讷,并没有扑过去一把攥在自己手中。
朱由校即位后,政治格局自然重新洗牌,外廷内廷都面临一系列人事变动。在内廷方面,最重要的司礼监的领导位置,显然非王安莫属。朱由校也的确发表了这样的任命。王安接到任命,上表辞谢,这本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