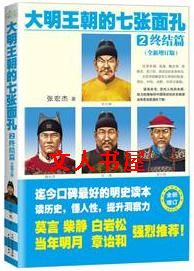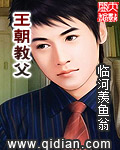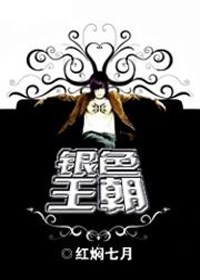龙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第4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重上江西捷音疏
十五年七月十七日遵奉大将军钓帖
照得先因宸濠图危宗社,兴兵作乱,已经具奏请兵征剿。间蒙钦差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后军都督府太师、镇国公朱【朱厚照及其自封的所有头衔】钧帖,钦奉制敕,内开:“一遇有警,务要互相传报,彼此通知,设伏剿捕,务俾地方宁靖,军民安堵。”
……
续蒙钦差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后军都督府太师、镇国公朱统率六师,奉天征讨,及统提督等官——司礼监太监魏彬、平虏伯朱【江】彬等,并督理粮饷兵部左侍郎王宪等,亦各继至南京。
臣续又节该奉敕【官样文字,大意就是接到皇帝命令】:“如或江西别府报有贼情紧急,移文至日,尔要及时遣兵策应,毋得违误,钦此。”俱经钦遵外【官样文字,指皇帝命令全都得到遵行】。
王守仁,这位中国历史上数得着的大哲学家,以心学著称于世的明代大儒,在这里被逼说谎。不知他草疏之际,是如何面对自己“致良知”的学说的?上述文字,想方设法表达了一个意思,即:平定叛乱的伟大胜利,完全是在英明统帅朱厚照亲自关怀、亲自部署和亲自指挥下取得的;胜利属于“大将军”,属于“大将军”的正确路线。
将朱宸濠这“战利品”收入囊中,朱厚照便安心在南方游乐,“讨逆”直接转化为虐民,到处搅得鸡飞狗跳。这是他在“温柔富贵乡”扬州时的情形:
经【太监吴经】矫上意【曲解、假托朱厚照的用意】,刷【搜觅】处女、寡妇。民间汹汹,有女者一夕皆适人,乘夜争门逃匿不可禁。
……经遍入其家,捽【揪】诸妇以出,有匿者破垣毁屋,必得乃已【罢休】,无一脱【幸免】者,哭声振远。{148}
而《明史》中的记载,除上述情节外,还说“许以金赎【准许被抢的妇女用钱赎身,敲诈】,贫者多自经【上吊】”{149}。——如此大弄,当然不是什么“矫上意”,没有朱厚照的旨意,一个太监,借他一个胆儿也不敢。扬州“有女者一夕皆适人”这个经典瞬间,被晚明小说家写入故事《韩秀才乘乱聘娇妻》,此篇收于《初刻拍案惊奇》,其中说:
又过了一年有余,正遇着正德爷爷崩了,遗诏册立兴王【嘉靖皇帝原为兴献王世子】。嘉靖爷爷就藩邸召入登基,年方一十五岁。妙选良家子女,充实掖庭。那浙江纷纷的讹传道:“朝廷要到浙江各处点绣女。”那些愚民,一个个信了。一时间嫁女儿的,讨媳妇的,慌慌张张,不成礼体。只便宜了那些卖杂货的店家,吹打的乐人,服侍的喜娘,抬轿的脚夫,赞礼的傧相。还有最可笑的,传说道:“十个绣女要一个寡妇押送。”赶得那七老八十的,都起身嫁人去了。但见十三四的男儿,讨着二十四五的女子。十二三的女子,嫁着三四十的男儿……
将正德的事安到嘉靖头上,只是小说家避实就虚的小滑头,而这一幕确确实实发生在正德十四年十二月的扬州府。近代诸多戏曲剧种如粤剧、潮州戏、黄梅戏等,都将此情节搬演成戏,名《拉郎配》,香港亦曾出品根据粤剧改编的故事片,近年又有央视制作的电视剧《拉郎配》。如今,“拉郎配”作为荒唐的同义词,在生活中广为运用,但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始作俑者便是这位正德皇帝朱厚照。
在南方朱厚照尽兴玩乐,流连忘返。直到第二年十月下旬,才携着他的“战利品”回到北京。一路之上,“每令宸濠舟与御舟衔尾而行……及至通州,谓左右曰:‘吾必决【亲自审断】此狱!’”{150}对他来说,这些现已写入自己功劳簿的“战利品”,是一生荣耀的顶峰,他必会大张旗鼓加以张扬,以让世人尽皆拜倒在他的丰功伟绩之下。八月,离开南京之前,他就曾专门搞了一个献俘仪式,但他不厌其多,注定会搞第二次——在北京,这个他诞生的地方。他命礼部、鸿胪寺的负责官员,足足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来研究和准备北京的献俘仪式。待得一切停当,十二月十日,朱厚照以亲自押送俘虏的方式,正式回归皇城(此前一直驻跸通州)。遥想当日,颇有威尔第歌剧《阿伊达》第二幕终了前奏响《凯旋进行曲》、高歌《光荣啊,埃及》大合唱时的壮观。《武宗实录》描述了当时的场面,为使读者更真切地感受其情景起见,今将原文转为现代语言如下:
皇帝终于回到京城,文武百官整整齐齐地守候在前门外正阳桥的南侧。这一天,军容大耀。皇帝一身戎装,策马而至,到了正阳门下,掉转马头,笔直地坐在马背上,注视着远方。但见那些叛乱者以及他们的家人,有数千人之多,被押着逶迤于道,然后顺序陈列在马路【即今之北京前门大街】东西两侧示众。所有罪俘脖子后都被插上白旗,上面书写着犯人姓名。已被斩首者的头颅,则被悬吊在竿子上,也插上白旗。一眼望去,数里不见头。皇帝就这样在正阳门下,一动不动,检阅良久。待皇帝回宫,浩大的俘虏队伍又特意被安排经东安门【今不存】穿越大内而出……这一天,北京城就像被白色所覆盖,举目眺望,四下皆白。
经历了这一时刻,朱厚照的光荣与梦想就走到了尽头。仿佛上天安排好了似的,“威武大将军”朱厚照用这样的场面做了他的人生谢幕。重返皇城和献俘仪式后的第三天,朱厚照一病不起,病情延宕了两个月,终在豹房一命呜呼。对于这样一个人来说,能够这样地死去,也就不能算太窝囊。
研究朱厚照的心理,我一直认为他的成长发生了严重的障碍,以至于人格上的“断乳期”迟迟不能结束。虽然已经二三十岁,但行事的态度和方式实质仍是儿童的。细细分析一下,不难看出他所谓的“尚武”不过是男性幼童对“骑马打仗”的普遍兴趣的延续,想当然、逞性妄为、全然不考虑主客观条件、缺乏计划和目的性……这些表现,与真正的理性的军事行为毫不相干,而只是一个男孩子的娱兴活动。在他眼中,军事从来不是一种科学,需要才智、理论,需要思考与研修。他认为,将军和统帅是想当就可以当的,任何人,随时上马提枪,便可以行征伐之举、打胜仗。最足以表明战争于他不过是场游戏的,莫过于南征朱宸濠这件事,他毫不在乎军事过程本身,而欣然接受一种纯粹表演性质的仪式,当他一本正经将别人俘获的敌人当做自己的战利品接受下来,并一再为此举行受降仪式的时候,整个场景已经完全戏剧化、虚拟化和游戏化,而他身处其间不过是行使一个演员的扮戏的本分,由此来取得快乐。这正是儿童时期人人爱做的“过家家”游戏的另一情节的版本。
人格存在缺陷,这种情形极普通。倘搁在平常人身上,可任由他在成长中和社会的磨炼、砥砺中,自行弥补和改善,抑或求助于医师,慢慢地加以纠正,并不是多么可怕的事情。但当它们发生在一个皇帝身上,就变得有些可怕。因为做皇帝者,只要他不乐意,是可以拒绝任何纠正的,无论来自社会还是来自医师,谁都不能给他一点教训,或让他明白与承认自己的缺陷。其次,皇帝一旦做了便是终身制,不会像别人那样,做得不好或不合适,就被换掉——他会一直做下去,不论他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多大不便,后者却只能注定去忍受。专制与独裁的害处就在这里,国家和人民的福祉,只能仰仗皇帝这个人本身没有太大毛病,一旦不能这样,却并没有任何制度可以化解他个人对国家和人民的伤害。于是帝王的性格、性情、爱好以至癖好,就不再仅仅是他个人的私事,而成为国家政治的基本层面。如果不是皇帝,朱厚照尽可以耽于他各种不切实际的梦想,他心理和人格上迟迟不能摆脱“断乳期”也只是他个人的不幸;然而这一切与皇帝权力捆绑在一起时,整个国家都在为其支付高昂费用。当意识到朱厚照耗去国家大量物力的所谓“西征”,只不过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所玩的一次“超级骑马打仗”游戏,我们心里当是何种滋味?
双“宝”合体
朱厚照怎么死的?说起来也让人哭笑不得,他的死,起因于嬉水。
从南京返程途中,九月初九,朱厚照一行抵达苏北清江浦。这位贪玩的皇帝,“自泛小舟,渔【钓鱼】于积水池。舟覆焉,左右大恐,争入水中,掖【架着胳膊】之而出”。就是说,落水之前,小舟上只有他自己,而他显然是只旱鸭子,不谙水性,否则一片叫做“积水池”的小水不至于应付不了,还需要别人下水抢救。正因此,他所受惊吓应该不小。同时,这年有闰八月,九月实为平时的农历十月,而农历十月换算成公历应该已是十一月份,虽然并非北国,十一月的苏北却也寒意初上了。冷水一激,加上极度惊吓,身心内外交逼,长期酒色无度以及旅途劳顿等诸多因素,也一道发生作用,“自是,遂不豫【生病】”{151}。
事情怎么看都有些滑稽。这个三十岁的大男人,很适合给自己买一份“儿童意外伤害”保险。
病情的发展,没有记录。唯一涉及具体病症的一笔,是北京献俘礼后第三天,朱厚照在天坛主持天地大祀,举行第一遍献礼时,“上拜,呕血于地”{152}。“仆【倒伏】于地,斋宫礼不克终【没能完成】。”{153}既然吐血,大约属于肺疾。
此后便在苟延残喘中,挺过了十二月和正德十六年的一月、二月。
三月十四日,“上崩于豹房”。《武宗实录》对全部过程的记述如下:
先一夕【三月十三日晚间】,上大渐【病情加剧】。惟太监陈敬、苏进二人左右。乃谓之曰:“朕疾殆不可为矣。尔等与张锐【东厂提督太监,口碑最坏同时也是朱厚照最信任的宦官之一】,可召司礼监官来,以朕意达皇太后【母后张氏】——天下事重,其与内阁辅臣议处。之前事,皆由朕而误,非汝众人【指众近幸】所能兴也。”尔俄,上崩。敬、进奔告慈寿皇太后,乃移殡于大内。{154}
这番临终遗言,看上去可疑,每一句都不大像朱厚照可能说的话——比如说,没心没肺之如他,居然对自己的一生流露出了忏悔之心。尤其是这些话尽出仅有的两个在场太监之口,全然是不可考辨的孤证。玩其语意,无非两点:一是授权张氏与内阁大臣决定一切大事;二是为阉宦之流开脱,而将错误统统揽于自身。这两层意思,受益人是谁,一目了然,令人极疑其为太后张氏与大太监们据各自利益达成某种妥协的结果。
疑点还在于,朱厚照是从十三日晚间病情加重的,死亡时间大约在次日凌晨(这一点记载不详,更见可疑),其间应该尚有二三个时辰,完全来得及召见重臣或通知张氏等到场,但事实却是“敬、进奔告慈寿皇太后”——亦即一直等到朱厚照已死,才由陈敬、苏进两个太监跑去通知张氏。这个明显存在漏洞的情节,背后有三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有人压下朱厚照病危的情况不报——比如张锐和司礼监首脑,但绝不会是陈、苏这两个级别较低的太监——以便独掌朱厚照最后时刻的秘密。第二种可能:并不是等朱厚照死后,才由陈、苏将消息通报外界;相反,朱厚照死前有人来过,与太监们就若干事宜有所谋议。第三种可能:朱厚照一命亡归之际,身边确实只有陈、苏两人(或者加上张锐、司礼监首脑等其他太监),没有亲人,没有大臣——原因仅仅是,朱厚照早有吩咐,根本不想见后者。
有关第三种可能,我们发现两个月前刑科给事中顾济曾上书朱厚照,隐然指责他疏隔骨肉母子之情:圣体愆【失,丧失】和,中外忧惧。且人情之至亲而可恃者,宜【应该】莫如子母室家。今孤寄于外,两宫隔绝,至情日疎【疏】。陛下所恃以为安者,复何人哉!{155}从这奏章来看,不但朱厚照死时张氏可能不在场,就是他罹病并走向死亡的整个期间,母子都不曾相见。这确实超出人之常情以外,非极深的隔阂不足以解释。在此,我们的思绪不能不又回到故事开始时的“生母之谜”。这件事,虽为历史悬案,但在朱厚照生命之最后时刻,他的作为却仿佛在专门向我们揭示谜底。而逆向推论,正因为如此,从张后这方面说,她必须未雨绸缪,牢牢抓住时机,在朱厚照将死未死之际,控制局势,搞定皇位继承人(朱厚照膝下从无一儿半女),阻止可能的不利情形发生,以保全自己。她不会傻乎乎地呆在慈宁宫,对这个并非亲生的皇帝儿子掉以轻心;她或许的确从未亲自前去探视过朱厚照,但并不意味着她不可以暗中派人随时了解豹房的动静,在第一时间取得情报。事实上,她早已就指定皇位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