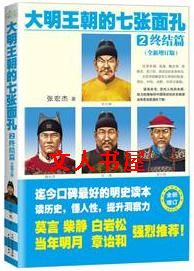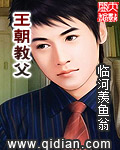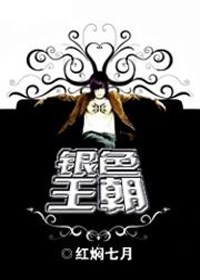龙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第3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自古帝王到从谏为圣,拒谏为失。国家治乱,常必由【因】之。顾【向来】顺旨之言易入,逆耳之言难受【采纳】。故治日【政治稳定的时候】常少,乱日常多。臣等每以此说进于陛下,诚欲陛下为圣德之君,天下成至治之世也。今文武公卿台谏,合词伏阙,皆谓盐法不可坏,而圣意坚执排群议而行之……臣等岂不知顺旨者有宠、逆耳者获罪,若贪位恋禄、殃民误国,则不独为陛下之罪人,抑亦为天下之罪人、万世之罪人矣。区区犬马之诚,犹望陛下廓【开拓,扩大】天地之量,开日月之明,俯纳群言,仍从初议,以光圣德,天下幸甚。若以臣等迂愚不能仰承上意,则乞别选贤能以充任使,将臣等放归田里,以免旷职之愆【过失】。{56}
辞呈中三人虽然自斥无能,但字里行间分明说,唯有皇帝应对此事负责。
也许,朱厚照唯一未尝料到的,便是内阁居然全体请辞。他毕竟年龄尚轻,登基方才年余,政治上毫无经验不说,连在朝臣中物色、培养“自己人”也根本来不及,一旦三老撂挑子,千头万绪自己如何应付得了,更何况以三老的影响,此事的后果将绝不仅仅是他们的离去……我们虽无从知道接到辞呈后正德的内心世界,但想必他经受了一场羞怒交加的感情风暴——因为最终在三辅臣辞职的压力下,他被迫宣布:接受户部方案,半与价银,半与盐引。
危机虽得暂渡,却可以想象正德与他的文官系统从此势不两立,结了极深的梁子。大臣们的做法固然有例可循,正德却不免感到被要挟的滋味,毕竟他乃新君,立足未稳,在此之际,竟遭内阁以集体辞职逼己就范,也确有身陷绝境之痛。
俗话说“君无戏言”。朱厚照头天还那么强硬地甩下“此事务要全行”的话,第二天便在内阁辞职的威胁下改弦易辙,虽然事后朝臣给他戴上“从谏如流”的高帽子,来帮他遮羞,但他内心恐怕只会想到“奇耻大辱”四个字。仅隔一个月,当那场大政变爆发的时候,我们尤其感到,正是崔杲奏讨盐引事件把正德君臣矛盾推向极致,从而点燃了导火索。
在朝臣一方,也许解读有误,以为正德真的“从谏如流”,也许是想趁热打铁,抓住有利时机重创皇帝身边群小,也许两者兼而有之——总之,在赢得盐引这一回合的胜利之后,他们“把斗争引向深入”,矛头所向由事到人,从低级别太监转向正德最倚信的几个核心太监,即有名的“八党”——明代“八人帮”。
所谓“八党”,指环绕在正德身边的八位高级宦官刘瑾、马永成、谷大用、魏彬、张永、邱聚、高凤和罗祥,此八人自正德登极以来不单诱其堕落,实际上也渐渐控制了他。朝臣普遍认为,新君即位以来“圣学久旷、正人不亲、直言不闻、下情不达”以及“朝令夕改”“政出多门”{57}诸状,根子就在这八人身上。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应该乘盐引事件之东风,解决“八党”问题,斩草除根。
于是,“健等遂谋去‘八党’,连章请诛之。言官亦交论群阉罪状”{58}。盐引事件结束之后的一个月内,斗争达到白热化。以三辅臣为首,群臣奏章雪片似的飞来,攻势甚猛。一时间,朱厚照颇难招架。为缓兵计,他派朝臣并不反感的司礼监太监李荣、陈宽、王岳等,前往内阁说情、讨价还价,先说“朕将改过矣,其为朕曲赦若曹”,遭到拒绝后,朱厚照索性祭出“鸵鸟大法”,对大臣奏折“留中不出”。然而,当户部尚书韩文挑头递上由各部大臣签名的奏疏时,朱厚照再也坐不住了。
这个韩文,前面我们已经认识他。在盐引事件里,他领导的户部首当其冲,站在与皇帝和太监斗争的第一线。可能因为他是管钱的,对于那些内幸如何靡费、贪污和侵损国家财政,了解更加深切,感受更加强烈;据说他每每奏完事从朝中退下,对僚属们谈及这些事,“辄泣下”{59}。他手下有一个人叫李梦阳,时任户部郎中。说起李梦阳,那可不是等闲之辈,虽然他居官不高,却乃当朝有名的大才子,以他为首的“前七子”是明代文学最重要的流派之一,所有搞文学的人耳熟能详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便是他所提出的文学主张。此人做官也是一个“刺儿头”,骨头相当硬。早在弘治年间,即曾因弹劾张后兄弟、“势若翼虎”的张鹤龄而坐牢。当日,三阁老并言官等交相上书猛攻“八党”之际,韩文在户部与一班下属亦倍加关注,日日谈论,说至慷慨激昂处,韩文免不了又是涕泗横流——这时,李梦阳在旁冷冷开了腔:“公大臣,义共国休戚,徒泣何为?谏官疏劾诸奄,执政持甚力。公诚及此时率大臣固争,去‘八虎’易易耳。”一语甫出,激得韩文气血上涌,“捋须昂肩,毅然改容”,赞道:说得好!“纵事勿济,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报国。”
一个重大的行动当即酝酿成型:第一步,由韩文领衔、李梦阳执笔、经众同僚讨论修改,草成一疏,在朝中广泛征集签名之后,上奏皇上;第二步,上疏后的次日早朝,将由韩文领头,偕九卿、阁员等重臣及百官,伏阙请愿,直至皇上下旨拿办“八党”为止。
想那李梦阳何等人也,由他担纲草疏,分量力度岂是泛泛可比?在《明史》里我们可以读到这件直接导致明代一场大政变的著名奏章,其云:
人主辨奸为明,人臣犯颜为忠。况群小作【为】朋,逼近君侧,安危治乱胥【都;皆】此焉关。
臣等伏睹近岁朝政日非,号令失当。自入秋来,视朝渐晚。仰窥圣容,日渐清削。皆言太监马永成、谷大用、张永、罗祥、魏彬、丘聚、刘瑾、高凤等,造作巧伪,淫荡上【指朱厚照】心。击球走马,放鹰逐犬;俳优杂剧,错陈于前。至导万乘【君上】与外人交易,狎昵媟亵,无复礼体。日游不足,夜以继之,劳耗精神,亏损志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气靡宁。雷异星变,桃李秋华。考厥【突发状,指上述“异象”】占候【自然气候】,咸非吉兆。
此辈细人,惟知蛊惑君上以便己私,而不思赫赫天命、皇皇帝业,在陛下一身。今大婚虽毕,储嗣【皇位继承人】未建。万一游宴损神,起居失节,虽齑粉若辈【指群小】,何补于事。高皇帝【朱元璋】艰难百战,取有四海。列圣【指过往明朝历代皇帝】继承,以至陛下。先帝临崩顾命之语,陛下所闻也。奈何姑息群小,置之左右,以累圣德?
窃观前古奄宦误国,为祸尤烈,汉十常侍、唐甘露之变,其明验也。今永成等罪恶既著,若纵不治,将来益无忌惮,必患在社稷。伏望陛下奋乾刚【刚健的天道】,割私爱,上告两宫【父皇、母后】,下谕百僚,明正典刑,以回天地之变,泄神人之愤,潜削祸乱之阶,永保灵长之业。
确实是大手笔,奏章写得气势很盛,不容辩驳。开篇即以君臣大义立足,正气凛然;随之迅即一一点出“八党”之名,以一连串精炼有力的“四字句”,述尽他们的胡作非为;进而转入对朱厚照的“劝谏”,指出无论从自爱还是仰体祖宗创业之艰、先帝顾命之嘱的角度,“姑息群小,置之左右”都是有违做皇帝的责任和道德的;最后,则鉴之以史,用历史事实说明“奄宦误国,为祸尤烈”,“若纵不治”“必患在社稷”。通观全文,天理、人伦、历史全站在作者一边,正德里外不是人,简直一无是处。但更要命的是,奏章摆出了“清君侧”的架势,正德虽不喜读书,历史上一些“清君侧”典故还是知道的,而且他的直系祖宗朱棣当年就是打着“清君侧”的旗号把建文帝赶下台,眼下,掂量掂量韩文本章里的用词,年少无助的他难免心惊肉跳。而比写在纸上的言语更令他惊惶的是,满朝官员这次采取了联合行动,伏在宫外请愿,志在必得,一定要将“八党”“明正典刑”。
朱厚照再次派王岳等前来谈判,这次开出的条件是,且留“八党”小命,将其发往南京“闲住”。所谓“闲住”,是明宫对获罪太监的一种处置方式,相当于流放。朝臣方面坚决不同意,正德就反复派人来磨泡,据说“一日三至”。最后一次,刘健忍无可忍,掀了桌子,恸哭道:“先帝临崩,执老臣手,付以大事。今陵土未乾【干】,使若辈败坏至此,臣死何面目见先帝!”{60}王岳见状,知群臣此番倒“八党”决心已定,乃与衔旨同来的另两个太监范亨、徐智当场表示,他们赞成阁议,将回去密奏皇上明晨逮捕“八党”。史书上称王岳等“素忠直”,未必可信,比较可能的是,王岳等作为“八党”之外的内臣,在权力争夺上与后者素有隙怨,满朝上下齐心合力欲除“八党”,本亦正中下怀,刘健的坚定不移,更让他们打消疑虑,乃欲与朝臣里应外合,扳倒“八党”。刘健等意外得此奥援,信心倍增,以为大局已定。
古往今来,历史多次因某个小人而中间改道,此刻复如是。
却说当时在场有一人,姓焦,单讳一个芳字。此人乃一地道小人,《明史》给他如下评语:“粗陋无学识,性阴狠。”{61}正德改元,他靠谄媚做了吏部尚书,犹嫌不足,冀更上爬,加之跟刘健、谢迁不合,久有龃龉,所以虽然迫于时势而在朝臣倒“八党”运动中参与其事,内心却极不愿看到此事最终告成,因为显而易见,此事一旦告成则刘谢势力必然益发强大稳固。那日,一旁听了刘健与王岳们的计议,焦芳不禁暗中转动着脑筋。他以一个小人的天性以及独到判断,认定从本质上说,世上万事应该是“正不压邪”——只要“邪恶”一方有所防备,“正义”向来输得很惨。他觉得眼下就是这样一个可以押宝的关头,他选择把宝押在“邪恶”一方。就像三百年后的晚辈袁世凯一样,焦芳用来下注的本钱也是告密。他在第一时间把王岳与刘键密谋奏请皇上逮捕“八党”的消息,捅给“八党”。王岳还没来得及去见正德,“八党”一干人早已把正德团团围住,痛哭流涕,并将王岳等如何与外臣交结、合谋剪除异己的情状诉诸正德,其间,少不了添油加醋一番,以使正德形成这样的意识:除“八党”是假,这些人真正的矛头是对着皇上,必欲将其架空,然后任意摆布。
自韩文本章呈上后,正德一直在惴惴不安中度过,对方来势汹汹也若此,年仅十五岁的他自然又惊又怕,传说被吓得啼哭起来,连饭都不吃{62}。此刻又听到发生内廷、外臣相勾结的事,直有末日临头之感。
王岳支持朝臣的举动,犯了大忌。明制,内官不得与外廷交结,违者死。其实王岳等人实在有些冤,因为原本是正德派他们去内阁协调此事,并非私下暗通。但经“八党”一渲染,好像就变成了王岳背着皇帝伙同刘健另有图谋。
“八党”缠了正德一夜,先是哀求,待知性命无忧后,则转守为攻——告诉正德如何反击,而这恰恰是正德的燃眉之急。其间,刘瑾表现出他在此曹中见识过人的一面,他的分析直捣要害:朝臣为什么敢这么肆无忌惮地哗闹?根本原因是“无人”,是皇上没有在关键位置上安排自己的人!“有则惟上所欲为,谁敢言者!”{63}的确,“八党”虽受宠信,但其职守皆非要害,比如刘瑾,只是钟鼓司掌印太监——除了掌管每日上朝的钟鼓(说得不好听,就是敲钟的),再就是负责调教乐工、搬演杂戏。
刘瑾一点拨,正德豁然开朗。是啊,一旦在重要位子上都安排自己人,今后哪还会担惊害怕、受制于人?瞬间,他心头阴云一扫而空。正德立即颁旨,拘捕王岳、范亨、徐智,由刘瑾取代王岳入掌司礼监{64}兼提督团营,调丘聚提督东厂、谷大用提督西厂,张永等并管京营事务。至此,内廷中枢以及京城主要特务机构和禁卫军,全落“八党”掌中,一场彻底的大政变就这样在夜幕掩护之下悄然发生……
然而,宫掖外,以为稳操胜劵的刘健对此木然不觉,他还这样对身边因久候无果而有些焦躁的群僚说:很快便有好消息,大家只需再坚持坚持。(“事且济,公等第坚持。”{65})
毕竟是书生!
正德元年十月十三日清晨,候在左顺门外的百官终于看见了内使的身影,然而当宣读圣旨时,人们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旨意宣布,皇帝赦宥刘瑾等八人,并对他们的职务做出新的任命;旨意还强调指出,这是皇帝的最终决断。
天翻地覆的激变!所有人措手不及,呆若木鸡。刚才还信心满怀的刘健,惊讶得说不出话来。现场一片寂静,没有激愤,甚至连一点骚动也看不见,因为事情以人们最不可能设想的局面画上了句号,就像对弈的时候对方弈出匪夷所思的一招,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