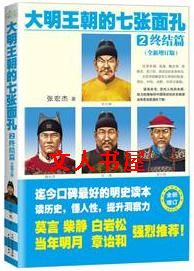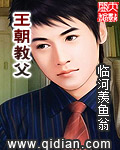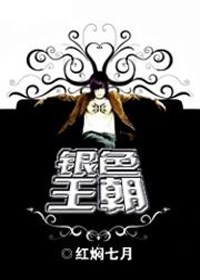龙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第3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深两岁被立为太子时被派来做贴身侍女,此后直到朱见深十八岁。朱见深经历着一个男孩的童年、少年和青年,而所有这一切,里面都有万氏——一个成熟的女人,一个处在十九岁到三十五岁之间的女人,一个除了她所照顾的这个小男人,身边再没有别的男人的女人。这女人将教给朱见深什么呢?吃饭、穿衣、说话,也应该还有别的……
想想贾宝玉身边的袭人吧,《红楼梦》第六回写贾宝玉梦中与秦可卿缱绻之后,“迷迷惑惑,若有所失……遂起身整衣。袭人伸手与他系裤带时,不觉伸手至大腿处,只觉冰冷一片沾湿,唬的忙退出手来,问是怎么了?宝玉红涨了脸,把他的手一捻,袭人本是个聪明女子,年纪又比宝玉大两岁,近来也渐省人事,今见宝玉如此光景,心中便觉察了一半,不觉也羞的红涨了脸面……”“渐省人事”的袭人与宝玉尚且有这种故事,何况万氏跟小她十八九岁的朱见深之间?前面说到周太后因不解而质询朱见深,据说朱见深这么答的:“臣有疝疾,非妃抚摩不安。”{13}话已很露骨了,他对万氏明显有一种旁人所不可代替的“肌肤之恋”,至于后者如何做到这一点,则“不足与外人道也”,猜想起来,肯定不止当“疝疾”发作时吧!
多好的小说素材,可惜还没人利用。
成化喜欢半老女人,为恋母情结所困,虽然心理或人格上略有障碍,但说到底是他的私事,本亦无可厚非。麻烦在于他是皇帝——皇帝的事,能是私事吗?
成化二年,朱见深当爸爸了!这头一个孩子居然是一个男孩儿,而这男孩儿的母亲居然是万氏!天晓得,“贞儿”还真鸿运当头,刚刚除掉吴皇后,自己就生了皇长子,有这资本,再加上皇帝几乎注定不衰的恩宠,将来夺取皇后位子岂非易如反掌?果然,朱见深立刻晋封万氏为贵妃。
可是,老天却跟他们开了一个委实有些刻毒的玩笑。成化的长子正月出生,连名字都没来得及取,到当年十一月竟然病夭了。报应吗?天谴吗?不知道。总之,“贞儿”的美梦就这么破灭了。年近四十,生育能力式微已成定局,何况皇帝身边还有那么一大批“当打之年”的生力军!设想一下,在美女如云的后宫之中,一个既无青春又无姿色、几乎没有再次生子机会、彻底绝望的半老女人,内心会怎么样呢?变态,是必然的。
她从此变成了一个杀手,一个专门谋害胎儿或婴儿的超级杀手。史称:“掖廷御幸有身,饮药伤坠者无数。”{14}这可是明确记在正史里的。“无数”,意味着所有成化种下的种子都被她逐一拔了根苗,而且必定不止是男胎,因为只要密探来报某某宫人受了孕,她就一律投之以毒药。这实在是太过恐怖的一幕。只有一次,万氏失手了:又一个宫女被宠幸后,传出怀孕的消息,万氏照例下药,但中间环节却发生了一些为她不知的情节,这孩子终于被秘密在别宫养活——此人非他,正是正德之父、日后的弘治皇帝。关于这桩惊险故事,稍后再作详述。
万贵妃对失子之痛所发起的疯狂自我补偿,并不仅仅限于搞死成化与别的女人弄出来的胎儿。她开始让自己的亲属大捞特捞,她的三个兄弟喜、通、达,贪得无厌,仗着姐姐,直把国库当做自家银行。他们不断从各地弄来奇巧之物卖与宫廷——所谓卖只是形式而已,因为那些东西的价值与其价钱完全不相称,“取值至千百倍”{15}。更荒唐的是有时他们干脆做的是无本生意,从成化那里讨来盐引,把盐卖了钱,再买成玩物回卖与宫廷,“车载银钱,自内帑出,道路络绎不绝,见者骇叹”{16},府库几为之掏空。
如只搞钱也还罢了,但搞钱的人很难不搞权,因为极权体制下钱和权两个东西总是结伴而行,搞钱是因为有权,有权就会搞钱。万贵妃就很好地演示了这种关系。她搞权搞得远远超出宫掖争宠的需要,其触角进而延伸到整个朝政。她是一个女人,女人是做不了官的;其次,她虽然擅宠于成化,惜乎名分仅为贵妃,且明摆着已失去做皇太后的前途,所以吕后、武则天模式也与之无缘。不过不要紧,她可以找代理人。上哪儿找?很简单,到太监里找。太监中万氏死党甚多,钱能、梁芳、覃勤、韦兴都是有名的靠结欢万氏而作威作福的大太监,这里着重说说汪直。
汪直可说是万氏嫡系,从小在万氏所住昭德宫当差,做事很称万氏之心,成化则爱屋及乌,让汪直先升御马监,再掌西厂,终于“威势倾天下”,跻身明代巨阉之列。
我们知道,明朝特务机构过去只有锦衣卫和东厂,现在却斜刺里冒出来一个西厂,它是成化皇帝专为汪直设的。这西厂有万贵妃撑腰,来头之大可想而知。据说西厂捕人,根本不用奏知皇帝,完全自作主张,想抓就抓。汪直出行,随从甚众,前呼后拥,“公卿皆避道”,国防部长(兵部尚书)项忠以为可以不吃这一套,结果被当街狠狠羞辱一番。史家评曰“权焰出东厂之上”——自西厂汪直一出,原先不可一世的东厂就算不了什么了。
汪直这样折腾了大半年,搞得人心疑畏,朝臣按捺不住,终由首辅商辂率群僚弹劾汪直,指控汪直用事以来“卿大夫不安于位,商贾不安于途,庶民不安于业”。成化阅疏大怒,派人至内阁问罪:“用一内竖,何遽危天下?谁主此奏者?”但商辂们似乎豁出去了,居然答道:大家同心一意为天下除害,没有主次先后;满朝臣官上上下下,皇上如果觉得有罪,尽管全部逮起来好了——俨然有“罢朝”不干的意思。与此同时,那位曾当街为汪直所辱的兵部尚书项忠又在发起新一轮的弹劾,倡议所有部长级高官联名倒汪。成化大约没料到朝臣如此团结一致,不得已暂罢西厂,让汪直回御马监任事。然根据“正不压邪”的规律,可以预见朝臣们这次无非得逞于一时罢了。
汪直避了避风头,暂时退场,成化对他的宠信可是一点亦未尝衰减,仍时秘遣汪“出外刺事”……汪就这样静候邪恶必定战胜正义的规律发生作用。果然规律起效了,只是来得之快恐连汪直自己亦不曾料到。仅隔一月,倒汪大将项忠即被废为民。原因是朝臣中一部分“聪明人”经过观察,迅速得出结论:皇帝在汪直这一边。于是审时度势,他们掉转枪口,对准汪直的反对派。项忠首先被诬构除掉,首辅商辂见状也称病引退,随之而去的辞免的大臣多至数十人。屡试不爽的邪恶必定战胜正义规律再次奏凯,不仅西厂复设,且汪直其人从小丑一跃而为伟人,满朝尽传拍马谀颂之声。一位名叫戴缙的御史甚至说:“大臣群臣皆无裨于政,独有太监汪直摘发,允协公论,足以警服众人。”此君两年间连升五品,做到了都御史(都察院首长)。士大夫乃竞起效尤,什么“西厂摘伏发奸,不惟可行之今日,实足为万世法”一类谀词不绝于耳,士风一时为之大坏。
这种结果完全合情合理。中国帝权政治体制内,皇帝和朝臣之间有一种天然的离心力;朝臣越看不顺眼、越加排斥的人,皇帝反而愈信赖愈为倚靠,比如太监就是这样。太监是什么人?家奴也。朝臣却是一帮跟皇帝挑刺儿找碴儿、让皇帝闹心憋气的家伙。所以商辂、项忠想要扳倒汪直,简直是开国际玩笑!
最后汪直究竟怎么失宠的呢?还是他的同类立的功。几年后,大约汪直太过势焰熏天让别的太监心理不平衡,一次宫中演戏,不知是谁指使小太监阿丑排演了一出调侃小品,饰成醉汉在那里骂人,旁有曰:“圣驾到。”不理,谩骂如故,再曰:“汪太监到。”阿丑赶紧爬起来逃走,一边逃一边说:“今人但知汪太监也。”成化看了很不是滋味,史书的形容是“稍稍悟”,实际上“悟”字应该代以“怒”,并且也一定不是“稍稍”,未尽形于色而已。应该并非巧合——就在观剧后不久,执领东厂的大太监尚铭就跑到成化那里秘密揭发汪直,说他如何侦得汪直私下里说过什么什么“秘语”,以及汪直做过哪些哪些“不法事”——详情究竟若何,史书语焉不详,总之,成化就此疏远了汪直。到成化十七年,汪直被打发到大同做镇守,不让回京;很快又发至南京御马监,西厂同时第二次撤废;再后来,降汪职,究办其党王越、戴缙、吴绶等,不过汪本人却终得善终于南京。
总结汪的倒掉,有两点:一、完全得力于太监内部的争风吃醋,东厂尚铭正是西厂汪直权场崛起的最大受损者,这证明了突破口总是来自同一营垒里面,更证明邪恶很难被正义所击败,却往往要由另一股邪恶来战胜。在这一点上,汪直也预演了正德朝刘瑾的下场。二、以汪直那样的罪愆而得善终,在明朝这个量级的权阉中是独一份,何也?我推想还是因万贵妃之故。汪在成化十七年失势,万氏则直到成化二十三年才死去,倘非如此,汪直要想有比刘瑾、魏忠贤更好的命,恐怕不可能。{17}
朱棣以后,明朝历代皇帝的颟顸、下作、昏智,明显呈逐代上升之势,到成化皇帝朱见深,算是又创了一个新高。
过去人们抨击帝权统治,多从大事着眼,比如暴君如何虐民、昏君如何误国等;但我读《明史》最深的感触却是,对其中很多皇帝来说,问题根本不在于他们作为国家领袖的素质、才能如何,而是作为一个人,一个极普通的有正常心智的人,是否合格的问题。
像这位成化皇帝,其脑瓜子里究竟装了些什么东西,无可揣度,纯然是不可思议的。偏爱半老女人、沉湎房中术、迷信妖僧……这些情节虽然荒唐,然揆诸人性,都算情有可原。可是,设若巨万之家硬是被家贼盗得一干二净,主人还无动于衷,就实在让人不明所以了。朱见深恰就是这样一个大呆瓜。
梁芳、韦兴,这两个和万氏兄弟里外勾结的“硕鼠型”太监,终被揭发。朱见深前去视察国库,发现国家历朝积存下来的七座藏金窖已经空空如也(“帝视内帑,见累朝金七窖俱尽”)。史载朱见深见此骇人之状,只淡淡说了两句话。一句是:“糜费帑藏,实由汝二人。”另一句是:“吾不汝瑕,后之人将与汝计矣。”{18}头一句等于废话,事情明摆着这样,何用说?第二句除了明确表示他不会追究此事,似乎还在为自己死后两位宫廷巨盗的命运担忧——这像人话吗?像正常人做的事吗?这样的人,斥之为“弱智”毫不为过吧?
成化帝唯可自豪的是,他的陋劣与不可理喻并非登峰造极;等他嫡亲的孙子朱厚照登上皇位,立即在同样禀赋上后来居上、大放异彩,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所以说:好戏还在后头。
身世之谜与窝囊爸爸
朱厚照出生后不久,便发生了一桩在整个明代都数得着的惊天大案,时称“郑旺妖言案”。
案子主人公郑旺,是北京最底层社会的一员,住在京城东北角的郑村镇,家里世世代代当兵。
明朝制度:一入军籍,“世世不改”。“兵之子弟为余丁,既为出缺时充补,又为正兵及官调发时或勤操时执耕稼之事。”{19}郑旺正是这么一个“军余”,用今天的话说,大概就是预备役士兵。
这郑旺虽然讨了老婆,还生了一个女儿,可他实在太穷了,所以像这种人家通常有的情形一样,女儿养到十二岁就被卖到富贵人家,一来换点钱,二来也是给女儿找条活路。
最初女儿是被卖到贵族焦礼的伯爵府,后听说又被转卖给一姓沈的通政{20}当婢女。这郑旺,自把女儿卖掉以后,就再未将她放在心上,直到有一年,约摸弘治十六年前后,邻村发生的一桩事却忽然让他想起了已被卖掉多年的女儿——他听说附近驼子庄有户人家的女儿入了宫,众乡邻就说,这家人如今算是皇亲了。此事令郑旺忽发奇想,不知怎的觉得自己女儿也进了皇宫。倘若果真如此,他郑旺不也同样做了皇亲吗?穷疯了的郑旺于是展开他的“皇宫寻女行动”。他有没有循序先到伯爵和通政府邸打听女儿下落,史无记载,我们所了解的是他径直奔皇宫而去,仿佛认准了人就在那儿。
谁都知道北京人长于结交,再没能耐的人保不准也认识几个场面上“说得上话”的朋友。显然,五百年前北京便已是这种情形,连郑旺这号人,居然也有两个锦衣卫“舍余”的铁哥儿们——所谓“舍余”,亦即锦衣卫人员的家属子弟——一个叫妥刚,一个叫妥洪,是兄弟俩。
由于锦衣卫是皇家鹰犬,跟内廷多有往来,所以郑旺就托妥氏兄弟走走太监的路子。妥氏兄弟果然替他联系上了乾清宫太监刘山{21},过了一段时间,刘山传递消息,竟然说郑旺的女儿找到了,确在宫中:“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