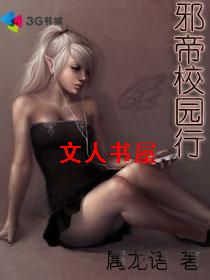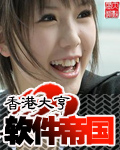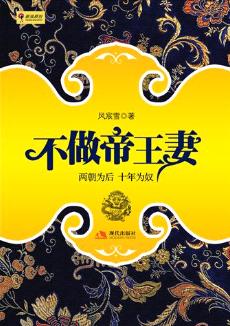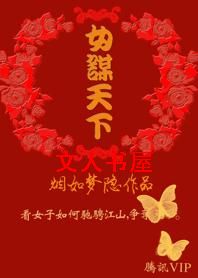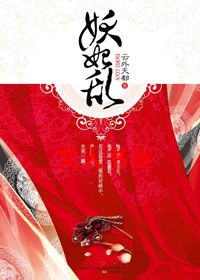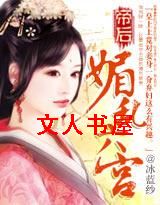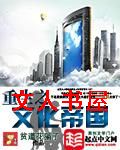曹操与献帝-第2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若此诗为我孔融所写,诗末该如何着落?”白芍不假思索,一笑而答:“山不知高,海不知深,文魁才尽,无以自矜。”孔融笑道:“无以自矜不过是无以自夸也,不如再改为‘文魁才尽,无病呻吟’,岂不更痛快?”
四人全笑了。
孔融接着问白芍:“这诗若你写,末尾二句该如何着落?”白芍应语随答:“山亦厌高,海亦厌深。移山填海,天下太平。”孔融显得大度笑道:“好好,实为才女,名不虚传。再借着酒胆说一句,丞相,你这主簿实是才貌双全啊。”说着他与曹操都笑了。白芍说:“知道孔大人今日一番戏言耳,实为给丞相添趣。”孔融点头道:“是,是。你今日这一番言论呢?”白芍说:“也戏言耳,给孔大人添趣。”
孔融接着说:“诗言志,既在有意也在无意。今日主簿自言‘移山填海’,此乃精卫之志也。上古神农炎帝之女,为东海淹死,后化为一只鸟名精卫,终日衔西山之石填东海不已。精卫移山填海乃是意志坚强、不畏艰难之象征,也是怀深仇大恨而誓报仇雪恨之象征。不知主簿无意间露出精卫之志,有何深仇大恨而誓报誓雪?”
孔融此话问得锐利,目光也直射白芍。
白芍垂下目光不想回答。
曹操见此哄慰道:“好好,我与孔融小孔夫子今日饮酒作乐而已。”又对孔融说:“方才论诗,你居了下风,当罚酒三杯。由主簿来罚。”曹操一挥手,左右斟酒满杯。白芍缓了缓神情,举酒递孔融:“敬孔大人酒。”
孔融看着白芍纤嫩之手欲接不接,叹道:“美哉此手,如脂如玉!”而后接过酒,不饮却道:“昔日燕太子丹请荆轲刺秦王,饮酒于华阳之台,让其所宠幸美人出来敬酒,荆轲见其双手如玉曾赞叹道:‘美哉手也!’席散,太子丹派内侍以玉盘送物于荆轲,荆轲开视之,乃美人之断手。太子丹明告荆轲,无所吝惜。荆轲叹曰:‘太子厚遇轲,乃至此乎?当以死报之!’时至今日丞相若能将此美哉之手赠融,融也誓为死士,为丞相行刺天下任何枭雄!”说着举杯一饮而尽:“丞相看如何?”曹操笑说:“荆轲见美女之手动了色心,太子丹则断美女手送之以断其望而已。今日孔融孔夫子拿荆轲赞手说事,不过是喝酒动了色心而已。”
曹操戏谑而笑,转头见白芍不悦,乃说:“好好,孤与孔大人戏言耳。”孔融又连饮白芍敬过来的两杯酒,说:“融今实非戏言。卑职夫人新丧,倘若主簿不嫌弃,丞相又肯割爱,我当立择吉日明媒正娶主簿为夫人。”说着径自起身,整理衣冠,堂堂正正叩拜于曹操面前:“借酒胆包天,望丞相成全。”
此举实出曹操意料。
这时白芍起身,冷淡地说:“丞相还有事吗?若无事,我先告退了。”
曹操立刻对孔融说:“知进退吧,你已得罪了主簿。”孔融听出究竟,慨叹一声,起身对白芍道:“得罪,得罪,融又借酒戏言耳。”一边入座一边说:“我凭今日主簿之三敬酒,就可为丞相当死士去行刺四方了。”曹操一边安抚白芍重新坐下一边说:“此天下孤要行刺谁?袁绍?袁术?孙策?马腾?哪个值得我派刺客行刺?剪除诸雄,一平海内,我用不着这等手段。此乃小人之所为。”孔融说:“秦王不用,太子丹要用。丞相不用,丞相或早晚成秦王之势;但反丞相者必用也。刺客未必小人之举,但诚为弱者之举也。”曹操说:“言之有理,我当年行刺董卓,正是以弱击强。”孔融还接着自说自话:“曹府内早晚会潜伏刺客也。”
曹丕不由得打量了白芍一眼。
白芍注意到他打量,坦然佯装不知。
曹丕打量了白芍,自己又走开了神。
曹操问:“曹丕,今日你始终似心神不定,定有大事要言。”曹丕至此承认道:“不瞒父亲,确实有事。”曹操说:“讲。”曹丕为难:“暂不急。”曹操说:“是否觉得人多不便?”曹丕未否认。曹操挥退左右,又说:“讲吧。“曹丕仍不言。曹操说:“主簿早已参与曹府机密议事,你是否避讳孔融?”孔融欲起身:“你们议事,卑职先告退了。”曹操伸手制止,对曹丕说:“若讲公事,孔融乃谏议大夫,且为政正直,不必避讳;若讲家事,孔融是我挚友,也但言不妨。”
曹丕略想一下说:“先讲一件要事、公事。事关太尉杨彪。”
曹操注意了,孔融也注意了。曹丕说:“据杨彪的一个亲随叫杨小的举报,那日田猎路上,他亲见杨雕先后将两支箭递杨彪,杨彪插到自己箭壶中。看来杨彪那日也是准备借箭射人的。”曹操点了一下头,沉吟道:“不出所料。但杨雕至死也未交代此事。杨彪也肯定早已将那二箭销毁。”曹丕说:“杨小还举报,袁术密使昨日到杨彪府中,现还在他家。”曹操说:“此事才重要。”曹丕说:“是否可凭此举报突击搜查杨彪府宅,连密使同密信一并查获?”曹操说:“袁术两年前就私藏先王玉玺僭号称帝,大逆不道。杨彪原与袁术儿女亲家,现又秘密沟通,确是重大嫌疑。但突击搜查仍缺十足理由。即使查获袁术给杨彪密信,也只表明袁术的一厢情愿,并不能给杨彪定罪。”曹操略思忖道:“将杨彪府宅四面严控起来,但等信使出来,就将其逮捕。杨彪必有回信,到时连人带信一并查获。”曹丕立刻点头道:“遵命。”
曹操转头对孔融道:“此确非小事,还望酒仙慎勿泄漏。”
孔融此时早没了酒意,说道:“丞相做事合乎理法。卑职若与丞相意见不同,必在朝上分庭抗礼,这种通风报信、鸡鸣狗盗之事,融绝不会做。况丞相如此信任融,融必以信相报。”
曹操又问曹丕:“还有何事?”曹丕说:“此事更难讲。”曹操问:“公事,家事?”曹丕说:“既公事又家事。”曹操蹙了下眉:“照讲不妨。”曹丕说:“许都最大的那桩人命案,即费庄灭门案已全部侦破。”曹操“噢”了一声听着。曹丕说:“主谋与我曹家有关。”曹操仍只是“噢”了一声。曹丕讲:“是我舅舅。”曹操略怔了一下:“卞夫人之弟?”曹丕说:“是丁夫人之弟,丁铎。”曹操皱眉了。他站起来踱了几步,而后又坐下,对孔融说道:“我这位丁夫人尖酸泼辣,连我都常退避三舍。她就此一位亲弟,此事甚为难办。”他转头问曹丕:“你打算如何?”曹丕说:“当然还该依法办,只不过丕想请示父亲大人,是否略缓几日,与丁夫人……”曹操摇头了:“此事恰恰不可延缓,更不可事先沟通丁夫人,那就尤成难事了。证据若已确凿,立刻抓捕归案,火速审理,做成既成事实,那样丁夫人那里的难办反而少些。否则苦了你父亲了,明白乎?而况你出任许都太守,本是揭榜昭于天下的,秉公办案不可有丝毫含糊。”曹丕说:“遵父旨。”
白芍同情地看了曹操一眼。
此时有人急忙来到亭子边禀报有秘事。曹操一挥手:“道来。”那人却径直上到曹操身边耳语道:“皇上正与董承入太庙登功臣阁说话。”曹操一听,自言自语道:“方下朝即如此,实在蹊跷。”他对孔融说:“有一要事须我亲自处理,别人替代不得,今日小饮就到这儿吧。”
曹操立刻乘十六抬大轿,在众将士护卫下急奔皇宫。
刚到宫门下轿,恰迎董承匆匆出来,有一顶轿正在等他。
曹操立刻当道迎住董承。董承急无躲处,只得立于路侧施礼。曹操问:“国舅何来?”董承说:“适蒙陛下宣诏,赐以锦袍玉带。”曹操看着董承身上穿系的锦袍玉带,点点头:“何故见赐?”董承说:“陛下忆念董某旧日西都救驾之功,故有此赐。”曹操又点头:“陛下真是不忘有功之臣。这玉带可解下容我观赏一下?”董承知衣带中必有密诏,唯恐曹操看破,迟延不解:“丞相何需看此?”曹操略变色:“你解不便,我可令人帮你解。”略一示意,左右上来。董承连忙道:“何需劳众。”便解下玉带交与曹操。曹操翻来覆去看了半晌,未发现破绽,笑道:“果然是条好玉带,可否再脱下锦袍借看一下?”董承心中畏惧,不敢不从,遂脱锦袍献上。曹操亲自以手提起,对着日光细细详看,亦未发现可疑处。他便自己穿上锦袍,系上玉带,回顾左右:“长短如何?”左右皆称丞相穿着正好。曹操对董承说:“国舅即以此锦袍玉带转赐给我,何如?”说着盯着董承。董承说:“君恩所赐,实不敢转赠;容董某另外制作锦衣玉带一套奉献丞相。”曹操踱了两步,停住说:“国舅受此锦袍玉带,莫非其中有什么不可告人之密谋吗?”董承惊慌说道:“董某焉敢?丞相如要,便当留下。董某虽受君恩所赐也绝无吝惜。”曹操仍存疑惑地打量着董承,董承索性施礼道:“衣带丞相留下,董某就此告辞了。”曹操这才笑道:“天子之赐,吾何相夺?聊为戏耳。”就脱解锦袍玉带还董承。
董承这才又施礼,穿系上锦袍玉带上轿走了。左右问曹操:“丞相进宫还是回府?”曹操看着董承远去的轿子说:“回府。”
第四节
董承受汉献帝赏赐锦袍玉带乘轿回到家。一下轿门吏、家奴秦庆童早在大门口迎接。秦庆童侍候着董承上台阶进了大门,惊喜奉承道:“这锦袍玉带果真是皇上所赐?”董承不愿与家奴多说:“是。”秦庆童本想讨个好,没想到董承脸色并不好看,就不再说了,只站在一旁打量董承身上的锦袍。
董承入到厅堂,崔夫人与侍妾元英一并迎接。二人都看着董承穿系的锦袍玉带眼睛发亮。崔夫人惊喜道:“陛下所赐?”董承转头瞥了一眼,秦庆童知趣,无言退下了。临退与元英对了一眼。董承这才坐下说:“陛下亲领我入太庙,上功臣阁,忆念我当年护驾之功,将他穿系的锦袍玉带解下赐我。”崔夫人说:“那大人该高兴才是,为何愁眉不展?”董承不便讲,只能长叹一口气:“圣恩难报啊!”崔夫人说:“大人累了,刚下朝又入宫,让元英给你料理侍候一下,我去让厨子备餐。”
崔夫人退下了。元英走到董承身后给董承捏了两下肩膀,又将董承的脑袋慢慢放倒枕在自己胸脯上揉起来。董承有些不耐烦地说:“你是不是又自己犯骚拿我的脑袋来解乏?”元英眯眼惺忪地晃悠着身体嗔道:“轮不上用大人身体,还不让用用脑袋呀。”董承真不耐烦了,抬起头摆了一下手:“今日没心思,免了。”元英讪讪地退下。
董承脱下锦袍举起来察看,没发现什么,又摇摇头穿上。拿起玉带又看,似乎也没有什么。这时崔夫人进来了:“大人,怎么不让元英侍候了?”董承道:“心中有事。”崔夫人说:“先用餐吧。”董承一挥手:“饭也不想吃,我实有大事中之大事!”
董承这日一直心绪不宁。到了夜里,一人独坐书院,在灯下将锦袍反复看了,仍无任何发现。他背手而踱,自言自语道:“圣上赐我袍带,命我细观,必有其意,今不见痕迹,何也?”又取玉带检查细看,乃白玉玲珑,碾成小龙穿花,背用紫饰为衬,缝缀整齐,并无破绽。董承百思不解。此时有动静,门被轻轻推开,他喝问:“谁?”是侍妾元英,夜装素丽,云鬓芬芳,说:“想问大人是否要服侍?”董承挥了挥手:“我这里独自夜读,不用侍候。”云英看了一眼董承手中的玉带,欲言而止,退出了。董承又拿起玉带在灯下观看,仍无任何发现。窗外又有轻声咳嗽,他喝问:“哪一个?”窗外答道:“是小人秦庆童,想问大人夜深要何侍候?”董承烦了:“早已有言,今夜无须任何侍候!”窗外秦庆童道:“那小人退下了。”
董承略生疑惑地看了窗户一眼,站起走到门口,推门出来,唯见一片月色,静无人影。他又回到房中,拿起玉带反复查看寻觅,仍无所获。他将玉带放至案几上,无奈摇头。良久,苦思不得其解,困倦袭来,正想伏案而寝,忽然灯花落于玉带上,烧着背衬。董承急忙用手擦拭之,已烧破一处,里面微露素绢,且隐见血迹。董承惊骇,急取刀拆开视之,展开的竟是汉献帝手书血字密诏。他初览一遍已涕泪交流,而后起身背靠台案朝窗站定,拿起血诏宣读:“朕闻人伦之大,父子为先;尊卑之殊,君臣为重。近日操贼弄权,欺压君父;结连党伍,败坏朝纲;敕赏封罚,不由朕主。朕夙夜忧思,恐天下将危。卿乃国之大臣,朕之至戚,当念高帝创业之艰难,纠合忠义两全之烈士,殄灭奸党,复安社稷,祖宗幸甚!破指洒血,书诏付卿,再四慎之,勿负朕意!建安四年春三月诏。”董承宣读完,将诏书供放于台案上,而后转过身,背南朝北向诏书跪拜道:“臣受诏遵旨,赴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