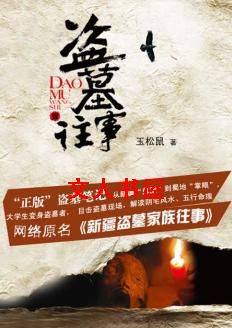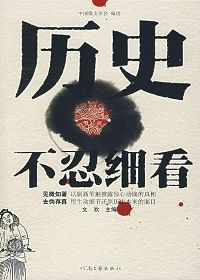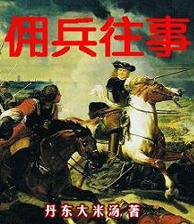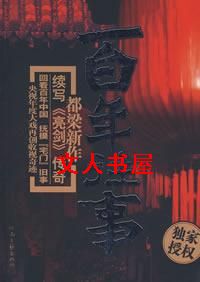往事不忍成历史-第1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1950年2月,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苏。当时中苏间通信靠短波电台联络,毛泽东出访苏联的决定,国内只有少数高层领导人知道,但美国报纸却公开报道了,蒋介石甚至还指派特务头子毛人凤制定了颠覆毛泽东专列的计划,铁路沿线的天津段甚至发现特务埋设的手榴弹。中方估计,完全可能是无线电码被破译。
有无线电常识的人都知道,无线电报是通过短波发射台发向天空,通过电离层反射后由收信机接收的。无线电波在宇宙空间是一种共享资源,保密系数很低。因此中国党政代表团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同时,随访的中国邮电代表团与苏方邮电部签订了《建立电报电话联络协定》,决定修建北京至莫斯科间直达有线电信线路,以适应中苏间交往的需要。
北京至莫斯科间的国际电信线路,全长12000多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陆上有线电线路。中国境内从北京经山海关、锦州、沈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到我国边境城镇满洲里的国境线,与苏联远东通信线路接通。中国境内全长2478公里,东北地区(包括我国内蒙古东部地区)为1900公里。工程任务是全线沟通两对可开通三路载波的铜线(3。5和2。9毫米径各一对),另根据国内通信需要架挂若干对铜线和铁线。这趟线路多是日伪时期留下的杆线,大部分在解放战争中或毁于战火,或被土匪盗毁。东北解放后,虽有部分段落抢修恢复,但按开通长距离载波通信要求需要重新改建。因此工程任务是绝大部分需新建或改建杆路、加挂线条、调整线位。全线均按我国电话专家侯德原设计的88式交叉调整交叉点施做交叉。在国际线路中还要完成哈尔滨至我国边境城镇绥芬河间的调整线位交叉工程,作为国际线路的备用线路。
为了完成这项规模庞大的工程任务,邮电部将它列为1950年的国家重点工程,全线开绿灯。东北邮电总局组建了由姥爷(副局长孙继述)兼任总队长的国际线路工程总队。供应处长白蕴章、财务处长孙绍迟兼任副总队长,分别负责器材、资金的筹措。工程师谢鼎为技术总负责人。总队只有六七个办事人员负责审查工程设计、审批器材和施工费用预算、器材分屯调拨、工程调度等工作。人员很精干,办事效率很高,急事不过夜、大事加班赶,甚至通宵达旦。
沈阳、锦州、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邮电管理局分别成立了工程大队或直属队,由各管理局局长或副局长兼任大队长或直属队长,连同总局工程队,共组建了9个施工队,每队30至50人。各管理局都从市县邮电局或驻段线务员中抽调觉悟高、技术好的线务员参加施工队,工人们都以参加国际线路工程为荣。
总队建立之初,对整个工程规模、沿线情况、原有杆线残存和可利用程度都不摸底,也找不出一个可以说清从山海关到满洲里全线情况的人,特别是对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戈壁草原一段都没人去过。身为总队长的姥爷亲率工程技术人员深入沿线,逐段检查线路情况和施工及分屯器材条件,基本摸清了工程规模以及各段施工的难度。然后夜以继日地赶制总体工程设计、器材和工程费用概算、器材运输分屯计划,使这一规模宏大而又艰巨的工程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1950年4月初,东北邮电工作会议又明确提出,修建国际线路是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工程于5月1日开始,争取年底全线贯通。当时国家处于医治战争创伤的恢复时期。资金不足、器材匮乏、工程技术人员奇缺,在短时间内完成这么大的工程,困难重重。在邮电部的苏联专家康纳布列夫疑虑地说:“这么短的时间,如能完成这么大的工程,我给你们立碑!”
在整个施工过程中,线路工人们真正发扬了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总局队、长春等队在完成了山海关至沈阳间工程后,六七月份集中力量修通了齐齐哈尔至满洲里一线。这段线路原有杆线残存无几,完全要重新立杆架线。几个队分头从扎兰屯、牙克石、海拉尔施工,线路穿越大兴安岭和呼伦贝尔大戈壁草原,不仅地形复杂,而且荒无人烟,气候异常,野狼成群,饮水也仅靠远地车运。施工人员住在帐篷或蒙古包里,中午戈壁草原气温高达摄氏40多度,夜晚则降到10度以下。工人早晚上下工地穿着棉袄走三四十里;中午穿着单衣干活还汗流浃背。蛟叮虫咬、风餐露宿,每天工作十二三个小时,但却没人叫苦。
入冬的11月份,正处于抗美援朝战争的紧张阶段,为了加快工程进度,总队调集几个队分头赶修哈尔滨至齐齐哈尔段。这一段的萨尔图(今大庆油田地区)是沼泽水害区,终年积水,电线杆整年浸泡在水中。立杆、架线、做交叉都要下到齐腰深的水中作业。当时没有在水中作业的防护用具,北国的11月,冰封雪飘,工人们都争先恐后地破冰赤腿下水,冻得顶不住了,上来喝几口酒、烤烤火,暖和过身子后下水再干。
在修建长春至双城和长春至铁岭段时,正值东北滴水成冰、地冻三尺的12月,一个工人一天只能用丁字镐刨一个杆坑。举起镐狠劲刨下去,只能刨下拳头大一块冻粘土,手掌震裂、关节肿痛是常事。但工人们仍咬牙完成了这段近400公里冻土地的新建杆线工程。哈尔滨至绥芬河线路工程,正值北国的“三九天”,由于日本侵略者在边境实行强迫“并村内迁”的残暴政策,百公里内几乎无一村落。因此工人们有时在摄氏零下40度的严寒中住在帐篷里,被褥外再铺上厚厚的麦草御寒,踏着一二尺厚的积雪坚持施工,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完成了施工任务。
在这么短的时间,完成如此艰巨的施工任务,与邮电部和东北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为了筹措器材,各邮电管理局千方百计挖掘库存、并将有些不开载波的线路上的铜线拆下以补充工程用铜线的不足。由于需要大量木杆,东北人民政府指示林业部门尽量支援,按时按需提供;指示铁路部门尽量沿线按点分屯器材,无论整车或零担,随时随地装卸。不停靠货车的小站,也破例停甩车皮,大大减轻了施工中的运输工作。
东北邮电管理总局十分重视国际线路工程。总局局长陈先舟已年过半百,仍冒严寒深入工程现场指导工作,给工程队送来了猪肉、大米、面粉等生活用品。
朝鲜战争最紧张阶段,美军飞机经常飞临中朝边界甚至深入中国境内狂轰乱炸,东北已处于第一线,工作异常紧张,已没有休息日可言。身为总队长的姥爷和工程师们以身作则,带领大家每天加班至深夜。吃住在办公室,听取各施工队电话汇报,分析工程进度,解决工程中的具体问题。姥爷每到工程现场都随身携带话机,随时搭挂在线路上检查工程质量,与总局和各队取得联系。东北邮电管理局许多老同志讲,姥爷对工程质量要求极其严格,容不得半点虚假成分,但对同志却非常关心、平易近人、工作作风很民主,从不摆领导架子,许多工程问题都是在现场和工人一起研究解决的。
国际线路工程如此之大,当时邮电部又没有统一的规范,只有由总队暂定一些主要规格标准。班组长只能经短期培训上岗,许多技术问题也只能在施工实际中去解决。北满地区冬夏温差很大,如何设计杆距和导线垂度,成为保证国际线路畅通的关键。日伪时期的习惯作法是不考虑导线的热胀冷缩程度,都将导线收得很紧,冻断了再接,连续锻炼几个冬天到不断为止,这样做显然会影响电路通畅的。工程师谢鼎建议,根据国际线路沿线每年最高最低温度以及风速等情况,自行设计导线垂度,并用垂度测量尺严格按架线时的气温收紧垂度。姥爷及时采纳了这条建议,派人收集沿线气象资料,由工程人员算出垂度标准,解决了导线的热胀冷缩问题,防止了冬天断线、夏天混线问题的发生。
国际线路全部工程从1950年“五一”后开工,到12月12日与苏联远东通信干线正式联通,历时仅7个月。由于各局保证了工程质量,我方线路与苏方远东线路连接后,立即畅通,这也是我国长距离路线建设史上罕见的。
这条国际线路的质量也经受了历史考验。20年后的1971年,林彪出逃,坠机蒙古温都尔汗。我的岳父、时任驻蒙大使许文益,为急于向国内报告情况,听取国内指示,在不能利用蒙古国电报局发报的紧急情况下,断然启用已封闭数年的经莫斯科至北京的国际有线高频专用电话(热线电话),及时报告了飞机坠毁情况。这条线路在历经20年、而且封闭数年之后,仍可供紧急启用,可见这条国际线路的质量是过得硬的。
抢修中朝通信干线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军仁川登陆后迅速向北推进,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为了保证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中国人民派出了志愿军入朝作战。
为了抗美援朝的需要,邮电部决定:对沈阳—丹东—新义州—平壤的对称电缆载波干线进行抢修维护。这条电缆干线是日伪时期日本人为侵略朝鲜和中国建设的,制式与我国东北的一致,但线路年久失修,1951年朝鲜新义州至平壤的长途地下对称电缆又遭到美机轰炸破坏。邮电部指示,姥爷代表中国邮电部与朝鲜信递省(朝鲜邮电部)会商:由东北邮电管理局派出一支长途电缆抢修队伍,奔赴前线,与朝鲜邮电工人一道,抢修遭受战争破坏的电缆。
这条线路是日本人遗留下来的通信干线,容量有5个四线组,开放3至6路载波电路,是当时沟通朝鲜南北和我国的主要通信干线,但修复这条干线却困难重重。首先是没有工程资料和工程技术人员,一时无法下手。“伪满”时期,这些电信设备和技术资料及维修管理都是日本人掌握,不让中国人插手。姥爷找了当时在总局留用的几个日本工程师,可是他们对此采取支吾搪塞的态度不肯出头。后来了解到留用技术员纪守民有这方面资料并参加过该方面工作。于是立即组织抢修队,让纪守民当教员为工程队边上课、边学习、边操作。
其次是设备能力不足。抗美援朝时期,我国还不能生产长途对称电缆,也不能制造三路载波机。为了朝鲜战场的需要,只能将日本人在我国东北沿前苏联边境埋设的对称电缆挖出来,送到朝鲜供抢修使用。没有载波机,就利用缴获的国民党使用过的美军CF1A四路电缆载波机支援朝鲜使用。
当时,在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配合下,已把敌人赶到了“三八线”,但是我们没有制空权,敌机不断地轰炸新义州至平壤的铁路线和公路线。而长途电缆干线恰恰是沿着这一线路铺设的,因此不断遭到破坏。为了防止敌机袭击,工程队常常利用夜间抢修,但夜间敌机也很猖狂,到处都是照明弹,工程队为对付敌机想了不少办法。随着我军空军力量壮大,线路沿线安全了许多,邮电工程队常常可以看到我空军机群与敌机在空中搏杀的壮观场面。
1952年2月,我邮电工程队完成新义州至平壤的全线抢修工程,恢复了通信,保证了我赴朝志愿军前线指挥部与祖国的通信联络。回国之际,朝鲜信递省颁发命令,授予我抢修队以“信递省劳动模范”称号和奖章。
此后,事业如虹、正值壮年的姥爷忽然沉寂了。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姥爷是因为“特嫌”问题而身陷囹圄。其罪状是:解放前能在国民党邮电部门做报务员的,不是“军统”就是“中统”;辽沈战役接收沈阳邮电局时为了安全和保密临时安放在家中的电台成了“与蒋介石进行秘密联络的工具”。更没想到的是,揭发姥爷的恰恰是与他一起出生入死的亲密战友,这是一位由红军摇机员出身的领导干部。尽管审查了两年未发现任何问题,但姥爷还是忍痛离开了他钟爱的通信事业。以后姥爷在沈阳许多基层单位待过。按说,人生遇到这么大的事情,放在谁都会郁闷的,但姥爷却不以为忤,没有悲天悯人。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派”用协和耳光打穿了耳膜,他都泰然处之。旧社会的磨难,参加革命的艰辛和生死考验,已使他历练出一种意境,始终以平常心态对待身边所发生的一切,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这样,他伴随着共和国的风风雨雨走了过来。十一届六中全会后,在邮电部过问下,姥爷的问题得以解决,并重新回到邮电队伍中来。姥爷今年已是95岁老人了,但许多事情还坚持自己动手去做。沈阳家中几十米的客厅里,几乎布满了自己做的鱼缸,用遥控器控制的彩灯使各种热带鱼五色斑斓;他制作的盆景在沈阳市比赛中还拿过奖牌。
纵观姥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