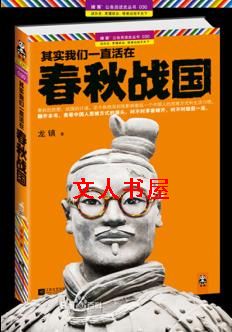绚日春秋-第59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狄阿鸟再蹬他几脚,欺负个够,也不见他再吭一声,干脆下了炕,出来看看,天虽然未亮,雪光却遍地,此时鸡叫遍地,倒也接近天明,他感觉酒后浑身酸软,伸伸懒腰,发觉王志已经起来了,刚刚打完一趟拳,素衣马靴,抱个热毛巾站在门口擦汗,热气蒸腾,就说:“那人怎么和我睡在一起?!”
王志笑道:“可不?!你哥俩均喝了不少,一定要亲热。”
狄阿鸟想象一下自己醉酒之后,和仇人勾肩搭背,同床而卧,不禁有点儿恶心,问:“他昨晚也喝了酒?!”
王志说:“是呀。百姓与官兵内外对峙,他心里也不痛快。”
狄阿鸟紧张地问:“死伤多不多?!”
王志无可奈何地摇了摇自己的脑袋,疑惑地说:“死伤在所难免。不过事情发生在下午,到了晚上,百姓们容易被驱散,行辕又经他人提醒,及时让安县长出面,处理得法,又组织了闾里官吏进行疏导,总的来说,没什么大的伤亡,据说只伤了一百多人。安县长现在还在走动,挨门串户呢。我就搞不明白,前些日子,虽有械斗,总体来说还好好的,怎么?!哎,现在就发生了百姓们冲击衙门的事情?!难道因我不听安县长的劝告,插手地方事务而起,给地方埋下的祸端?!”
他略一犹豫,轻声说:“他们断定,背后有不法分子在煽动。”
狄阿鸟笑道:“不法分子煽动民变,用意何在?!难不成,他们冒个头,故意让官府去抓他们么?!”
狄阿鸟力主穆二虎不会这么干,王志也不好往穆二虎身上讨论。他只是说:“百姓均说邓小公子下毒,纷纷大喊:惩办凶手。健少侯知道后,为避免死伤,一声令下,让军队外撤,将邓小公子抓捕归案,在衙门外点火公审,公开说:若有谁愿作证,一经证实,就地判了个斩立决。结果出乎意料,几个和邓平耍闹的无赖竟出来指认。少侯一定是想到了你,判个了斩立决,让士兵提着头颅给人看。邓北关人在行辕,瘫倒在行辕,没有过去,他妻子却在衙门外头背过了气儿,醒来诅咒,定要上京告少侯,让少侯不得好死。少侯插手地方事务,无疑是为自己惹祸,唉,也算为你进了心。你去看看吧,人头就在衙门外头悬挂着。”
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
狄阿鸟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当天晚上,自己喝醉酒,睡着了,竟不知这个大雪纷飞的夜里,火光映人脸,衙门外百姓们情绪高涨,齐声高喊,几个兵士提来人犯,五花大绑,大刀一扬,把人给杀了,提着人头示众。
他还真想不到和自己对头睡着觉,若无其事的健符竟敢这手。当时怎么一个情况?!所谓的“公审”不过是让百姓们看着杀,这是在断案吗?!这是在割脑袋取悦人。军士鼓噪,将军从权杀人,割人脑袋取信军心,这样的事儿很平常,可是以治军之法治人,却践踏了律法,的确是草芥人命。试想判定是非以人众而不以律法,人岂不皆以众敌法?!官府难道也为了取悦民众而屈枉之?!众人一闹,就提上人头给人看,让人知道自己多公证,这还是官府吗,不是劫富济贫,快意恩仇的绿林好汉?!
他虽有一胸快意,却不承认健符在为他杀人,只觉得这姓健的也太目无王法,什么事儿都敢干,怎顺手怎么干,心说:你不就是做过御林军中郎将吗?!不就是仗着天子宠信,父亲有本事吗?!别人不敢干的事儿,你敢干,干脆上绿林得了,我就不信,在京城你也敢这样乱来。
狄阿鸟说:“怎么真有人出来作证呢?!怎么这么巧,有证人在跟前呢。”
王志说:“所以有点玄,真像他们说的,背后有人煽动,要不是我们在一起喝酒,他们还真以为你在背后煽动。”
狄阿鸟心中一动,闪现出一个人,连忙往外跑,跑到县衙,只见衙门外头的旗杆上,果真悬着一枚人头。
天未大亮,站在下面,只能看到黑乎乎的一疙瘩子。狄阿鸟想及邓平贪图妻子之美色,觉得妻子定被他所害,即使不是死在他手,也一定与他有关,坐一旁大笑不止,团了一堆雪团,扬手往上丢,一边丢一边问:“你也有今日?!”人头挂得高,不容易丢到,他丢了几团,一阵烦躁,爬起来,一溜烟回王志那儿扯了一把弓,一壶箭。这回回来,天已经显亮,一大早出衙门扫雪的公差站在衙门旁,他也熟视无睹,朝上头看得真切,拈指便射,将一壶箭射了个精光。
其中两支钉不进结冰的人头,落在地上,其它的却个个入肉,插在上头。
北风把人头头发卷成一个扇面儿,裹了人头,外头再扎一把箭,随风摇晃,他这才出气,心说:“你有父子,我无兄妹么?!你以为你死,是死在别人手么?!”
他欣赏了一会儿雕花人头,肯定邓平的死一定是阿妹在背后造势,想起自己兄妹几个已可守望相助,热泪差点喷发,一边去寻路勃勃,让他带话回去,一边想:狄阿田也太没分寸,岂能拿这么多人命当儿戏?!
第一卷 雪满刀弓 一百三十九节
他到了路勃勃那儿,也见到了李多财,吩咐完路勃勃,让他开了城门后先回山寨,按自己原先计划的与樊英花讲,说自己稍后想法儿回去,这又问李多财:“这事是不是田小小姐那儿在背后使钱?!”
李多财说:“商会老李家暗中牵了头,想必确实是小姐使的手段,而且事前也有人在暗中收买我们的人。”
他又说:“驿丞死了。昨晚的事儿我们的人也在里头掺合。”
狄阿鸟不曾听樊英花提起,愕然道:“怎么可能?!”
李多财说:“就在咱家出事的那天晚上。那天晚上,姓邓的带着兵士在驿站出入,第二天驿丞就没有起床,被人在心窝子里捅一刀,趴在姘头身上,姘头也死了,也是一刀毙命,喉咙给割了道口。我这边几个认识的人聚了头,说这姓邓的太把我们十三衙门放在眼里,怎么也要给他点颜色看看,他们都这么说,我也跟着骂,分手之后,一个有点交情的拉我喝茶,给我引见了个人,那人给我一百两银子,让我们四处煽风,我下来一摸底儿,那个人是老李家派到外头的伙计,在当地面儿生。”
狄阿鸟怕官府会调查,说:“你想法传话给黑先生,老子的事儿不许他们再插手,万一官府调查,岂不是引火烧身?!”
李多财说:“官府查不出来,也不敢查,到我们十三衙门这儿怎么查?!我们头头又死于非命,无头案明摆着指向姓邓的,谁不觉得是我们十三衙门干的?!是我们干的,他们能怎么样,把暗衙掀个底儿,与我们打官司么?!最多不了了之。”
狄阿鸟点了点头,说:“那你让他们赶紧走,回京城去,别在这儿呆了,她毕竟年龄小,不知隐忍,难免出事儿。”
李多财说:“她一时还走不了吧?!我听人说官家要找商家贷粮筹款以补军,当地筹贷不来,外地商户还不知晓,以我看,他们是不愿意放过这个商机的!”
狄阿鸟对战胜不抱希望,天时地利人和应失尽失,打胜仗的机会渺茫,作以劝告:“那你就说给他们知道,官兵不是稳赢,要是打输了,这么一大笔费用,我们找谁要,岂不是自己先破了产?!”
他告别出来,回到王志府上,健符还没起床。王志在当门摆下酒食,等着他回来,见了他,请他坐下,他不肯,说:“我的心冷了,等着回去过日子呢,待会儿你别留我。”
狄阿鸟也是作个借口,北伐的事儿,他真的心冷了,可是不跟着,自己都把天子给自己的东西出示给众人,怎么能不跟着呢,跟着出力吧,自己确实心凉,也就图跟着做个哑口葫芦,对行军打仗的事儿不管不问,不理不睬,提前给自己造个势头。王志果然不快,大声说:“邓平都给你杀了,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你要怎么办好?!”见他没吭声,王志笑着说:“且吃些,听有些人说,你是不想出力。”
狄阿鸟叹了口气,说:“你别说,我还就真不想出力,说邓平是为我杀掉的,你当我是白痴么?!你们为平息百姓,反倒蔑视国法,杀了就杀了,你怎么偏偏安在我头上,让我欠着人情?!”
王志不再说话,只为他写酒。
写着,他喝着,却是说:“算了,让我跟着,我就跟着。”
里屋突然冒出一句话:“就知道你会这么说?!”狄阿鸟这才知道健符已经醒了,作色道:“你自己说,你是不是为我杀的?!”里头沉默了一会儿,说:“不全是。可也是想让你满意,才杀的。这一仗,没有你,不能取胜,既然不能杀邓北关,那只好杀他儿子让你出气。你不信么?!”
狄阿鸟哼了一声,说:“嘴长在你身上,你爱怎么说,怎么说。”
里头又说:“你先告诉我,这一仗怎么才有必胜的把握?!”
狄阿鸟有点恶心,心说,他们父子就这本事儿,反口讽刺:“你不知道就问,何必装模作样,让我先说。”
里头提议说:“要不?!我们都写到纸上。”
狄阿鸟想知道他到底有多少能耐,给答应了,看到王志递到笔墨,提笔写道:“最好以骑兵奔袭,次则以骑兵先行推进,步兵紧随接应。”写完之后,发觉王志伸头,生怕他当了传话筒,用手一掩,轻蔑地说:“你把他的拿过来。”王志笑了笑,进屋拿了张纸,摊在他面前。字与字相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龙飞凤舞地写着八个大字:“长途奔袭,掩其不意。”狄阿鸟抓抓脸,把自己写的那张纸交给王志。
王志拿屋里去了。
健符看了哈哈一通笑,说:“既然我们想到一起了,你觉得你还什么推辞的么?!无论是骑兵作战,还是长途奔袭,我想,没有人比你这个塞外生长的二胡子更熟悉。”
狄阿鸟大怒:“你才是二胡子?!”
他也不得不承认,从这一点上来说,自己确实有别人不可比拟的长处,想及长月方面的意思,怕是天子也是这么想的,这一仗,道路崎岖,补给困难,运输不意,又是隆冬,快过年了,然而,翻过来去想想,正因为如此,长途奔袭,以快打慢,以有准备打无准备,才是最有利的。
健符不以为意,说:“这一仗,陈元龙肯定也是这么想,不过,他有私心,定然让我作先锋,试探锋锐,而自己以中军接应,照你所说,以骑兵先行推进,步兵紧随接应。我想让你给我做参军,调理官骑,如何?!你放心,白羊王的首级给你留着,你要是割得下来,白羊王的家私就是你的,绝无人敢夺。”
狄阿鸟沉默了一会儿,说:“给我就算了,你听我的,立刻改赏军之令,白羊王家私,用以论功行赏,分跳荡(阵战破敌)之功,斩首之功,擒首之功,忘身之功,罚,加上杀良,杀俘,跳荡大功,千人之数,从所叙之十人,更改为一百人,擒到首领时,士兵可以共执共分,尽量让将士们均沾上点儿功劳。”
王志没有听说过,问:“忘身之功?!”
狄阿鸟说:“就是受伤的,战死的,给予跳荡之大功。”
健符在里头说:“这样均沾的话,就没有什么重赏了。”
狄阿鸟说:“劳军三倍于饷,可你想过,才多少钱,为了这点钱,战死多不划算?!你们再高举馅饼,说,十户何赏,百户何赏,千户何赏,如此赏格,实不公平也,几个人能得赏,擒获敌首,岂只一人之功劳?!一战下来,死者不得一文,侥幸擒了敌首的,登时巨富,岂公平乎?!”
健符没有吭声,因为从朝廷的观点看,朝廷没钱,设重赏不均沾,比均沾而不设重赏要划算得多。
狄阿鸟冷笑说:“做不到,休找我。”
健符说:“我答应你。”
狄阿鸟说:“俘虏营不可猝用,朝廷未作沟通,猝用生变。你们自己筹集官骑。”
王志说:“你上次不还在说,俘虏可以用来以夷制夷的么?!怎么改了口?!”
狄阿鸟说:“抓获他们的时候,你们不曾想收服人心,现在要打仗了,反想用他们,没门,以他们作战,只需对面狼嚎一声,顿时反戈。”
健符在里头沉默了一会儿,说:“你让指挥,你也不行么?!你通晓他们的语言,告诉他们,他们只要能打赢,就饶他们不死,给土地,给耕牛……”
狄阿鸟打断说:“给女人也不行。朝廷败坏信誉,你父亲把什么都做绝了,他们也不信。再说了,朝廷未曾给予过他们恩德,就驱使他们作战,胜负又未可知,他们凭什么站在朝廷一边,对他们自己的部族作战?!”
里头大声说:“你少拿我父亲比今日,时不同,势不同,当日,游牧人蜂拥,我父亲绝杀之,是为了震慑他们,他们以战为耕,倘若久聚中土,祸莫大于此,朝廷具备实力,的确不许他们染指中原,我父亲那么做,使万千胡贼谈虎色变,相夺辎